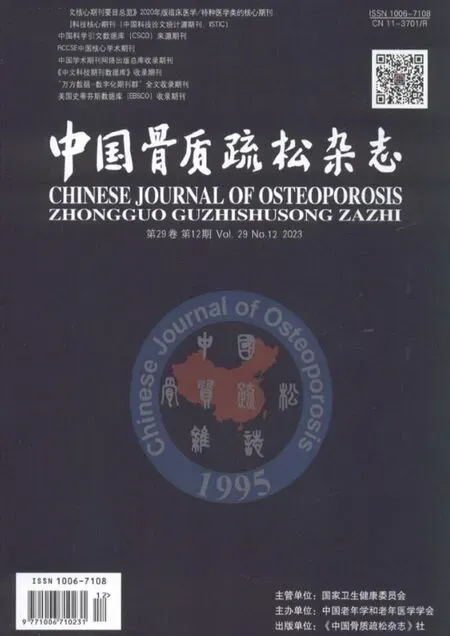肌骨共病視閾下肌肉骨骼交互功能研究進展
劉晏東 鄧強 彭冉東 王雨榕 檀盛 楊海云 李玙璠 向倩倩 楊軍
1.甘肅中醫藥大學,甘肅 蘭州 730030 2.甘肅省中醫院,甘肅 蘭州 730050
肌肉和骨骼在生物力學和化學分子的作用下共同調節著肌骨系統的新陳代謝,并組成了新興的研究領域-雙鏈肌骨系統串擾學說[1]。如果提到肌肉與骨骼在病理上的交互作用,那肌少癥(sarcopenia,SP)與骨質疏松癥(osteoporosis,OP)之間的關系以及二者共同的產物肌少-骨質疏松癥(osteosarcopenia,OS)則是討論的主題[2]。SP與OP在肌-骨亞單位下具有相同的臨床和生物學特征,而所謂OS即指SP與OP共存的一種獨立疾病,它以肌肉質量、功能和骨質同時減少為特征[3]。研究表明,SP和OP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4],且二者存在協同效應并可導致更嚴重的負面結果。在比利時,一項納入了288例老年受試者的調查顯示,SP患者合并OP的風險比非SP患者罹患OP的風險高4倍[5]。此外,SP和OP具有相同的危險因素,如遺傳因素、過量飲酒、長期吸煙、缺乏活動以及營養不良[6]。
1 肌-骨的生理交互功能
肌-骨系統作為一個精細協調的單元運作,肌肉與骨骼的相互作用不僅體現在它們的解剖關系上,還與機械效應有關[7]。肌骨之間也通過復雜的生化因素進行交流,以協調它們從發育到老化過程中修復與衰減的關系[8]。
1.1 生物力學因素
1.1.1機械負荷對肌骨的共同作用:機械壓力過低是老年人肌骨衰減的重要因素,長期臥床和較少運動的中青年人群以及處于太空失重環境下的宇航員也可罹患該病,這是由于肌骨系統所承受的機械負荷降低所致[9]。骨骼肌的質量取決于蛋白質降解和合成的平衡。Mena-Montes等[10]研究證明,長時間、低強度的增加機械力可通過減少炎癥、活性氧以及改善線粒體功能和GDF-11(一種與肌再生相關的蛋白質)來逆轉大鼠的SP癥狀。Uda等[11]也研究了機械刺激與肌質量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機械負荷增加可通過mTOR誘導蛋白質合成增加。骨骼的機械轉導機制更為復雜。骨細胞可響應機械刺激并通過一系列反應(鈣離子通道、氨基酸等第二信使的作用)最終激活機械敏感基因,促進骨形成[12]。而機械信號在骨細胞內主要是通過細胞內環境、相鄰細胞間和不同細胞間獨立單元中的功能性機械傳感器(微管、細胞骨架、纖毛、細胞外基質和連接蛋白)來轉導[13]。可促進對近微環境和納米環境感知的跨膜受體整合素也被認為有助于各種機械刺激后離子通道的激活[14]。雖然骨骼肌和骨骼之間的機械轉導機制存在差異,但也有證據表明二者之間可能存在一些共同的機制,以及多種機制的協同作用[15]。通過機械負荷增加肌質量和骨密度也被大量臨床數據所驗證,Cattaneo等[16]研究發現運動員們在經過16個月的足球訓練后骨密度和肌質量均發生正向變化;Liu等[17]發現游泳對骨密度有重要影響,可以明顯改善手握力和肩部、背部的肌肉力量;Boshnjaku等[18]通過評估不同運動對骨密度和肌肉質量的影響發現,久坐對照組的骨密度和肌肉量最低,這些數據都強調了運動對骨骼和肌肉的積極影響。
1.1.2肌骨雙向機械作用:骨骼肌可為骨骼提供動能和保護,并可將機械壓力作用于骨骼以影響骨強度;而骨骼為骨骼肌提供附著部位,是骨骼肌施加機械力的杠桿,可將機械力反作用于肌肉以調控肌質量。二者的雙向機械刺激是連接肌肉與骨骼的關鍵紐帶,對自主運動具有核心的促進作用[19]。機械串擾理論認為,骨骼肌通過以下方式促進骨骼的機械負荷:肌肉嵌插部位收縮產生的拉力、肌肉跨關節收縮產生的骨骼間壓縮力以及肌肉驅動長骨抬起遠端物體時的彎曲力。骨骼肌施加在骨骼上的機械負荷是骨重塑的重要影響因素,骨骼不僅適應來自肌肉的靜態力,還適應肌肉收縮產生的動態力[20]。“機械恒溫器”理論[21]進一步描述了肌骨之間的機械相互作用,該理論指出骨骼肌對骨骼施加的機械力若超過一定的閾值,骨轉換就會從骨吸收轉向骨形成以減緩OP的發生。更深層的分子機制是骨細胞在受到機械壓力后,ERK5被迅速磷酸化,骨細胞在這種應激下通過Wnt/β-catenin信號通路進行重組,從而將感知到的機械刺激轉化為生化信號并引發合成或分解代謝[22]。此外,離子通道、瞬時受體電位和G蛋白偶聯受體在骨機械轉導過程中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23]。研究發現,骨骼肌質量變化會誘發骨膜和膠原纖維發生拉伸變化,從而刺激骨骼生長。在青少年時期,肌肉力量較大,所以對骨骼施加的機械負荷會導致骨骼強度增加。相反,隨著年齡的增長,肌肉力量的下降會使部分骨骼發生重塑失衡[24]。此外,舉重運動會增加腰椎的負荷,從而增加腰椎骨密度;且由于舉起重物需要保持肌肉緊張,這樣骨骼就會將機械力反作用于肌肉[25]。
1.2 生物化學因素
1.2.1肌骨生化交互作用:骨骼肌還可以以非機械方式調節骨合成和代謝,亦即生化串擾。筆者在閱讀文獻的過程中發現,與機械串擾相比,科學界似乎對生化串擾的研究力度更大,范圍更廣。肌肉和骨骼均來源于胚胎的間充質干細胞,它們的發育在無數重疊基因和生長因子的作用下密切協調。肌肉分泌組由數百種分泌肽組成,這為理解肌肉如何與骨骼交流提供了概念基礎和全新范式[26]。這些因子中的大多數是巨大的細胞因子家族的成員,但其他生長和分化因子也可能在肌肉和骨骼之間傳遞信號。例如,離子和非肽小分子信號系統通常提供微環境來聯系細胞間的通訊[27]。
1.2.2肌因子調控骨骼:Pedersen[28]在2010年首次提出術語“肌因子”以描述由骨骼肌分泌的,可促進骨骼生成的活性因子,為骨骼肌和骨骼間的生化通訊提供了直接證據。目前被明確定義的肌因子包括肌抑素(Myostatin,MSTN)、白細胞介素-6(IL-6)、IL-7、IL-15、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IGF-1)、堿性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FGF-2)和鳶尾素等[29]。IGF-1主要在肝臟中產生,但也在運動期間的肌肉中產生,其傳導復雜且具有組織特異性,涉及JAK/STAT、PI3K和ERK等多條信號通路[20-21]。已有文獻明確指出,IGF-1除了對肌肉具有合成代謝作用外,還可對成骨細胞產生積極影響[30]。Sui等[31]認為,在骨骼中IGF-1可促進成骨細胞增殖和分化、抑制破骨細胞活性、調節腎臟1α-羥化酶(激活25-OH-維生素D)和磷酸鹽的重吸收。MSTN隸屬腫瘤生長因子-β(TGF-β)超家族,是肌細胞增殖和分化的負調節因子,MSTN敲除小鼠表現出肌肉肥大且骨密度顯著增加,該作用的起效通路可能是NFATc1/RANKL通路[32]。IL-6是一種促炎細胞因子,最初在體力活動后的血液中發現,Pedersen等[33]發現IL-6不僅對葡萄糖攝取和脂肪酸氧化有影響,如果與其可溶性受體gp130結合后,還可以刺激骨吸收。值得注意的是,IL-6還可增加早期成骨細胞分化,這意味IL-6可能通過負調節增加成骨[34]。IL-7和IL-15也是骨骼肌中的白介素因子,它們也通過同樣方式影響骨重塑[35]。鳶尾素由運動介導,除了對肌肉的影響外,還可以以低劑量方式提高皮質骨密度。這可能是通過上調骨橋蛋白和硬化素等成骨基因來實現[36]。
1.2.3骨因子調控肌肉:骨骼也作為內分泌器官發揮對骨骼肌的支持作用,骨源性因子包括骨鈣素(OCN)、FGF23、硬化素、前列腺素 E2(PGE2)、RANKL/Wnt-3a 和轉化生長因子(TGF-β)[1]。OCN是一種成骨細胞特異性非膠原蛋白,已被證明可通過Gprc6a受體向肌肉發出積極信號。OCN的慢性輸送不僅可以增加肌肉功能,還可以通過PI3K/Akt/p38 MAPK途徑促進肌母細胞增殖,并通過Gprc6a-Erk1/2信號傳導促進肌源分化[37]。FGF-23由成骨細胞和骨細胞分泌,在調節全身磷酸鹽和維生素D水平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除此之外,骨源性FGF23還可能影響肌肉功能[38]。TGF-β主要來源于骨骼并儲存在礦化骨基質中,可向肌肉發出相關信號,用TGF-β治療的小鼠顯示出原始和特定肌肉力量的產生減少[39]。Waning等[40]證明骨源性TGF-β可通過增加氧化應激導致肌無力。硬化素是由SOST基因編碼,由成熟骨細胞分泌,可通過經典Wnt/β-Catenin途徑抑制骨形成,而Huang等[41]發現硬化素也可通過抑制Wnt-3a對C2C12肌母細胞分化產生不利影響。PGE2是通過環氧合酶合成的信號分子,與炎癥和肌肉再生等多種生理病理過程有關。PGE2可通過增加骨細胞中的PI3K水平直接激活β-catenin途徑[42]。此前,Harada等[43]已證明PGE2可加速C2C12肌母細胞增殖和分化,提示來自骨骼的PGE2信號傳導可能對骨骼肌生成很重要。
2 肌肉與骨骼在病理上的相互影響
2.1 炎癥作用
眾多證據表明,慢性炎癥狀態是導致骨骼和肌肉質量損失的第一大原因,這與促炎細胞因子的生成增加有關,而該類因子的增加很可能是通過激活泛素-蛋白酶途徑來完成[44]。在部分臨床條件下,促炎因子損害機械轉導并觸發肌骨系統再生抑制劑MSTN、SOST和DKK-1的產生。炎癥水平的升高還會使ROS逐漸產生并刺激先天性和獲得性免疫系統釋放額外的細胞因子,從而使慢性炎癥適應免疫平衡[45]。研究還發現,類似TNF-α、IL-1和IL-6等促炎細胞因子在影響肌肉生成的同時還可促進骨吸收,此外,流行病學研究表明,SP和OP皆與C-反應蛋白(CRP)呈正相關,而CRP正是活動性炎癥的標志[46]。炎癥老化是免疫功能低下、長期生理刺激、遺傳、環境和年齡等多種復雜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而這些因素的變化同樣會影響肌蛋白水解并導致骨礦化減少,從而導致肌肉和骨骼質量下降,但SP和OP的發生順序并不明確[47]。
2.2 激素減少
在肌骨共減的病理發展中起關鍵作用的激素包括生長激素(GH)、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IGF-1)和性激素。人體的肌肉和骨骼均表達雌激素受體,無論肌肉或骨骼的雌激素受體表達降低均可影響另一方的質量及功能。正因為這樣,絕經后女性的雌激素替代療法能夠有效增加骨骼和肌肉質量[48]。男性年齡相關性SP、OP和肌骨共減的發病機制并不明確,但一般認為雄激素代謝而產生的雌激素在保存骨量方面發揮主要作用。老年男性的低睪酮水平預示著肌骨共減。事實上,睪酮水平降低首先會導致蛋白質合成減少,隨后致使肌肉質量損失并最終通過生化反應影響骨骼重塑[49]。
2.3 脂肪浸潤
也有人認為,炎癥浸潤可將間充質干細胞分化轉向脂肪生成,而高水平的骨髓脂肪組織與骨質流失有關;肌脂肪變性與肌細胞功能障礙有關[50]。目前的研究結果也支持這樣的假設,即較高的脂肪量可能是OP與SP之間相互作用的危險因素。Wyshak等[51]發現,體脂百分比與39歲及以上的女大學生的手握力和椎骨骨折之間存在顯著關聯。Hsu等[52]在一項社區橫斷面研究中發現,脂肪量與全身的骨礦物質含量呈顯著負相關。Bredella等[53]發現,肝臟、肌肉組織和血液中脂肪含量較高的肥胖者骨髓中脂肪含量同樣較高,這使他們面臨肌骨共減的風險。
3 肌骨共病的危險因素
3.1 遺傳及不良習慣
遺傳因素可顯著影響骨量和肌量,尤其是維生素D受體多態性已被證明與OS的發病密切關聯[54]。荷爾蒙因素對肌骨的影響貫穿整個生命周期,例如,低睪酮和低雌激素水平分別對男性和女性的肌肉萎縮和骨質流失產生不利影響[48]。過量飲酒和長期吸煙不僅會對成骨細胞和成肌纖維產生直接毒性,還通過對性激素分泌、蛋白質代謝、鈣磷代謝的不良影響造成肌骨共減。Kanis等[55]進行的一項Meta分析顯示,每日飲酒超過400 mL有可能增加骨折風險。一項納入法國608例社區男性的研究顯示,每周攝入酒精量超過210 g則會引發肌質量降低[56]。Law等[57]的一項Meta分析顯示,與非吸煙者相比,吸煙者的骨骼強度較差。另外,暴飲暴食導致的肥胖(脂肪浸潤)也可通過促進炎性因子的釋放干擾正常狀態下的肌骨代謝[50]。
3.2 運動及營養因素
運動可誘導線粒體的生物發生和功能運轉,增加衛星細胞及成骨細胞的數量和功能,同時抑制炎性因子,促進蛋白質合成。此外,定期運動干預后,肌纖維長度和肌腱僵硬等非質量依賴性肌肉因素也分別增加了10%和64%[58]。由運動介導的激素樣肌因子鳶尾素是由肌細胞運動后產生,近期研究發現鳶尾素對骨密度和肌質量均有積極影響[36]。相反,制動時間與肌骨衰減呈正相關關系[9]。良好的飲食習慣對于維持肌骨健康至關重要,營養攝入通常被認為是影響骨骼和肌肉的重要因素,比如鈣、蛋白質、必需氨基酸和維生素D的足量且聯合應用同樣可促進成骨及成肌作用,這些物質通過釋放IGF-1、抑制甲狀旁腺素和促進鈣吸收來調節細胞蛋白和生長因子[54]。隨著機體衰老,肌骨系統對蛋白質和維生素D的敏感性下降,間接導致肌肉和骨骼的分解代謝加劇,最終威脅肌骨健康,而缺乏此類營養導致OS發生的概率在53%以上[59]。腸道微生態紊亂(主要是腸道菌群的豐度和多樣性的異常變化)是導致肌骨衰減的另一重要原因,胃腸道內短鏈脂肪酸、益生菌、益生元和合生素的缺乏通過復雜的分子機制深刻影響著肌骨系統的代謝重塑[60]。
4 結語
鑒于全球人口平均年齡的逐漸增加,肌骨系統疾病對老年人群的威脅已僅次于心血管疾病,成為了世界性的公共衛生難題和社會經濟負擔。肌肉和骨骼緊密耦合,互為因果,由肌肉骨骼交互功能為基礎的肌骨共減綜合征作為SP與OP的疾病復合體,更使SP與OP所造成的不良結局呈現出1+1>2的疊加效果,所以有學者們將肌肉減少與骨質疏松的關系形容為“危險的二重奏”,所以對肌肉骨骼交互功能的研究已經刻不容緩。目前,醫學界雖然對該領域展開了較多研究,但理解肌骨共病視閾下肌骨交互作用的深層機制依然具有挑戰性,這將影響對肌肉骨骼衰變臨床治療方案的制定。在未來,有必要對肌肉骨骼交互功能的分子細胞機制及信號通路進行更深度的研究,這將有利于對SP和OP共同靶點和特效藥物的開發,克服肌骨分治的各種不良后果并實現肌骨精準靶向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