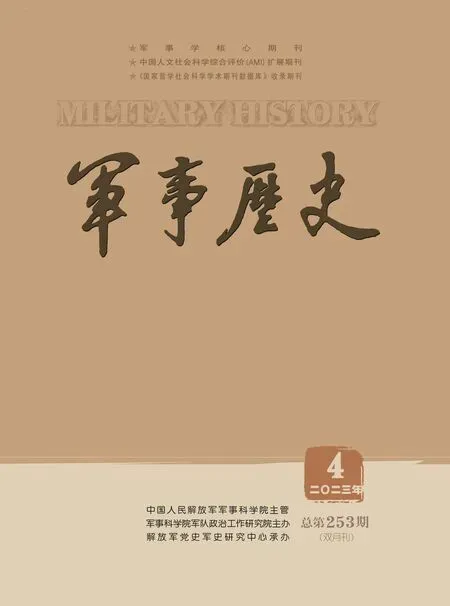清朝嘉慶年間的海防議論
——以海盜蔡牽事件為中心
★ 潘是輝 張婭雯 李 燦
清朝以馬上得天下,早期對于水師的建置并不積極。清初,為了統一東南沿海地區,僅以臨時編制的形態組成水軍與南明鄭氏集團抗衡。直至康熙元年(1662),方始設置福建水師提督與浙江水師提督來統領閩浙沿海水師營務;康熙三年(1664),又設置廣東水師提督,但在三年后裁撤,一直到嘉慶十五年(1810)才復設。由此可以看出清朝在嘉慶以前,相對于西北陸路,東南沿海并非其重視的防務所在。①參見[清]昆岡:(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550、551、553;李其霖:《見風轉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師與戰船》,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4 年,第147、151、165 頁。
在清朝設置水師提督的三個省份中,以福建最為緊要,除了清初與鄭氏集團水師對抗的考慮外,臺灣收復后班兵②康熙二十三年(1684),經施瑯建議,決定抽調福建原有兵額來臺灣駐防,可得“兵無廣額,餉無加增”的經濟效益。駐防臺灣的官兵三年一換,謂之“班兵”。參見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年,第260 ~262 頁。的配運、確保臺海兩岸的貨物運輸等,都是當時海防的重點項目。是以本文以福建沿海作為主要考察區域,首先對福建水師的建制作制度方面的簡述,再以嘉慶年間海盜蔡牽事件③對于蔡牽事件,有許多專門的著述流傳下來。比較著名的有:[清]鄭兼才:《六亭文集》卷4《紀御海寇蔡牽事》;[清]魏源:《圣武記》卷8《嘉慶東南靖海記》。近人論述可參見鄭廣南:《中國海盜史》,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319 ~346 頁;蘇同炳:《海盜蔡牽始末》,《臺灣史研究集》,臺北:“國立編譯館”,1980 年;李若文:《海賊王蔡牽的世界》,臺北:稻香出版社,2011 年。為觀察核心,采用微觀歷史學①微觀史學興起于20 世紀70 年代末,是當代西方史學思潮之一。微觀史學重在放大和傳遞普通人的生活經歷和精神體驗,從而完成見微知著、由特殊到一般的歷史認識過程。通過對個人命運的深度挖掘,相關史學著作往往能夠吸引普通讀者的閱讀興趣,從而獲得廣泛的影響力。相對于宏觀史學,微觀史學更加關注歷史人物個體和小事件。通過縮小研究規模,可以追蹤個體的行為和決策,最終目標是借此去窺探一個更大范圍的普適性。微觀史學的優勢在于,它使歷史學家能夠更近距離地了解過去人們的實際生活方式、決策方式以及與他人交往的方式。(Micro History)厚敘述②厚敘述,又譯作“深描”,是現代英國哲學家吉爾伯特·賴爾首創的概念,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茲在其論文《深描:邁向文化的闡釋理論》中對其加以論證發揮,來表達自己對民族志的寫作要求。格爾茨認為,文本是一個文化描寫的系統,對文化的描寫,要注意闡述其意義,而非傳統民族志式的事實性描述。基于此,格爾茨開創了“深描”的文本寫作方法,即對社會活動進行具有豐富意義的、全貌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方式,解析嘉慶皇帝與軍機大臣及地方官員們對于海盜入侵時諸多問題的考慮與舉措,以此試圖來了解嘉慶年間對福建沿海防務的各界議論狀況。
一、福建的水師防務
福建水師提督,在康熙元年(1662)以施瑯(1621—1696)擔任該職后,旋即于康熙七年(1668)裁撤。康熙十六年(1677),復以海澄公黃梧(1618—1674)之侄黃芳世(1642?—1679)管福建水師提督事,翌年復設該職。③參見[清]伊桑阿等纂修:(康熙)《大清會典》卷92《兵部》,第9 頁。福建水師提標,設提標總兵官一員,駐廈門。茲根據嘉慶《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和乾隆《福建通志》的有關記載,可一覽當時福建沿海的水軍兵防體系(見下頁表1)④資料來源:(嘉慶)《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473《兵部》,第7 ~11 頁;[清]郝玉麟等修纂:(乾隆)《福建通志》卷16《兵制》,第19 ~81 頁。按,南澳地區位于閩粵交界,南澳鎮亦設有右營,但專管廣東地界。參見李其霖:《見風轉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師與戰船》,第164 頁。。

表1:嘉慶時期福建地區海防水軍編制表
由表1 可以看出,乾隆年間福建沿海水師的駐防地點已遍布福建沿海各海防重地,包含福州南臺島、福州閩安、寧德霞浦、平潭島、廈門島、金門島、漳州東山島、臺灣艋舺(今臺北市)、滬尾(今淡水)、安平(今臺南市)、澎湖島,甚至廣東汕頭南澳等地都是福建水師的重要駐防區域。就防守區域來看,已能由點至面經緯整個福建附近洋面。
再看統計數字,當時福建水師戰船共配置有310 艘各式船舶。李其霖統計歸納后指出,清朝設置戰船數量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復臺灣之前達到一個高峰,高達500 多艘,之后戰船數量多維持在300 艘左右。⑤參見李其霖:《見風轉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師與戰船》,第386 ~388 頁。可見承平日久,福建水師因循巡海捕盜的習慣,百年來都沒有增加戰船數量的規劃。
再來看兵丁人數,表1 的統計顯示,福建水師在編制上有2 萬多人;軍官加上編制外的額外外委差不多達400 余人,數量上不可謂不多,然而對比康熙年間杜臻《粵閩巡視紀略》中所記載的福建水師人數,尚有不足。⑥[清]杜臻:《粵閩巡視紀略》,載《欽定四庫全書·史部七·傳記類》。參見李其霖:《見風轉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師與戰船》,第128 ~130 頁。清代各官方文書對水師兵員數量的記載,常有出入,但差異并不多。參見陳炳容、吳秀琪:《古地圖與金門史研究》,金門縣文化局,2022 年,第274 ~275 頁。由此可見福建水師歷康熙、雍正、乾隆直至嘉慶數朝,一百多年間一直受到忽視之一斑。以這樣的船只、兵力數量要防守廣闊的福建沿海,當然有些吃緊,特別在蔡牽等海盜侵擾東南海疆時,問題更是凸顯出來。
嘉慶二年(1797)九月開始擔任福建巡撫的汪志伊(1743—1818)⑦汪志伊,安徽桐城人,嘉慶二年(1797)任福建布政使,同年九月升福建巡撫,嘉慶六年(1801)請辭養病,嘉慶十五年(1810)再任閩浙總督,對東南海疆的狀況十分熟稔。參見《清史稿》卷364《汪志伊傳》。按,《清史稿》將汪志伊任閩浙總督的時間,誤為嘉慶十六年(1811)。,就曾對福建沿海防務的實際情形,提出《議海口情形疏》⑧[清]汪志伊:《議海口情形疏》,[清]陳壽祺等修纂:(道光)《福建通志》卷87《海防·疏議》,同治十年重刊本,第38 ~41 頁。本篇標年為嘉慶四年(1799),是《福建通志·海防·疏議》收錄嘉慶朝的唯一一篇。:
閩洋北接浙江,南連粵省,延袤二千余里,島嶼周回,口岸叢錯,設立水師三十一營,額設兵二萬七千七百三十名,額設大小戰船二百六十六只,分列南北,為犄角之勢。中以泉州之崇武為界。自崇武而南,派令南澳、銅山、金門暨提標后營各鎮將巡緝。自崇武而北,派令海壇、閩安、烽火暨金門右營各鎮將巡緝。往來梭織,聲息相通。一遇匪船游奕,即互相知會,上下兜擒,聲勢頗壯。
從這段議論不難看出,當時閩省官員依然使用傳統“捕盜”的保守觀念來看待即將進入19世紀的海防,以為妥善擇地設兵勤加巡防,就能使海疆永靖。不過,他也開始點出當時水師的問題,其一在“船身笨重”,其二在“舵工兵丁”:
嗣因船身笨重,捕盜不甚得力,經前署督臣覺羅長麟①覺羅長麟(1748—1811),滿洲正藍旗人,乾隆四十年(1775)乙未科進士。歷任福建興泉永道、山東巡撫、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兩廣總督,乾隆六十年(1795)署閩浙總督等職。參見《清史稿》卷350《覺羅長麟傳》。奏準,照商船式樣改造八十只,較為靈捷。又因舵工例用兵丁,常在本轄洋面巡哨,未能熟悉隔轄港道沙線,經前督臣魁倫②魁倫(1752—1800),完顏氏,滿洲正黃旗人。副將軍查弼納孫,襲世管佐領,兼輕車都尉,歷任四川漳臘營參將、建昌鎮總兵,乾隆五十三年(1788)任福州將軍,乾隆六十年(1795)十月接替覺羅長麟署閩浙總督,嘉慶元年(1796)實授閩浙總督。參見《清史稿》卷362《魁倫傳》。會同前撫臣費淳③費淳(1739—1811),浙江錢塘(今杭州)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進士,歷任江蘇巡撫、福建巡撫,嘉慶四年(1799)任兩江總督。參見《清史稿》卷350《費淳傳》。奏準,召募商船諳練船工,駕輕就熟,奮勉追捕。
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福建海防重在兵丁及船舶的配置,對于船舶形制大小以及掌舵船工技術是否熟練這些海船的根本問題未能有效掌握。而在造船技術不斷進步的背景下,兵船火力大小以及航速等正是海戰勝負的關鍵,此時閩省水師的兵船已不能與商船比擬,由此可見其船只更新落后之一斑。閩浙總督玉德(?—1808)④玉德,瓜爾佳氏,滿洲正紅旗人。歷任湖南衡州知府、岳常澧道、山東濟東泰武道、山東按察使、安徽按察使等職。乾隆六十年(1795)任山東巡撫,嘉慶元年(1796)任浙江巡撫,嘉慶四年(1799)十月開始署閩浙總督,嘉慶五年(1800)正月實授轉正,嘉慶六年(1801)又署福州將軍。玉德在閩任職期間,適逢海盜蔡牽勢力最為猖狂的時期,其綜理閩政,對事件的蔓延責無旁貸。玉德的傳記,參見《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卷188《疆臣》。就曾描述當時的船況上奏曰:“查(乾隆)六十年以前緝匪兵船,大號名曰繒船,長八丈,闊二丈二尺,船身高大,式甚壯觀。因水師鎮將稟稱繒船船身高大,駕駛笨重,盜匪船小快捷,緝捕不能得力。”⑤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11 冊,嘉慶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740 頁。括號內文字,為依前后文意所加,下同。
汪志伊在《議海口情形疏》也對添設重兵提出他的看法,認為添設汛兵還不如就近招募沿海鄉勇來得好用,更可以看出其在福建實際任官的經驗:
又有議請于海口添設重兵者。查海岸綿長,十里設汛,五里安塘,每汛約添丁十名,合計非萬余人不可。皇上綏靖海疆,固不惜此經費,然必事歸有濟,方使帑不虛糜。今沿海既不可步步為營,而每汛添兵不過十余名而止,顧此失彼,何當實用。……蓋沿海村莊以海為田,人自為守,一有盜船臨境,則岸民千百為群,農具皆成兵器,是鄉勇已倍于盜匪,亦大有助于官兵。且各汛設有防海大小炮位,以高臨下,以逸待勞,一炮可當千軍之勇,洋盜不敢近岸者以此。所有各口岸,似無庸添設重兵。至水師長技,除駛船、推舵、轉篷、折戧、扒桅、泅水、對施槍炮、往來攻擊外,其制勝者尤在奪上風,放風箭以燒篷,擲火牌以轟船,射舵工以窮駕馭。閩省弁兵,從前未免因生疏而怯懦,甚至暈船嘔吐,數年來緝捕洋匪,拔弁于老漁,簡兵于海戶,配定舟師,頻年在海涉歷風濤,獲犯頗多,技藝日臻嫻熟。
汪志伊以實際經驗指出,當時的水戰技巧重在“駛船、推舵、轉篷、折戧、扒桅、泅水、對施槍炮、往來攻擊”,“制勝者尤在奪上風,放風箭以燒篷,擲火牌以轟船,射舵工以窮駕馭”,因此招募沿海熟練掌舵的船工等鄉勇,“拔弁于老漁,簡兵于海戶,配定舟師”,經過實際施行,確實是可行的辦法。
在《議海口情形疏》中,也點出當時面臨的“夷盜”與以往遭遇的“土盜”之不同,可以看出汪志伊在福建省長期為官的敏銳觀察:
至若洋匪,從前不過土盜出沒。自乾隆五十八、九年間,安南夷匪,膽敢竄入,互相勾結,土盜藉夷匪為聲援,夷匪以土盜為爪牙,沿海肆劫,擄人勒贖。若非搶掠商船食米及串通貪利之漁戶、行戶運米而出,易贓而回,并接濟淡水,資送火藥、炮械等項,安能久留洋面為匪。……臣復核盜匪情形,近數年頗有不同者,治土盜易,治夷盜難。蓋土盜不過一二桀驁,掠商漁而乘其船,脅其人漸成黨羽,計一船之真盜無幾,余皆被擄耳。被擄者未嘗不恨盜,亦未嘗不思歸。以兵攻盜,兼可以盜攻盜。廣開脅從之生路,重懸購盜之賞格,并將捕盜所獲之贓,給與擒盜來獻之人,以歆動盜伙,離間盜心,使相疑忌。自是土盜聞風陸續投首,剿撫兼施,當無難清理。而夷盜則不然,夏初乘南風而來,秋末乘北風而返,并無投首之心。尤可惡者,船大而高,炮多而壯,匪恃商船不敢抗衡,即官兵戰船,形勢限于仰攻,槍炮窘于逆擊,較治土盜稍覺其難。然夷盜之蹤跡在洋,其食用未嘗不需于陸。臣惟有力加整頓,嚴飭沿海地方官認真絕行戶之透漏,嚴飭各守口員弁實力清漁船之夾帶,務使賊贓無人代消,食米、火藥無人接濟,以窮其術而困其力。仍一面選精銳之舟師,鼓勇敢之戰士,相機掩擊,以殲其魁,而除其黨。則洋面自可日漸肅清,而生民之生計仍無妨礙矣。
汪志伊已經察覺到時代已經有所不同了,“夷匪”不僅與“土盜”有差異,造船技術使得“船大而高”,制炮技術也使得“炮多而壯”,以當時海防水師官兵配置的戰船規模,已經很難壓制這些橫行于洋面的海盜,將會造成“形勢限于仰攻,槍炮窘于逆擊”的不利局面。①水師提督李長庚在與蔡牽船幫作戰時,就有“提督所坐之船,為通幫最大,及并攏蔡逆之船,尚低至五、六尺,是以不能上船擒捕”的感嘆。參見《嘉慶實錄》嘉慶十一年八月三十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11 冊,嘉慶十一年八月三十日。汪志伊進而提出,不僅要嚴格執行堅壁清野的保守作法,“嚴飭沿海地方官認真絕行戶之透漏,嚴飭各守口員弁實力清漁船之夾帶,務使賊贓無人代消,食米、火藥無人接濟,以窮其術而困其力”,而且要以積極的方式,“選精銳之舟師,鼓勇敢之戰士,相機掩擊,以殲其魁,而除其黨”。
三、對蔡牽事件的檢討
清朝嘉慶年間最嚴重的海防問題,就是海盜蔡牽侵擾事件,其持續時間之久、蔓延之廣,著實考驗著閩浙沿海的防務體系。從前節的整理可以看出,以當時福建的海防兵力顯然不足以應付廣闊的福建洋面,特別在海盜蔡牽侵擾期間,問題更被凸顯出來。蔡牽侵擾臺灣,朝野緊張,各式上奏及諭示頻繁往來于京城與福建之間,滿朝文武都為此絞盡腦汁思考解決問題的辦法。
從福建水師提督李南馨(?—1801)①李南馨,廣東嘉應州長樂縣(今廣東省五華縣)人。乾隆三十五年(1770)庚寅武科進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任福建銅山營參將,乾隆五十五年(1790)任福建澎湖水師副將,嘉慶二年(1797)任金門鎮總兵,嘉慶四年(1799)任福建水師提督,嘉慶六年(1801)因病死于任內。參見《五華縣志·人物》,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640 頁。在嘉慶六年(1801)六月的奏折,不難看出蔡牽事件對福建水師的嚴重考驗:
伏查閩洋蔡牽等匪,南奔北竄,蹤跡靡定,現經派委海壇、金門二鎮總兵及閩安、烽火等營將領,統率舟(師),長年在洋往來偵捕,并不稍分畛域。即南澳、銅山鎮將及臺灣、澎湖兩協副將,亦俱帶領兵船,在洋堵緝。其余各營游擊、都司、守備,亦多隨同鎮將帶□緝匪。較之從前只在本境輪班巡哨,勞逸懸殊。②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己篇》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第693 頁。
只是騷擾事件一拖經年,閩粵浙地方官員不時發來斃匪多名的奏折,要求各級水軍將領晉升官階,且對陣亡官兵進行撫恤,然而海盜的侵擾還是持續蔓延。嘉慶十年(1805)五月,嘉慶皇帝訓斥福建水師提督李長庚③李長庚(1750—1807),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三甲第二名武進士,授藍翎侍衛。歷任浙江衢江營都司、提標左營游擊、太平營參將、樂清協副將、福建海壇鎮總兵(署)、海壇鎮標右營游擊、銅山營參將(署)、銅山營參將、澎湖水師副將(署)。嘉慶二年(1797)任澎湖水師協副將。翌年升任浙江定海鎮總兵,之后累功晉升至浙江水師提督,嘉慶六年(1801)九月任福建水師提督總統閩浙兩省水師。嘉慶十二年(1807)在與海盜蔡牽船戰中陣亡。謚忠毅,三等壯烈伯。李長庚的傳記資料相當豐富,有:《清史稿》卷357《李長庚傳》;[清]阮元:《揅經室·二集》卷4《壯烈伯李忠毅公傳》;《國朝先正事略》卷22《名臣·李忠毅公事略》等。近人論述可參見周維強:《靖海孤忠:浙江提督李長庚的海上生涯》,《淡江史學》第26 期,2014 年9 月。等幾位武官道:
粵東艇匪經李長庚等督率舟師追過南澳,擊沉盜船二只,傷斃執紅旗賊目一名、賊匪多名,該匪紛紛竄逸過粵,業據李長庚飭令鎮將帶領兵船在連界洋面巡防堵緝。此時艇匪既竄粵洋,閩省正可專注蔡逆,攻圍兜捕。現據奏稱,蔡逆匪船由淡水仍從東大洋竄回內地,蹤跡自必不逮。且據船戶報稱,蔡牽之妻因前在臺灣打仗,身受槍傷,瘡發身死,此亦一好機會。聞蔡牽之妻素為主謀,該逆惟婦言是聽,今已身死,則內無助惡之人,該逆必心忙意亂,官兵正當乘其窮蹙之時,圍擒務獲。著玉德轉飭李長庚,并傳知許松年④許松年(1767—1827),本籍浙江瑞安,經由武舉加入溫州水師鎮標,后于嘉慶十年(1805)因海盜蔡牽騷擾臺灣,閩浙總督玉德奏請由許松年護理金門鎮總兵渡臺助剿。嘉慶十一年(1806)署臺灣鎮總兵,嘉慶十二年(1807)因功實授金門鎮總兵,道光元年(1821)調任福建水師提督。參見《清史稿》卷357《許松年傳》。、杜魁光⑤杜魁光(?—1807),江蘇阜寧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武舉出身,乾隆五十七年(1792)擢升福建營守備,嘉慶六年(1801)任福建閩安協副將,同年九月任南澳鎮總兵。參見《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卷301《將帥》41,第225 ~232 頁。、蔡安國⑥蔡安國,廣東潮州南澳廳人,行伍出身,乾隆六十年(1795)任廈門后營守備,嘉慶二年(1797)升廈門水師后營游擊,嘉慶七年(1802)任福建烽火門參將,嘉慶十三年(1808)任澎湖水師協副將。參見[清]周凱等纂修:(道光)《廈門志》,道光十九年玉屏書院刊本,第415、416 頁;[清]陳壽祺等修纂:(道光)《福建通志》卷120,第683 頁。等,將剿捕蔡牽一事責成伊等四人,如能齊心協力,將蔡逆克期弋獲,必當施以重恩,其或從前曾獲愆尤,亦可概予貰宥,設稍有怠玩稽延,則惟伊等四人是問。⑦《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10 冊,嘉慶十年五月十二日。
嘉慶皇帝面對蔡牽事件時,處理方式表現得非常開明,即使他不一定熟悉海戰,但是對臣下上奏建議的事項,多能坦然接受。嘉慶十年五月,閩浙總督玉德奏請添造大型戰船同安梭;數月后,時任臺灣鎮總兵官愛新泰(?—1807)①愛新泰,伊爾根覺羅氏,滿洲正白旗人。嘉慶四年(1799)任臺灣總兵官,主要職責就是對付蔡牽集團,雖未能將其殲滅,但也可以說是克盡職責,有為有守。嘉慶十二年(1807)十月,因積勞成疾,病亡于艋舺(在今臺北市)軍營,謚壯勇。參見《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卷302《將帥》42。也上折表達了添造同安梭一事的急迫:
臣等伏思,臺灣地方孤懸海外,水師兵力本單,自上年四月以來,該逆肆次竄赴臺洋,希圖伺劫,雖經官兵擊退,而賊蹤無定,難保其不倏去倏來,殊為可恨。誠如圣諭,蔡逆一日不擒,則海洋一日不靖。本年五月內,閩浙總督玉德奏,請添造同安大號梭船三十只,與該營兵船聯為一幫,以資戰守。欽奉諭旨,業已如所請行。②《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10 冊,嘉慶十年十月二十九,第668 頁。
從一年后嘉慶帝頒發的上諭中可以看出,其對這件事的積極態度:
大同安梭船原為緝捕洋匪之用,蔡逆雖較前窮蹙,而官兵追剿洋匪所需大船必當妥為趕造,以資駕駛,為沖涉風濤之備。既據該撫查明現在情形,所需大同安梭船但得四十號即可敷用,著溫承惠③溫承惠(1754—1832),山西太谷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拔貢出身,嘉慶十一年(1806)二月任福建巡撫,五月署閩浙總督。參見《清史稿》卷365《溫承惠傳》。督飭廠員如式趕辦四十號,并即勒限造竣,務期工堅料實,方可得力,不得藉詞于大船購料艱難,稍有推遲。④《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11 冊,嘉慶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第749 頁。
添造同安梭戰船,是嘉慶朝為解決水師戰船比海盜船只矮小的主要處理方式。根據道光《福建通志》卷84《國朝船政》的記載,同安梭戰船規模有三個型號:一號,船身長七丈二尺(約22 米),寬一丈九尺;二號,船身長六丈四尺,寬一丈六尺五寸;三號,船身長五丈九尺,寬一丈五尺五寸。⑤嘉慶十年(1805)議準臺灣水師兵船單微,添造同安梭30 只,編為“善”字號,分設臺協三營管駕配緝。參見[清]陳壽祺等修纂:(道光)《福建通志》卷84《國朝船政》,第35 ~38 頁。在當時來說,屬于較為大型的新式木造戰船。
在汪志伊于嘉慶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上呈的《奏報籌辦天津水師官兵船只情形折》附件《軍機處文件奏折錄副》中,有“一號同安梭船圖”,圖上標示著該船的各項規格:船身長七丈二尺,梁頭闊一丈九尺,大桅長七丈二尺,頭桅長五丈,尾桅長二丈二尺,配舵工水手40 名,配大小紅衣炮、重劈山等炮共14 門,以及藤牌、撻刀、竹篙槍等械若干。周維強補充說明一號同安梭船上的火力配置,稱一號同安梭船上擁有主炮6 門,其中1000 斤重紅衣炮(600 公斤)2 門、800 斤重紅衣炮(480 公斤)2 門、500 斤重炮(300 公斤)2 門,以及100 斤重劈山炮(60 公斤)4 門、80 斤重劈山炮(48 公斤)4 門,共14 門。⑥參見周維強:《“再現·同安船”紀錄片的歷史考察與科技呈現》〉,臺北《故宮文物月刊》第361 期,2013 年4 月,第104 ~105 頁。火力相當可觀。
嘉慶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嘉慶皇帝聽聞新造大船完工得以下海捕盜后,下諭道:
此次蔡逆匪船經李長庚督兵追至臺山外洋,大加攻擊,斃賊甚多,匪船隨向東南大洋折回奔竄,適省廠新造大船二十號完竣,隨經李長庚驗明換駕出洋并另挑米艇、同安梭船二十只,及另雇商船三十五只,經阿林保①阿林保(?—1809),舒穆祿氏,滿洲正白旗人,歷任山東鹽運使、湖南巡撫等職,嘉慶十一年(1806)五月接玉德任閩浙總督,其未到任前,由溫承惠暫署。嘉慶十四年(1809)七月調兩江總督,十一月卒于任。參見《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卷187《疆臣》39。交王得祿②王得祿(1770—1841),臺灣諸羅縣溝尾莊(今臺灣嘉義縣太保市)人,以武生身份招募義勇五百人,投身官軍參與對抗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起義,嘉慶元年(1796)毅然改投水師,任福建水師銅山營參將李長庚麾下,嘉慶十年(1805)升署澎湖水師協標左營副將,嘉慶十一年(1806)任福建福寧鎮總兵,嘉慶十二年(1807)四月調補南澳鎮總兵。在該年十二月間,李長庚在追捕蔡牽于黑水外洋時,不幸中炮陣亡;廷議王得祿委署浙江水師提督,嘉慶十三年(1808)年正月改為實任,六月改調福建水師提督。嘉慶十四年(1809)八月,王得祿與浙江水師提督邱良功合力圍堵蔡牽于黑水深洋,迫其毀船自沉,敘功著加王得祿晉封二等子爵(正一品秩),賞戴雙眼花翎。關于王得祿的傳記資料相當豐富,有:《清史稿》卷357《王得祿傳》;[清]姚瑩:《皇清誥授振威將軍太子太保原任浙江水陸提督二等子爵世襲賞戴雙眼花翎晉加太子太師贈伯爵賜祭葬予謚果毅顯考玉峰府君行述》,《臺南文化》第5 卷第3 期,1956 年,第174 ~175 頁。近人論述可參見徐明德:《清代水師名將王得祿傳略與年譜》,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1 年;蔡相煇、王文裕:《王得祿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年;顏尚文、潘是輝:《王得祿宗教信仰行跡之研究》,《嘉義研究——王得祿專輯》,嘉義: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8 年。、許松年統帶歸幫,隨同李長庚協力攻捕。此項新船高大堅固,正資適用,且炮械齊全,兵力厚集,李長庚務當督同鎮將等倍矢奮勉,乘蔡逆窮蹙之時,上緊躡剿,速獲兇渠。③《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11 冊,嘉慶十年十二月十七日,第974 ~975 頁。
對于閩浙總督玉德再次建議將陸路官兵抽撥500 人改為水師一事,嘉慶皇帝則傾向汪志伊在《議海口情形疏》中的意見,認為遠道添加兵員還不如就近招募沿海鄉勇:
惟所稱臺灣水師兵共二千五百八十六名,今添造兵船不敷配用,請將陸路兵內抽撥五百名改為水師一節,此則不可。陸路營伍亦有巡防緝捕之責,何得率爾抽撥,況以不諳水師之兵,調往充數,徒歸無益。臺灣海疆要地,即添設勁旅數百亦不為多,著玉德飭知臺灣鎮道就近遴選召募,亦可不必拘定五百名之數,或即于該處團練之鄉勇義民中擇其熟悉水師趫健得力者二三百名挑入水師營伍,責成該將弁等勤加操練,既可以資得力,而游手無籍之徒得以隸名營伍養贍身家,自可不致流為匪類,于地方亦有裨益,其應行支給錢糧,及如何分隸各營,定立巡防堵御章程,并著玉德飭交愛新泰等詳籌妥議。④《臺灣總兵愛新泰奏折(移會抄件)》,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上冊,第1056 ~1060 頁。此折最末記有“嘉慶十年十月初五日奉朱批,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顯示嘉慶皇帝已經看過,再交由軍機大臣會商處理。
從添造同安梭新船與以招募沿海熟悉水性的鄉勇取代陸路營伍改撥水師等事,可以看出嘉慶皇帝處理政事的睿智,但這些事情畢竟還是細枝末節,對于整體海防的大方向,嘉慶皇帝似乎囿于歷史局限,始終沒能給出大方向的宏圖遠見。
對于臺灣鎮總兵愛新泰嘉慶十年(1805)十月的這件奏折,《嘉慶道光兩朝上論檔》中尚留有后續處理的紀錄。此折開頭為“臣慶等謹奏,為遵旨會議具奏事”,具奏人是領班軍機大臣慶桂(1737—1816)⑤慶桂(1737—1816),章佳氏,滿洲鑲黃旗人,大學士尹繼善子,以蔭生授戶部員外郎,充軍機章京,超擢內閣學士,乾隆三十六年(1771)授軍機大臣,乾隆四十九年(1784)任福州將軍,嘉慶四年(1799)授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復直軍機。參見《清史稿》卷348《慶桂傳》。,就“等謹奏”“會議具奏事”等詞來看,這似乎不是慶桂個人的意見,應該是軍機大臣們會商之后共同擬具的上奏意見。因此,此奏折中的意見可以看作是當時朝廷大臣們的普遍共識。
軍機大臣們在會商之后,就建造新船同安梭后添募水師兵源一事,進行了更廣泛的討論。在“請添募水師兵丁,以資配船緝捕”一項,就提出:
查臺灣各營額設水師兵二千伍百七十名,除派防各汛及看守軍裝等項之外,總計存營及新募水師兵實止一千五百二十四名,現在新造大號同安船三十只,及臺營中號船十只、小號船十只,以五十只兵船計算,大號船每只需配舵手、戰兵七十名,中號船需配六十名,小號船需配五十名,總共需水師兵三千二百名,實不敷一千六百七十六名。此時若令全數召募,不但糜帑太多,一時亦未必有如許熟習水師之人,倘徒行充數,亦屬無益,自應先將水師實存出汛弁兵八百三十余名全行調回配船,酌撥就近陸營弁兵代為防守。至此外尚不敷水師兵八百四十余名,應令添募足數,請仍飭該總兵等欽遵前奉諭旨,在于本地團練鄉民內詳慎遴選,加意訓練,以收實效。其應給糧餉、器械以及陸營汛兵如何酌撥代防,均宜詳細再令核明具題,咨部辦理。統俟蔡逆就擒,海洋平靜,再行酌量裁減,以符原制。①《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10 冊,嘉慶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第669 頁。
大臣們的意見,還是先將水師官兵充分使用。經過仔細計算新造大小同安梭船數目和配載兵員人數,共計需要水師兵3200 名,當時臺灣各營編制水師兵不過2570 名而已。如果臨時添募新兵,雖然存在新增薪餉籌措的困難,但是能不能招募到熟習水師的可用之兵,才是更為關鍵的問題。所以大臣們建議,先將本來要防守汛塘要地的水師官兵登船使用,防守汛塘的任務暫時交由陸營官兵來接力協防,不足之數再用添募沿海熟悉水性的團練鄉民來補足。但大臣們也都知道,這實在不是長久之計,所以也明說等待海洋平靖了,再慢慢回復到原有編制。這實際上是一種因應沿海海寇侵擾的臨時性的保守可行辦法。
大臣們需要作更進一步的考慮,即水師兵員招募后,用來管理這些新募水兵的下級軍官配備問題。于是,大臣們對這一問題作了一番指示:
查兵船配載必需管帶之員,臺灣水師自副將以至額外外委共祗五十六員名,不敷差撥,該鎮請添設額外外委十名,以資管駕差委,事屬可行。應責令該總兵,于向曾出洋水師兵內秉公遴選,將熟習風云沙線、奮勉出力者咨部拔補,無許濫行充數。但臣等又思,額外外委分祗微末,不過管駕一艇,該處現添大號兵船三十只、水師兵丁一千一百余名,當聯幫緝捕之時,此外將佐是否足敷管轄鈐制,或應暫時增撥千總、把總數員前往督率之處,并請敕交閩浙總督率同該鎮酌量情形奏明辦理。②《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10 冊,嘉慶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第670 頁。
大臣們比較同意臺灣鎮總兵愛新泰增添十名額外水師下級軍官的辦法,但指示要先從曾經有登船出洋經驗的水師兵員中公平遴選,把熟悉沿海當地氣候水文地形而且勤奮負責的兵員先行升任。同時,又考慮到額外下級軍官畢竟職銜較低,是否足以管帶船只出洋捕盜的問題。經過統計,大船需要舵工、水手以及戰兵70 名,中船需要60 名,小船也需要50 名,遂指示閩浙總督與臺灣鎮總兵應撥派有經驗的千總、把總先行充任。
關于新增加薪資開支的處理辦法,大臣們也給予指示建議:
查弁兵出洋捕盜,經旬累月,不能不計及行糧,且沖涉風濤,履危涉險,尤應加以體恤。上(九)年蔡逆竄劫臺洋時,該鎮等因兵丁所需口糧無款可動,于府庫官莊項下暫行挪支,并因不能報銷,即于總兵及各營將備弁兵廉餉銀內攤派歸還,本非正辦。此時添設兵船,自應熟籌經費,以資口糧。查乾隆六十年該省酌改營船,前任閩浙總督長麟奏,請于藩庫撥銀二十萬兩,發商行息,每年取息銀二萬四千兩,以為出洋弁兵口糧及燂洗船只、修理篷纜之用,經戶部議準在案。今該鎮請于司庫撥銀十萬兩,發交臺灣,給商生息,以每年所得息銀一萬二千兩應付口糧,應如所請,準照乾隆六十年發商生息之案,以應支給。仍令該督、撫將動用司庫何款先行報部,年終即將出洋弁兵人數、日期并給過銀兩一并核實造冊,報部核銷。俟洋面肅清,即將本銀撤回,繳還本款。①《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10 冊,嘉慶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第671 頁。
蔡牽侵擾沿海數次,官兵經年巡捕,竟導致臺灣兵餉出現問題。之前臺灣鎮的處理方法是先將“官莊”②清代臺灣在收復臺灣初期即已出現官莊,其來源有承襲自鄭氏集團的產業、文武官員占有、官府投資招墾以及因案充公等。官莊的收入則由政府胥役或委托佃首征收,需列入正式的收入而受到稽核,收入大多用于支放餉銀或養廉銀等。參見李祖基:《清代臺灣官莊的研究》,《臺灣史研究》,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8 年,第256 ~279 頁;涂明志:《清代臺灣官莊研究》,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收入暫行挪支使用,但因與規定不合,事后竟無法報銷,只能運用臺灣總兵以及各營將備弁兵的養廉銀③養廉銀是雍正元年(1723)為防止官員薪資普遍不敷生活所需,便想方設法徇私貪污而設。“因官吏貪贓時有所聞,特設此名;欲其顧名思義,勉為廉吏也”。視各地富庶與否,養廉銀數額也有所差異,但一般說來,養廉銀通常為本薪的十倍到百倍不等。臺灣總兵的年俸大約為67 兩銀,軍事加給約144 兩銀,而養廉銀則竟有1500 兩銀之多。參見[美]曾小萍:《州縣官的銀兩——18 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董建中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年;[日]佐伯富:《清雍正朝的養廉銀研究》,鄭梁生譯,臺北:商務印書館,1996 年。來勻支攤還,這讓臺灣鎮的官兵們相當苦惱,更嚴重影響水師將官的軍心士氣。于是臺灣鎮總兵愛新泰想到乾隆年間處理林爽文事件的前例,要朝廷商借十萬兩,貸與商人們藉此收取利息,預計一年能得到一萬二千兩的利息收入,以此來支應水師官兵出洋捕盜以及修理船只等軍費支出。朝廷商議也基本認為這有前例可循,而且也是便宜可行的好辦法。
接下來,是愛新泰反映的臺灣千總、把總三年俸滿更調內渡的班兵問題。軍機大臣們認為班兵制度有著“既不致與本地游民日久相習,且使福建通省水陸標弁更番輪往,于臺灣水陸情形人人熟悉,風濤險阻習慣周知,更為有備無患”的深遠意義,不能偏廢,就給出了折衷的意見:
查臺灣一郡孤懸海外,番夷錯處,民俗強悍,從前設兵鎮守時,定制千總、把總三年俸滿均令更調內渡,誠以微員去留定有年限,既不致與本地游民日久相習,且使福建通省水陸標弁更番輪往,于臺灣水陸情形人人熟悉,風濤險阻習慣周知,更為有備無患,立法自有深意。此時若將千、把俸滿更調之例概行停止,誠恐行之日久,只有駐臺員弁熟習本地情形,其余各員轉不能均諳洋面風濤、臺澎形勢,何以資練習而裕巡防。惟此時緝捕緊要,該鎮因欲資熟手起見,臣等詳加酌議,除陸路千、把換班之處,應悉遵照舊例,無庸輕議更張外,其水師千總、把總內,可否飭令該總兵于三年俸滿應行更換時,詳慎區別,其中如有實在熟習水道而又奮勇出力、曾經著有勞績者,準其指名保奏,暫留數員,遇有守備、千總缺出,分別考驗題補,不得過拾分之三、四,仍照新疆員弁換班之例,一俟該處有熟手可以接辦,即將各該員咨送總督,在于內地相當之缺遴選調補。統俟海洋寧謐,仍即查照舊例辦理。④《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10 冊,嘉慶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第672 頁。
軍機大臣們雖然認為以此兵馬倥傯之際,將熟悉臺灣水路情形的官弁按時替換,實非良策,陸路千總、把總的三年換班之例應照樣施行,但是水師千總、把總如果有實在熟習水道而又奮勇出力、曾經著有勞績者,亦準許臺灣鎮總兵指名保奏,以暫時留用數員。
四、結論
蔡牽等騷擾閩浙沿海十數年,是清朝嘉慶時期的海防要事。靜謐已久的東南海疆,亂事蜂起,成為當時朝野關心矚目的焦點所在。關心國事的有識之士,紛紛提出建言議論,其中以福建巡撫汪志伊的《議海口情形疏》最具代表性。他以實際在閩任官的經驗認為,當時福建海防的配置區域尚屬合宜,兵力分布也算得當,不過問題重點出在“船身笨重”與“舵工兵丁”兩項上,并提出反對再添設重兵,轉而就近招募沿海鄉勇加入水軍以及勿使沿海居民接濟海盜的想法,這在當時來看都是切合實際的重要議論。然觀其《議海口情形疏》依然囿于傳統官府“捕盜”的保守觀念,在即將到來的19 世紀新時代的海防變局面前,明顯存在不足。
嘉慶皇帝在面對蔡牽事件時,處置的手法尚屬高明。對于船只的改良,其堅持添造同安梭新型大號戰船,也認同接受汪志伊在《議海口情形疏》中招募沿海熟悉水性的鄉勇取代陸路營伍改撥水師等建議,從中可以看出其處理政事大局的能力。但是,這些決策畢竟都屬于微末之事,而對于國家海防整體建設的大方向,嘉慶皇帝始終沒能給出較為遠大的宏圖考慮。
在前線實際帶兵打仗的臺灣鎮總兵愛新泰,也曾提出面臨的實際困難和問題:一是新船造好以后,需要增加的水師兵丁從何而來?二是兵丁補充足額后,管兵帶船的基層軍官從何而來?三是官兵配備齊全后,需要增加的薪餉從何而來?還有制度性的臺灣班兵問題等。這些都是當時緝捕海盜面臨的實際問題。當然,這些問題經過嘉慶皇帝交由軍機大臣會商討論后,都形成了一套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這也是讓嘉慶朝廷得以再度平定東南海疆的關鍵所在。
本文藉由鴉片戰爭之前清代嘉慶朝對于海防的諸多議論,采用微觀歷史學(Micro History)厚敘述(Thick Description)的方式,鋪敘嘉慶朝文武官員對于海盜侵擾東南海疆的諸多看法,從中可以看到海疆防御所面臨的諸多細微問題,如兵員、船只、舵工、薪餉,乃至整體的國家大政等,同時也可以看到在當時社會經濟文化背景下人們所受到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