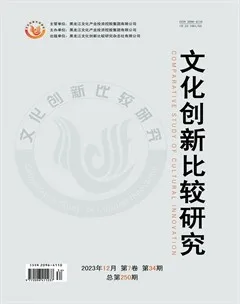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類型與提升路徑研究
王蘭,楊蔚
(茅臺學院,貴州仁懷 564500)
伴隨著全球化浪潮席卷而來, 國際間交流日益頻繁。 不同國度與文化背景的人們的溝通聯系日趨緊密。提升跨文化交際能力,增強文化自信成為我國當前適應全球化形勢下的突出矛盾。《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 年)》指出,要“培養大批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能夠參與國際事務和國際競爭的國際化人才”。 在“第四屆全國高校外語教育改革與發展高層論壇”上,教育部吳巖司長強調,“高等外語教育要全面融入高等教育強國建設,大力培養具有全球視野、通曉國際規則、熟練運用外語、 精通中外談判和溝通的高素質國際化人才”。 由此可見,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離不開國際化人才的培養, 而跨文化交際能力是國際化人才必須擁有的素質, 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就成了高校外語教育的一項重要任務。
1 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定義
學界有關跨文化交際的研究較早, 最早可追溯到20 世紀50 年代的美國,美國民事局的《跨文化研究備忘錄》中首次提到“跨文化交際”一詞,并以“有效性”為中心進行跨文化能力理論建構。跨文化交際學的奠基人愛德華·霍爾(Edward Hall)在其專著《無聲的語言》中指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使用時間、空間表達意義方面表現出明顯的差異(對時間、空間、交際的關系作了深入探討)。 1983 年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Current perspectives(ICC)的出版意味著跨文化交際的研究進入成熟階段。 國外關于跨文化交際的研究較為成熟,Triandis 認為跨文化能力的高低取決于3 個因素, 分別為獲取信息的認知、 使用信息的認知和與其他文化相關的知識。 因此,跨文化能力需要在了解文化知識的基礎上,運用信息的認知正確破譯新信息。Ruben 認為,文化與文化之間存在差異性,文化差異性越大,對個體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更是提出考驗, 個人在兩種文化進行轉化表達的過程中就越容易出錯。 個體則是通過不斷了解對方的文化以彌補兩種文化之間的鴻溝。因此,Ruben 眼中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實際上是個體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正確表達和翻譯的能力。 Alred 和Byram 則認為, 跨文化交際能力是一種適應其他文化的過程,這一過程伴隨著改變自身原有的知識、調試自身的態度和行為,最終達到適應其他文化的能力[1-4]。
跨文化交際能力研究的產生是基于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由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改革開放這階段與國外的交流相對有限, 使得我國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相關研究起步晚。經查閱相關文獻發現,我國較早開始進行跨文化交際研究的是20 世紀80 年代的外語教學,王躍漢提出在外語教學中,不能滿足于現有詞匯記憶和重復性訓練, 而要了解對方國家的文化,要在教學中引入跨文化交際的意識,著重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5]。胡文仲提出外語教學的跨文化交際要注重研究詞匯的文化內涵, 語用規則和語用順序等,以此了解不同詞匯文化內涵、語用規則及順序下所隱含的不同文化, 所以這里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注重強調了解對方國家文化的能力[6]。 進入21世紀,我國對外交流溝通增多,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研究逐漸從側重于跨文化能力的培養轉變到跨文化能力和交際能力并重上來。 張曉暉強調了跨文化交際能力對于高等教育中英語教學的重要性, 認為跨文化交際能力是指不同文化背景信息發出者和接受者之間進行正確、有效的交流和溝通的能力。這里不僅強調了跨文化交際能力中的跨文化能力的培養,還提高了跨文化交際能力中交際的重要性[7]。
由此可知,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的研究,都承認跨文化交際能力的跨文化性和交際性, 跨文化能力熟知語境下兩種或多種不同的文化, 恰當地解碼并予以轉換的能力。 交際能力即熟知目的語的語言技巧恰當地予以表達。 跨文化交際能力實際上是跨文化能力和交際能力的組合, 即指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有效、恰當交往的能力[8]。
2 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分類
學界對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分類主要基于對跨文化交際能力定義的操作化而得出, 即根據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定義進行操作化為不同的指標和要素。 趙愛國、姜雅明把跨文化交際能力概括為語言能力、語用能力和行為能力[9]。賈玉新將其分為基本交際能力系統、情感和關系能力系統、情節能力系統和交際方略系統[10]。 楊盈、莊恩平將其分為全球意識、文化調適、知識、交際實踐4 個系統[11]。 胡文仲將跨文化交際能力簡化為知識、動機和技能三部分,要求交際者同時具備意識、思想和活動層面的能力。學術界對跨文化交際類型的研究較為深入, 出現了較多有深度的研究成果[12]。 大致勾勒了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基本框架,并從微觀角度,即教學中改善教學方法以提升跨文化交際能力。但從宏觀角度看,根據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兩個基本屬性, 即跨文化能力和交際能力上分析跨文化交際能力類型的研究尚不多見。 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跨文化交際能力研究的深度發展。 筆者根據跨文化交際的兩大屬性“跨文化能力”與“交際能力”進行2×2 矩陣分類,將跨文化交際的類型劃分為小白型、 興趣型、 現實型和明星型4 類 (見圖1),并據此模型,探討其所蘊含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提升模式。 以期為跨文化交際能力提升提供新思路和方向性指導。

圖1 跨文化交際能力類型劃分
2.1 小白型
該類型主要指跨文化能力與交際能力均低的狀況。該群體往往對目的語國家的語言用法不了解,詞匯量積累少、語法等相關語言知識運用能力較強,加之缺乏跨文化意識, 缺乏直接閱讀目的語相關文獻資料的能力,僅能接觸相應的翻譯文本,或通過其他媒介了解目的語文化, 相應的了解渠道和范圍較為有限,導致其跨文化能力減弱,形成跨文化交際能力類型的小白型。同時,該類型也可能是興趣型和現實型互相轉化的結果, 當興趣型和現實型缺乏實際應用的“場域”。隨著時間的推移,其跨文化能力或交際能力逐漸減弱, 最終導致跨文化交際能力類型小白型的出現。
2.2 興趣型
該類型指跨文化能力高、 交際能力程度低的狀況。 該群體表現為對目的語國家文化有著較為濃厚的興趣。 通過閱讀目的語文本或通過其他媒介熟悉目的語國家文化,但由于目的語語言技能知識不高、自身忽視了目的語的學習,導致其跨文化能力高,交際能力低的興趣型。此外,該種類型還可能是由小白型轉化的結果。 這種情況往往屬于小白型群體,受“偶然”因素作用,對目的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或是出于現實需要,需要了解目的語國家的文化知識,但是其認為交際能力的提升 “沒有必要” 或提升過程“不同步”,其交際能力仍然保持較低水平,從而促進了小白型向興趣型的轉變。
2.3 現實型
該類型主要指跨文化能力低、 交際能力程度高的狀況。該類型表現為語言功底較好,積累大量目的語詞匯,相關語句用法較為熟悉,但是對目的語國家的文化缺乏了解的類型。 該類型常見于高中生或以應試為導向的學生。 該群體在經歷密集測試或備考后,詞匯量和語法知識達到較高水平,但由于絕大部分時間集中于應試,缺乏跨文化意識,導致跨文化交際能力較低。 同時,與興趣型類似,此種類型存在由小白型轉化的結果。 與小白型向興趣型轉化不同的是,這種情況往往不是基于興趣,更多基于自身現實利益的考量,從而促使小白型群體向現實型轉變。
2.4 明星型
該類型主要指跨文化能力高、 交際能力程度也比較高的狀況。明星型是較理想的類型,也是跨文化交際能力提升的終極目標。 該類型由跨文化交際能力興趣型和現實型經由以下兩種途徑發展轉化而來。第一種途徑,興趣型通過閱讀翻譯文獻熟悉目的語國家的文化, 通過努力不斷積累目的語語言知識和實際應用,其交際能力得到提升,進而完成興趣型向著明星型轉變。第二種途徑,現實型的語言功底較好, 通過閱讀目的語文本或翻譯目的語從而了解目的語國家文化, 并在實際運用場景中不斷練習兩種文化之間解碼轉化能力,跨文化能力得到提高,從而完成從現實型向明星型的轉變。
3 跨文化交際能力提升的多元架構及提升機制
3.1 跨文化交際能力提升的多元架構
對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基本屬性即“跨文化能力”和“交際能力”進行分類,是本文進一步深入探討跨文化交際能力提升的基礎。近年來,國內關于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研究尚未形成具有中國文化特點并經實踐檢驗的理論,在跨文化交際能力提升研究上,主要集中在微觀層面的大學英語課堂上, 如提出“ESA”課堂教學方法;課堂教學新途徑,利用網絡和多媒體教學有意識地開展跨文化培訓法; 構建創新性課堂教學模式,如產出型語言文化融合式教學模式等(索格飛、遲若冰,2018 年)。 不可否認,當下課堂教學依然是跨文化交際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徑。 但是隨著信息時代的發展,學習途徑逐漸多元化,個人自學已成為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重要途徑。同時,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提升本質是個人習得的過程, 所以個人自覺學習在跨文化交際能力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所以本文提出跨文化交際能力提升的二元治理機制,即課堂主導、個人自覺。
3.2 跨文化交際能力提升的基本模式
在之前的討論中, 提到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的研究,都承認跨文化交際能力的跨文化性和交際性,即跨文化交際能力是由“跨文化能力”和“交際能力”組成的。由此,跨文化交際能力提升的最終目的是達到“跨文化能力”與“交際能力”的雙升——明星型。根據圖2 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提升路徑,可以發現,跨文化交際類型完成從小白型到明星型的轉變, 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提升主體(課堂主導,個人自覺)可以由以下4 種路徑完成。

圖2 跨文化交際能力提升路徑示意圖
3.2.1 興趣優先模式(小白型→興趣型→明星型)
跨文化交際能力提升主體采取先提升跨文化能力的方式,促使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小白型”由路徑①逐步轉變為“興趣型”,然后再通過積累目的語的詞匯量和學習語法等提升交際能力, 經過路徑⑤完成跨文化交際能力由“興趣型”向“明星型”的轉化。3.2.2 現實導向模式(小白型→現實型→明星型)
這種模式指跨文化交際能力提升主體采取先提升交際能力的方式, 促使跨文化交際能力的 “小白型”由路徑④轉變為“現實型”,再通過閱讀及其他媒介了解目的語國家的文化和用語習慣, 提升其跨文化能力經由路徑③使跨文化交際能力完成“現實型”向“明星型”轉化。 由于跨文化交際能力中以剛剛畢業的高中生和應試為導向的學生為主,“現實型”主題濃厚, 因此大學教育要通過課堂講解目的語國家的文化,激發大學生對目的語國家的興趣。再加上個人自覺學習與反復實踐深化認識, 從而促使 “現實型”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提升。
3.2.3 “鐘擺”模式 (小白型→興趣型→←現實型→明星型)
這種模式并不局限于先提升 “跨文化能力”或“交際能力”。而是基于一種現實的思維,采用實用主義的態度去進行相應的提升, 最終達到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明星型”。 當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兩大主體基于現實的考慮決定是先改善兩種能力的一種, 則選擇相應的策略去提升。 當提升主體認為 “跨文化能力”成為其主要矛盾時,則通過閱讀目的語國家的相關文獻或通過其他媒介了解目的語國家的文化進而提升。反之,“交際能力”成主要矛盾時,則提升其“交際能力”,這就形成提升策略反復調整,成為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鐘擺”模式。
3.2.4 興趣現實并重模式 (小白型→明星型)
該種模式提倡“跨文化能力”和“交際能力”同步提升,這是一種較為理想的模式(見圖1)。 使得跨文化交際能力“小白型”通過路徑⑥直接發展成“明星型”。這種類型往往在“興趣”和“現實”雙重動因下產生的結果。 如在高中期間英語課堂上學習 “交際能力”,課下通過自覺學習通過閱讀英語文獻,了解目的語的文化,從而達到“交際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相對同步的提升。
4 結束語
綜上所述,4 種跨文化交際能力提升的4 種途徑是理想類型劃分的一種現象。 本文在建構模型中把“跨文化能力”和“交際能力”當成定類變量進行處理,對跨文化交際能力提升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在現實中, 受多重因素影響, 理想劃分不能完全體現。 現實中兩者卻是一個定序變量。 總而言之,本文簡單呈現了跨文化交際能力提升的基本宏觀策略框架, 以期為跨文化交際能力提升的路徑選擇提供思路或參考。 在具體實踐中,有更多復雜的因素影響,則需要進一步探討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