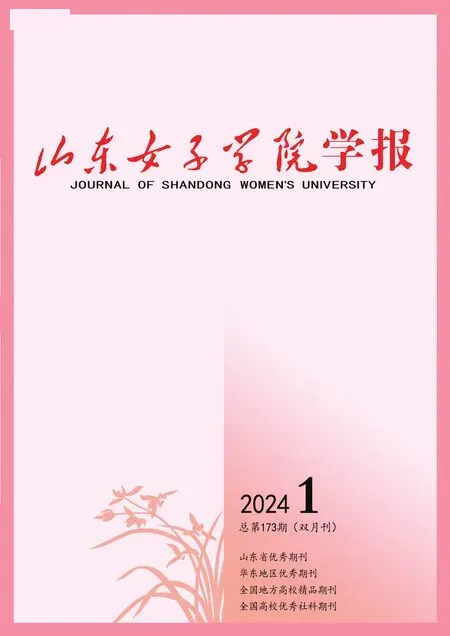女性主義視域下的武則天:成因、功績及局限
李 勇
(貴州大學 法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在父權制控制的封建社會,女性是從屬性的存在,她們的人格受貶低、發展遭到抑制。然而,當自由之光滲透進父權制的裂縫時,亦曾開出曠世奇葩——武則天。自20世紀中葉以來,我國有關武則天的研究非常豐富,但遺憾的是,既有研究中女性主義視角不足。早在20世紀90年代,便有人指出,“盡管曾有史學家、劇作家為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翻過案或塑造過‘矯枉過正’的武則天形象,但無論是學術界還是評論界,審視和評價武則天的依然是男性視角和雙重價值標準而缺乏女性意識”(1)陳怡:《“從女性視角重評武則天”討論會》,《婦女研究論叢》,1995年第4期。。如今,有關武則天的性別意識(2)參見辛瓏豆:《論武則天的女性意識》,《忻州師范學院學報》,2019年第6期。和武則天對同期女性的影響(3)參見畢秋生:《武則天與武則天時代的女性命運》,《菏澤學院學報》,2015年第6期。的研究雖然已經出現,但細致、系統、基于女性主義視角的研究仍然罕見。有鑒于此,本文旨在從女性主義理論和研究方法出發,闡釋促成武則天成為國家掌權者的關鍵性別因素、“共情倫理”指引下武則天給同時期女性帶來的福祉,以及在父權制和性別階級分化的交互作用下武則天作出的必要妥協。
一、武則天何以成為國家掌權者
關于武則天何以成為國家掌權者,或是認為武則天的出現只是孤立現象,并沒有明顯的前因后果;或是用宗教和迷信為武則天掌權附上神秘的色彩。實際上,對孤立性的強調和基于神秘主義的闡釋都不盡合理。武則天的出現既不是無跡可尋,亦非只能夠求教于宗教和迷信,而是多種因素耦合作用的結果。相對寬松的文化氛圍為武則天的出現提供了土壤;父母特殊的培養是孕育武則天的搖籃。袁天綱相面得出的“女主天下”之說,是父母改變對武則天的性別角色定位和武則天披荊斬棘登上皇位的助推劑。
(一)夾縫中的自由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也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開放性’社會。”(4)段塔麗:《唐代婦女地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頁。正是在這樣的社會中,女性的自我意識才會如此強烈,進而有條件孕育出武則天這樣“離經叛道”的女性。在武則天生長的唐初社會,“儒教的衰微、‘胡風’盛行等種種原因,使得唐朝形成了它特有的‘閨門不肅’、禮教不興的狀況”(5)高世瑜:《唐代婦女》,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就儒學而言這或許是劫難,對唐朝女性來說卻是莫大的幸運。這時,附加在女子身上的禁錮大為松弛,男性中心的道德觀被弱化,女性的社會地位得到提高,她們擁有了更多的自由。
封建禮法的相對松弛,從多方面改變了唐朝女性的生活。一是她們在婚姻家庭上獲得了更多自由。她們敢于追求愛情,貞操觀念相對淡薄。閨中女兒私結情好、已婚女性另尋伴侶之事多見,離婚、改嫁更是常態。二是社交活動增多。女性可以公開或單獨與異性交往,同席共飲、戲謔談笑,或書信往來、詩詞相贈。她們喜好“胡服騎射”“衣男子衣而靴”“露鬢馳騁”(6)(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24,長沙:岳麓書社,1997年版,第319頁。,經常參加打球、射獵等體育活動。三是貴婦干政蔚然成風。在處于鼎盛時期的百余年里,唐朝近半數時間是由貴族女性控制的。后妃干政在中國古代常見,但多出現在皇帝年幼或多病時,唐朝則非如此。唐時即便精明強干的君主在位,后妃輔政也常見,公主中亦出現了一批積極參政的女子。唐代宮廷女性求權之心熾盛,她們對權力的爭取似乎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歷史發展經驗的啟示是——時勢造英雄,偉大人物多是時代和環境共同造就的,女皇武則天的出現亦如此。在封建父權制牢固束縛的時代,女性處于集體沉默狀態。但這種沉默多是被迫的,當束縛她們的禮教有些許松動時,女性則迅速掙脫,甚至以一種求償的心態,奮力尋求曾失去的東西。在掙脫牢籠、尋求自由的女性中一般會出現少數突出者。她們在表現上與所處的社會格格不入,但實際上她們卻是時代和環境共同塑造的結果,對她們的闡釋需要融入大背景。就此,武則天的出現非偶然事件。“夫權的削弱、婦女在家國中地位的提高、男性士大夫寬容的性別觀念、‘牝雞司晨’政治禁忌的打破和女性貴族在政治中作用的增強,都為女皇的出現奠定了廣泛的社會基礎。”(7)張菁:《唐士大夫的女性觀與武則天現象的產生——以墓志為中心》,《江海學刊》,2011年第5期。由此形成的開放社會風氣為唐朝女性提供了難得的自由空間,亦在召喚武則天出場。
(二)父親男性化的培養
無論是基于父權制對女兒的管控,還是出于人性本能對女兒的愛,父親在女兒的生命歷程中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要搞清楚武則天何以具有超前的性別意識,破關斬將登上男性把持的皇帝寶座,不能忽視其父親武士彟的影響。武士彟原系山西木材富商,一生好學進取,政治上發跡于李淵起兵。武士彟突破商人的狹隘逐利本性,為李淵提供支持(有人認為是捐出家產(8)參見蕭讓:《武則天:女皇之路》,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9頁。),雖結果未卜仍誓死投效之。據記載,“士彟為性廉儉,期于止足,殊恩雖被,固辭不受,前后三讓,方遂所陳”(9)(宋)王欽若:《冊府元龜》卷464,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5244頁。。武士彟雖為商人,但未受商人固有之自私、唯利是圖、精明狡猾、投機鉆營等“劣根性”的鉗制,其具有的“廉儉”“忠節”(10)(宋)王欽若:《冊府元龜》卷627,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012頁。等良好品性為他更好地培養武則天奠定了基礎。
尤為重要的是,改變武士彟對待武則天態度的袁天綱相面事件。貞觀元年(627年),武士彟擔任利州都督,袁天綱赴京途經利州。袁天綱到武士彟家中,見其妻楊氏說,“唯夫人骨法,必生貴子”。在給二子、一女相面后,乳母抱出著男服的武則天,袁天綱道,“此郎君子神色爽徹,不可易知,試令看行”。后大驚,“此郎君子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轉側視之,又驚“必若是女,實不可窺測,后當為天下之主矣”(11)(后晉)劉昫等:《舊唐書》卷191,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093-5094頁。。這里流露出一個重要信息——“武后時衣男子之服”。如果說此時少女喜著男裝是自主選擇之果,作為3歲小兒的武則天著男服就是父母性別意識的直觀反映。蘊含其中的信息有二:一是武士彟有超前的性別意識,混同的性別觀念使他認為男女皆一樣,女兒可著男裝,兒子亦可著女裝;二是武士彟的“求償心理”(12)已有二子的武士彟求子心切或可解釋為:一是二子資質平平,且生母地位低下,難擔其厚望;二是楊氏身份高貴,且系皇帝指婚,頭胎生女,故望生子。參見[日]原百代:《武則天傳》上,譚繼山譯,成都:天地出版社,2019年版,第8頁。讓他把本為女兒的武則天視作男孩對待,故著男服。無論出于哪種理由,都顯示出武士彟具有在封建父權制相對松弛的環境中培養出女性國家統治者的積極性別意識。
史書雖未曾記載武士彟此時的心理活動,但基于常理不難發現他的心理活動及前后發生的轉變,即從最初的驚訝,進而懷疑,再至內心認同,以及由此帶來行為的轉變。“關于武則天的童年生活,正史上記載不多,可以確知的是武士彟無論到哪里上任,都會把她帶在身邊,跑遍了小半個中國。”(13)蕭讓:《武則天:女皇之路》,第11頁。孩童時武則天涉足之處,后來都留下喜聞樂見的傳說。這些具有神話色彩甚至夸大的故事性敘事固然不足為信,但可從側面反映出幼年武則天深受武士彟寵愛。這種寵愛不僅是傳統的父親對女兒的愛,更類似于父親對兒子或繼承人的培養,這使幼年武則天開闊了視野,學習了基本的面向男性掌握的政治社會公領域的處世之道。或許基于當下的觀點審視,武父對武則天偏男性化之愛或培養的做法不足為取,但考慮到依舊是封建父權制社會的背景,武父對武則天男性化的培養方式就應被看作是有價值的超前之舉。
(三)母親積極性別意識的影響
在那些走出家庭、獲得顯著成就之女性的身后通常存在著一位偉大的母親,女皇武則天也不例外。有關武則天母親——楊氏的史料記載不多,按照袁天綱相面得出的說法,“唯夫人骨法,必生貴子”(14)(后晉)劉昫等:《舊唐書》卷191,第5093頁。,楊氏本身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女子。“楊氏出自弘農。弘農楊氏打從東漢年間出了號稱‘關西孔子’的楊震后,成為名門。”(15)韓昇:《武則天的家世與生年新探》,《廈門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這說明楊氏擁有高貴的血統。“楊氏既為高門貴女,頗具北朝女子精明強干、大膽潑辣之風,不好針線女紅,輕視紡紗織布,喜詩書,善屬文。”(16)蕭讓:《武則天:女皇之路》,第10頁。在學識、才情和性格方面,楊氏亦不同于一般女子。經歷南北朝從分裂走向統一,見證隋朝從建立到滅亡,唐朝從起兵到建立,以及在此過程中經歷的坎坷命運后,無論內在品性還是對外在世界的看法,楊氏都得到了磨練。
據“咸亨元年(670年)八月二日,崩于九成宮之山第,春秋九十有二”(17)(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421頁。推測,楊氏結婚時至少已42歲。將之解釋為“父來不及為她尋得佳婿就撒手人寰,接著天下鼎沸,隋朝滅亡,歲月蹉跎,好不容易熬到唐朝建立,天下初安,楊氏才得以由唐高祖主婚,嫁給武士彟”(18)韓昇:《武則天的家世與生年新探》,《廈門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不盡合理。即便一般人家,父母死后,閨中女兒的婚姻亦會由其他尊長主導,更何況出身貴族的楊氏。而且,相較之平民女性,戰亂對貴族女性的影響相對較小。更毋論,“出身于周、隋大貴族的唐高祖李淵,對隋朝的皇族、宗廟和舊制度加以保護,使豪門貴族地主仍擁有相當大的勢力”(19)謝建明,黃華強:《武則天——尊法反儒的女政治家》,《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4年第3期。。楊氏結婚是唐后至少3年以上,此時再認為政治和社會因素導致楊氏晚婚亦顯牽強。另外,楊氏嫁給武士彟系高祖指婚。若非如此,已逾不惑之年的楊氏何時完婚,有無終身不婚的可能,是僅用現實因素無法解釋的。真正的原因在于,楊氏擁有一定程度的反抗封建婚姻禮教的精神,這樣一位不甘封建禮教束縛的母親必然會在各方面對女兒產生影響。
另外,篤信佛教為楊氏相信袁天綱相面的說法、改變對武則天的性別觀念和培養方式奠定了重要的心理基礎。唐朝佛教興盛,相術流行。佛教與相術背后之玄學的關系為何,以使二者同時存在?因為重玄思想屬于道家,故佛玄關系演變為了佛道關系。在唐朝,佛道關系復雜。道教通過“援佛入道”(20)張耀南,錢爽:《“離四句絕百非”與成玄英“重玄學”》,《宗教學研究》,2019年第3期。以完善理論建設。玄、佛、道之間的微妙關系,為楊氏相信“女主天下”之說提供了現實條件。自此以后,始終持守佛教信仰的楊氏會相信女兒終將成為掌權者的預言,至少她對女兒必定與眾不同的說法是深信不疑的。這種確信還會反映在行為方式上,無論是培養目標定位、教學內容安排還是性別角色認定,楊氏對幼年武則天的教導必將有別于其他女性。在武則天爭寵奪嫡的關鍵時期,楊氏通過積極行動給女兒提供支持,亦表明她對女兒將成為皇帝的確信。
(四) “女主天下”的內心確信
袁天綱相面時,武則天雖為3歲小兒,但隨著慢慢長大,無論是從父親(21)按照原百代的說法,“父親反復告訴她那個預言,直到年幼的武則天能夠背誦清楚為止,她并且答應父親,自己要努力促成這件事”。參見[日]原百代:《武則天傳》上,第69頁。還是他人言語中,幼年武則天都知悉“女主天下”之說,是可以確定的。加之,父母對自己特殊的培養方式,強化了武則天對“女主天下”的認同。根據后來在稱帝時/后試圖通過宗教玄學證成政權合法性的做法(如,利用彌勒佛化身為人普度眾生的傳說,自稱是彌勒化身金輪普照,給自己取大周金輪圣神皇帝的尊號(22)參見蕭讓:《武則天:女皇之路》,第32頁。)不難看出,或是受母親篤信之佛教的影響,武則天是相信宗教玄學之說的,亦為她認可袁天綱相面之說奠定了心理基礎。隨著內心認同而來的是對自身定位的改變,即武則天相信自己的命運有別于其他女性/皇帝妃嬪,她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女主天下”的預言。
武則天在貞觀十一年(637年)入宮時,母親流淚告別,她坦然答道,“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23)(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76,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474頁。。武則天表現出的異常冷靜態度可解釋為,在相面之說的指引下,她對進宮有必然的預期,或早已作好入宮準備。進宮十余年里,她的品級未獲升遷。太宗駕崩后,其更被迫出家感業寺。若將這些遭遇置于任一其他妃嬪身上,命運的沉浮將把她們傷得體無完膚,又有誰會再抗爭。在暗無天日的歲月里,武則天或懷疑過“女主天下”之說的真實性,但經過艱難的內心爭斗后,她還是相信“天命在我”(24)[日]原百代:《武則天傳》上,第262頁。“天地之間一定有神秘力量的存在,幫助自己取得非凡成就”(25)蕭讓:《武則天:女皇之路》,第334頁。。另外,“貞觀初,太白頻晝見,太史令占曰‘女主昌’。又有謠言說:‘當有女武王者’”(26)(后晉)劉昫等:《舊唐書》卷69,第2524頁。,此與袁天綱相面得出的“女主天下”之說不謀而合。“此種不謀而合的神秘,給武則天強烈的沖擊。”(27)[日]原百代:《武則天傳》中,譚繼山譯,成都:天地出版社,2019年版,第456-457頁。于是,她又想起袁天綱相面事件,進而強化了其對“女主天下”之說的確信。
基于幼年和入宮初年的不幸經歷,將武則天“想象成為單純由戾氣凝結而成的怪胎”(28)蕭讓:《武則天:女皇之路》,第5頁。的觀點,不足以闡釋她隱忍數十年,經過艱難險阻,最后登上至尊皇位的事實。武父去世之后短短兩年內,兄長的刁難形塑了伴隨武則天終身之暴力性格的說法,按照性格形成的一般規律是很難成立的。對武則天而言,初入宮伊始“心里便有著‘燕雀安知鴻鵠之志’的念頭,亦深知前途布滿荊棘,困難重重”(29)[日]原百代:《武則天傳》中,第456頁。。在險惡異常的環境中,兒時袁天綱相面得出的“女主天下”之說成為武則天的重要心靈依托,及其在艱難歲月里百折不撓的精神支柱和克服重重困難的核心動力。它像明燈一樣,將武則天從信與不信、掙扎、糾結、痛苦的深淵中拉出來,指引她走向權力的制高點。
二、武則天給同時代女性帶來的福祉
共情倫理的核心主張是,“我了解你的處境,因而我支持你”之設身處地的同理心。故不同于有研究者主張的武則天“基本遵循男權權力行使規則,以‘女扮男裝’進入封建權力系統乃至權力之巔,按照男權統治和文化規則治理國家幾十年……似乎沒有絲毫女性氣息”(30)徐琛整理:《女學者論武則天》,《婦女研究論叢》,1995年第4期。。本文認為,基于共情倫理和現實情況的審視,武則天不是沒有女性氣息,而是在被儒家禮教限制手腳和思想的情況下策略性地納入了女性氣息。事實上,提高女性的地位是武則天的長期目標,但凡有性別意識能夠嵌入的地方,武則天便采取行動以與同時代女性共榮耀。
(一)否定并反抗儒家禮教
在結構性貶低和壓迫女性方面,儒家禮教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在母權制社會,世系按母親計算,母親擁有崇高的地位。“母權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欲的奴隸,變成單純的生孩子的工具了。”(31)[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若說從根源看,母權制向父權制過渡源于生產方式的變更,以制度化方式固定這一變更的則是儒家禮教。儒家禮教打著“有序”的旗號,通過一系列禮法將女性合法、永遠地囚困在第二性的位置。在以父權制為基礎的封建社會,男性憑借儒家禮教成為了“當然”的掌權者,然后通過儒家禮教強化男權統治、證成男權統治的合法性,其間存在壓迫女性的惡性循環。就此,武則天反對儒家禮教是必然的,她成為國家掌權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這種惡性循環。
武則天反儒是一以貫之的。一是通過自身行為反抗儒家禮教。武則天敢于親自執政,本就是對儒家正統思想的蔑視和造反,是對“男尊女卑”觀念的批判。二是在科舉方面,武則天蔑視儒學經典,提倡詩賦文章。逐漸地,“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遐久,寖以成風”(32)(唐)杜佑:《通典》卷15,王文錦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01頁。。當這種文化風俗滲透至被儒家禮教形塑之男性身上時,他們對妻子、女兒乃至所有女性的態度亦會發生改變。對女性而言,新文化風俗的傳播將提升她們的自我認知。三是在保皇派以儒家禮教為據阻止立武則天為后時,她怒說道:“何不撲殺此獠”(33)(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290頁。,亦表明她對保皇派儒家信徒及其背后之儒家禮教動刀的決心和勇氣。在此,不能僅用殘暴和專斷來批駁之,因其涉及另一場無聲但激烈的斗爭——女性與男性/女性與束縛和壓迫女性之儒家禮教的斗爭。故清除保皇派儒家信徒不僅是武則天個人的勝利,還具有重要的反性別歧視和壓迫的意義。
鑒于在儒家禮教形塑起來的文化和政治中,女性不能執掌國家政權,是武則天面臨的最大阻礙。從此意義上講,武則天反儒,在策略上確實是為自己執政掃清障礙。就結果而言,這對束縛在儒家禮教下的同時代女性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在恪守儒家禮教的封建社會,多年不得太宗賞識、尼姑出身的武則天敢于反抗“男尊女卑”的傳統,打破“三綱五常”的禮教,登上至尊皇帝之位,是女性沖破儒家禮教、尋求自身發展的重大事件。試想之,當國家掌權者是女性時,又有誰敢明目張膽地說男尊女卑。武則天掌握國家政權的事實有力地證明了,除了逆來順受,女性還可以且有能力在所謂本屬于男人的世界里取得和男人同樣的成就。概言之,武則天掌握國家政權具有的示范意義,加之她采取的反儒舉措產生的積極社會效果,在當時的唐代社會形成了反儒的風氣。在封建父權社會的大背景下,這是對女性最友好的環境。
(二)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
在宗法禮制下,“喪服是表示身份等級和服喪人和死者之間政治、血緣關系親疏的原則”(34)段塔麗:《唐代婦女地位研究》,第212頁。,由此確定親屬集團的范圍邊界,及其內部的從屬關系。在封建禮教下,父親是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故《儀禮·喪服》規定,妻子為丈夫服斬衰(三年),丈夫為妻子服齊衰(一年),母在為父服和父在為母服差異明顯。如左散騎常侍元行沖所言,“天地之性,惟人最靈者,蓋以智周萬物,惟睿作圣,明貴賤,辨尊卑,遠嫌疑,分情理也。……。天父、天夫,故斬衰三年,情理俱盡者,因心立極也。……而妻喪杖期,情禮俱殺者,蓋以遠嫌疑,尊乾道也”(35)(后晉)劉昫等:《舊唐書》卷28,第1023頁。。服喪時間的差異體現了在以男性為中心、慣行家長制的封建社會,女性祖先受到嚴重不公正對待。在認識到提高女性地位必須先提高母親地位后,武則天又一次采取了“越軌”行為。
上元元年(674年),武則天上表高宗說道,“至如父在為母服止一期,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于母,慈愛特深,非母不生,非母不育。推燥居濕,咽苦吐甘,生養勞瘁,恩斯極矣!所以禽獸之情,猶知其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若父在為母服止一期,尊父之敬雖周,報母之慈有闕”(36)(后晉)劉昫等:《舊唐書》卷28,第1023頁。。就此,武則天提出了“建言十二事”,其中第九條為“父在為母服齊喪三年”(37)(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76,第3477頁。,被認為是在其執政生涯中最具女性主義色彩的提案之一。該建言被高宗采納,并下旨落實。垂拱元年(685年),武則天以皇太后身份主政時,將之列入《垂拱格》,成為正式的法律。“至(開元)二十年,蕭崇與學士改修五禮,又議請以上元元年(674年)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為定。及頒禮,乃一切依行焉”(38)(宋)王溥:《唐會要》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678頁。,“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成為后世標準喪期。
武則天上表時提到“夫禮緣人情而立制,因時事而為范。變古者不足多也”(39)(宋)王溥:《唐會要》上冊,第675頁。,是女性意識覺醒的典型表現。從“禮緣人情而立制”和“因時事而為范”可看出,此時武則天已對禮法古制產生了質疑。在質疑禮法古制的基礎上,武則天始擁有“變古”之意。她明知會遭到竭力阻撓,依舊以“傷人子之志”為由請求變更服喪制度,表明武則天清楚地認識到服喪制度喻示的女性從屬地位,并知曉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源所在。理由方面,武則天提出的“非母不生,非母不育”“推燥居濕”“咽苦吐甘”“生養勞瘁”(40)(后晉)劉昫等:《舊唐書》卷28,第1023頁。等,呈現出的是傳統女性以子女生養和照料為核心的家務活動,以及由此面臨的不利處境,依此為據主張父母喪服同制,乃是變相地承認了女性家務勞動的價值。概言之,武則天將亡母適用的“齊衰”改為“斬衰”,打破了家無二尊的局面,在服制上提高了母親家庭法律地位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妻子乃至所有女性的社會地位。
(三)改革婚姻家庭制度
武則天深諳在儒家禮教下,婚姻及由此形成的“家庭始終是婦女們難以沖破的牢籠”(41)段塔麗:《唐代婦女地位研究》,第25頁。。但在封建制度下,即便是作為國家掌權者的武則天,亦無法徹底為所有女性打破婚姻家庭禮教的束縛。然而,武則天并沒有望而卻步,而是以更具策略性和靈活性的方式為提高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采取了不少重要舉措。由此帶來的積極影響是,武則天時期,女性在家庭生活方面擁有前所未有的權利和自由。可以說,此階段女性的婚姻家庭法律地位在整個封建社會是空前絕后的。考慮到皇帝后宮雖特殊,但本質上仍是家庭的一種,故本部分的探討既指通常意義上的封建家庭,又包括廣義的家庭——皇帝后宮。
武則天在通常意義上的婚姻家庭方面采取的舉措主要如下。一是聘禮充嫁妝。顯慶四年(659年)朝廷下令:“天下嫁女受財……皆充所嫁女貲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42)《唐會要》顯示,聘禮充貲妝是李義府的提案。需要注意的是,在遭長孫無忌貶斥之際,李義府上表請立武昭儀為后,成為第一個支持立武則天為后的大臣,后為武則天寵臣,直至客死他鄉,武則天對這位追隨者都念念不忘。鑒于武則天和李義府之間的特殊關系,該提案很可能是李義府希武后旨上表的,奏折的通過是二人上下配合的結果。而且,此時武則天在朝廷的影響已經非常深遠,如果說聘財充嫁妝這一極具性別色彩的舉措沒有武則天的參與甚或是決定,很難成立。意為,此前由女方父親/家庭所有的聘禮均抵充嫁妝,歸出嫁女所有。此舉具有重要價值,對在室女而言,這在提高其家庭地位的同時,有助于減少父母賣女求財的行為;從出嫁女角度看,將嫁妝規定為私人財產、夫家不得侵占,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女性的財產權,亦有助于提高其在夫家的地位。二是改大婚時女子的跪拜禮為站立式參拜禮。2021年播出的電視劇《風起洛陽》中有個看似格格不入的畫面:大婚時,新郎行跪拜禮,新娘站立行禮。唐之前,大婚時男女均行跪拜禮。《宋史》顯示,“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對。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是婦人亦跪也,唐太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43)倪其心:《宋史》第九冊,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5778頁。,武則天當政廢女性跪拜禮。男跪女不跪的結婚行禮方式具有提高女性地位的象征意義。
武則天在皇帝后宮采取的典型舉措是改革妃嬪制。龍朔二年(662年),武則天主導進行妃嬪制改革:“置贊德二人。正一品。以代夫人。宣儀四人。正二品。以代九嬪。承閨五人。正四品。以代美人。承旨五人。正五品。以代才人。衛仙六人。正六品。以代寶林。供奉八人。正七品。以代御女。侍櫛二十人。正八品。以代采女。又置侍巾三十人。正九品”(44)(宋)王溥:《唐會要》上冊,第32-33頁。。此舉弱化了妃嬪的傳統角色,突出了女性職能的價值。“至少在名義上,她們是掌領宮中職事的人。”(45)陳弱水:《隱蔽的光景: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頁。在傳統的性別角色下,妃嬪本屬妻妾,生死榮辱均系于天子。此舉反映出,妃嬪像朝中大臣那樣擁有政治或實務上的職能。為每個位階設置定數,削減妃嬪數量,變相體現了武則天反對多妻制的態度。故研究者提出的武則天和高宗“形同一夫一妻”(46)[日]原百代:《武則天傳》中,第442頁。雖有夸大之嫌,但妃嬪數量減少確屬事實。考慮到深宮的寂寞、束縛和危險,對因此無須進宮的女性而言,何嘗不是福音。皇帝如此,官員百姓亦效法之,納妾的情況將會減少,賣女、強搶民女的情況亦有望減少,對普通女性來說又何嘗不是福音。
(四)調整政治、娛樂、祭祀活動
特開女試。武則天“因思如今天下之大,人物之廣,其深閨秀閨能文之女,故不能如蘇蔥超今邁古之妙,但多才多藝如史幽探、哀萃芳子類,自復不少。設俱湮沒無聞,豈不可惜?”(47)(清)李汝珍:《鏡花緣》,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頁。故擬令天下才女俱赴廷試,以文較高下。次年武則天下詔:“丈夫而擅詞章,固重圭璋之品;女子而嫻文藝,亦增蘋藻之光。我國家儲才為重,歷圣相符;朕受命維新,求賢若渴。……是用博諮群議,創立新科,于圣歷三年,命禮部諸臣特開女試”(48)(清)李汝珍:《鏡花緣》,第196頁。。類似于科舉中第者入朝為官,武則天設“女學士”“女博士”“女儒士”之職。若有意到內廷供奉,可在試用一年后量才取用。女性不僅能參加女試,通過者還有官職和俸祿,父母亦可享受相應的待遇。神龍元年(705年),女官已達三千(49)參見劉曉云:《唐代女官的特點》,《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S2期。,這從側面反映出武則天時特開女試的真實性。女官從事的固然是與傳統女性職能相關的工作,卻也通過協助處理政務最大可能地接近了權力的中心。
禁天下婦人為俳優之戲。“俳優,古稱倡優、優伶,后多指從歌舞藝人中分化出來的以調笑逗樂、滑稽表演為藝術特色的職業藝人。”(50)成軍:《隋唐俳優“戲弄”表演研究》,《戲劇文學》,2017年第12期。據《韓非子·難三》記載,“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俳優的地位極其低下,他們只是主人的附庸甚或奴隸。隋唐時,俳優在法律上屬于賤民,加之職業的特殊性,他們通常被限制在特定場所內,世代群內婚配。“樂人、歌者,舞者,穿著華麗,袍袖冠冕,舞衣翩躍,而俳優則上身袒裸,只是下身著褲,從未見有衣冠整齊者。”(51)于天池:《兩漢俳優解》,《中國典籍與文化》,2005年第2期。如果說這在男性身上彰顯的是地位低下,附加上性政治的作用以后,物化和低等級性在女俳優身上體現得更明顯。女俳優不僅會成為供男人性娛樂和戲弄的對象,甚至還會成為主人的性工具,這是對女性人格尊嚴的極度貶損。為避免這種情況發生,以維護女性的人格尊嚴,武則天力圖禁止女性為俳優之戲。故在顯慶六年(661年),時任皇后的武則天“請禁天下婦人為俳優之戲”(52)(后晉)劉昫等:《舊唐書》卷4,第82頁。,該建議獲得高宗的準許。

三、武則天性別意識和行動的局限
在掌握國家政權的數十年里,武則天雖提出不少對女性友好的舉措,但從整體看,她對封建社會中女性面臨之消極處境的改變并不多。“這是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基本格局決定的。”(54)段塔麗:《唐代婦女地位研究》,第86頁。武則天是儒家禮教的挑戰者,但她確實也置身于由此形塑的大環境中。“挑戰與妥協,斗爭與放棄,對自己能力的自信和對正統倫理觀念準則的力不從心,同樣存在在她身上。”(55)蕭讓:《武則天:女皇之路》,第261頁。武則天的性別階級身份——貴族階級女性,亦注定她無法真正地跨越階級限制,在更廣泛層面給普通女性帶來福祉。
(一)封建父權制根深蒂固
早在奴隸制時期,以男性士大夫的生活為參照,儒生對兩性附加了雙重道德標準,進而形成了男女之間強弱、主從、剛柔、尊卑的鮮明對比。“商周更替完成由父系制定型到父權制確立的過程,確立了父系本位、男性中心的父權制體系,基本格局是男主外女主內,婚姻的目的是為男性本位的父權家族利益,政治權力和家族財產傳承都在男子之間進行。”(56)張菁:《唐士大夫的女性觀與武則天現象的產生——以墓志為中心》,《江海學刊》,2011年第5期。至兩漢,男性士大夫強化了女性對家庭的依附,贊揚女性謙和之氣,要求女性柔順貞孝,卑弱寡欲,為丈夫、子女和家庭甘愿作出犧牲。“自漢代儒學立于‘獨尊’地位后,以‘三綱五常’為主要內容的封建禮教逐漸成為束縛女性的精神枷鎖”(57)段塔麗:《唐代婦女地位研究》,第142頁。,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男主外女主內等倫理綱常成為定禮,封建父權制正式確立。此后的兩千多年里,中國女性內化了儒家倫理綱常,并依此安排自己的生活,公認之理想女性形象亦是符合這套定禮的女性。
封建父權制社會的基調如此,哪怕身處開明的唐朝,女性依然處于由此構建起來的密網中。武則天固然有幸成為“漏網之魚”,但遠無與封建父權制“魚死網破”的條件和力量,而且事實上武則天的突破也是在父權主義框架下進行的。若試圖改變女性備受歧視、壓迫、剝削的封建父權制整體環境,僅憑作為統治者的武則天或少數貴族女性群體的意識覺醒還遠遠不夠,而是需要女性整體的意識覺醒。意識覺醒是向內的,它要求女性認識到附加于己身的父權統治是錯誤的,女性有權擁有與男性等同的權利和自由,進而形成改變不自由現狀的自覺。基于對唐代社會的審視不難發現,通常所說的唐朝女性社會地位高,指向的不過是穿低胸裝、男扮女裝、女性走出家庭等現象層面的東西,它們不能夠成為證成唐代女性意識覺醒的充要條件。在唐代女性依舊從心理上認同封建倫理綱常并依此安排自身生活的情況下,試圖徹底改變她們的生存和發展現狀并不現實。
(二)性別階級分化的作用
依據恩格斯的說法,“最初的階級壓迫是同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同時發生的”(58)[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57頁。,女性在總體層面可以被視為受壓迫階級。依此,在將封建父權制作為敵人的情況下,武則天確實與唐代女性乃至封建社會所有女性同處同一陣營。但正如齊拉·愛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的研究所顯示的,除共同面臨的父權統治外,女性并非同質性的群體,階級分化帶來了女性群體內部的差異(59)SEE ZILLAH EISENSTEIN,Constructing a Theory of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Feminism,Critical Sociology,Vol.25,No.2-3,1999,pp.196-217.。納入階級因素的考量不難發現,武則天與同時代女性的階級地位懸殊,這決定了僅借助父權制分析難以全面解釋武則天性別意識及其行動的局限。在揭示造成這種局限性的原因時,女性群體內部的階級分化不容忽視。
按照標準不同,武則天與同期女性之間的階級差異大體可分為兩類。一方面,如果說武則天能為同期女性帶來福祉,更多指向的是地主階級(庶族地主)而非平民女性,這是她生長于地主家庭的事實決定的。基于對武則天掌權時期采取的措施的審視不難發現,打壓士族地主、扶持庶族地主是她始終堅持的立場。武則天的性別意識和行動與她代表的庶族地主階級利益和政治主張是一致的,這注定了她無法跨越階級限制,設身處地地為社會中下層女性考慮。另一方面,作為貴族女性的代表,武則天的性別意識和行動亦有限定性。從初入宮門的那一刻起,她便脫離了普通女性的生活,她所經歷以及看到和聽到的亦只是貴族階層女性在深宮中的遭遇。無論是泰山封禪還是變革妃嬪制度,武則天性別意識覺醒及采取之行動的受益者更多是同屬貴族階級的女性群體,而非普通的社會中下層女性。
根據傳統政治哲學家的說法,人類“自利”和“互利”的本性決定了“行動者”和“受益者”一般是等同起來的。這種等同在爭取權利或尋求解放的女性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通常而言,女權運動是由特定女性發起并主導的,旨在解決的是她們所關切的問題,這可以適用于對武則天性別意識和行動的分析。立場決定思想,作為地主階級女性和貴族階級女性的代表,武則天很難真正了解中下層女性的需求,更毋論超越階級限定性,對她們給予更多的愛與關懷了。故有學者譴責道,“武則天作為女性登基稱帝,完成了堪稱偉大奇跡的逆襲,是改變萬千女性命運的一次千載難逢的重大機遇。但武則天沒有抓住這次機遇,她僅是給自己和極少數貴族女性的生活帶來重大變化,未從根本上推動女性命運的改變”(60)畢秋生:《武則天與武則天時代的女性命運》,《菏澤學院學報》,2015年第6期。。即便沒有那么絕對,這種譴責亦有一定的道理。女性群體內部的階級分化及由此帶來之立場的差異,注定了武則天難以從根本上推動同時代女性命運的改變。
(三)局限的具體表現
女性參政依舊受到嚴格的限制。自儒家禮教被確立為指引女性的行為規范以來,女性的活動領域便被劃定在家庭內部。在武則天執掌國家政權的唐朝,固然有少數女性成為宮官,皇室女性亦積極參與政治生活,但男性主導政治的狀況并未有實質性改變。武則天執政時雖面向全國才女開女試,但詔書顯示,女試中第者,“其有情愿內廷供奉者,俟試俸一年,量材擢用”(61)(清)李汝珍:《鏡花緣》,第196頁。。也即,即便通過女試并拿到名次,女性可以獲得的最多不過是成為“內廷”官員的機會,與朝廷官員不可同日而語。唐朝的“內廷”是參照“外廷”(朝廷)設置的,設有宮官(多為女性)制度。女性宮官負責掌管內宮事務,工作內容與普通女性在家中負責的事務有相通性。就此,“女試”與科舉存在實質性的差異,女性成為宮官亦不等同于“參政”。即便經過武則天的特許,權傾一時且有“巾幗宰相”之名的上官婉兒終究也不能上朝議政。
還政于李唐。皇位同姓相襲是封建王朝的常規做法,武周則是例外。武周皇位繼承更具突破性的兩種可能都被武則天推翻了。一是立太平公主為皇太女。武則天稱帝后,在太平公主“沉敏多權略”(62)(宋)司馬光:《資治通鑒》,第6651頁。、嫡親皇子資質平平、社會相對開放的情況下,出現了立皇太女的最佳時機。二是參照封建父權制傳統,在侄子中尋找皇位繼承人。然而,武則天既未打破“傳男不傳女”的傳統而傳位于公主,亦沒有將皇位傳給武姓后代,而是還給高宗嫡親皇子。另外,武則天發布了意料之外但情理之中的遺詔——袝廟、歸陵、去帝號。武則天決定將神主歸李唐宗廟,自稱“則天大圣皇后”。如果說年輕時武則天試圖顛覆以父權制為底色的國家政權,在確定皇位繼承時確實動過冊立皇太女和傳位于武姓后代的念頭,但最終仍決定將皇權還給李唐。在心理和行為上,武則天最終都向曾經挑戰過的世界和森然可畏的秩序屈服了。如果說武則天在與男權的斗爭中取得了一定的勝利,但試圖推翻宗法制度的斗爭卻是失敗的。
武則天的舉措更多反映的是特權階級女性的利益。無論是初衷還是結果上,武則天采取的具有性別意識的舉措多有階級限定性。變革妃嬪制度體現的是貴族女性的需求,相對提高的只是少數女性的地位。更多普通女性依舊被束縛在家庭內部,無休止地從事家務勞動。消耗女性青春乃至生命的家務勞動被認定為沒有經濟價值,她們不得不依靠丈夫的供給而生活。女試方面,武則天頒布的詔令提到,“他如體貌殘廢,及出生微賤者,俱不準入考”(63)(清)李汝珍:《鏡花緣》,第197頁。。出生是女性參加女科的前提,出生微賤的女性被剝奪了唯一可能接近政治權力的機會。武則天稱帝的行動傳達了“女性不能參政的規則可以被打破”的重要信息,故相較于他朝,此時女性參政的情況確實更為常見,以太平公主為代表的宮廷貴族女性曾掀起一波參政浪潮,其他女性的參政之路依舊被阻斷。除一般意義上的特權階級女性外,這里提到的特權階級女性還包括武則天的同族女性。從武則天以皇后身份參與國家政治伊始,其母、姊、侄女均獲得封賞。武則天稱帝后,武姓四代女性親屬和姨母亦得到了相應的封賞。
四、結語
或是出于器重酷吏的任人偏好,或是出于心狠手辣的處世之道,或是出于有悖常禮的生活作風,或是出于對儒家禮教動刀的果斷,甚或只是出于女性的性別身份,武則天在很長時間里都是以“悍婦昏君”的形象出現在研究者的書寫中的。然而,透過女性主義的棱鏡,撕開父權制文化傳統編織的性別歧視面紗可見,武則天不是昏君、僭主、崇尚酷刑的法家代表,而是擁有輝煌而偉大一生的傳奇女子。身處極度壓制女性的封建父權制社會,武則天不屈服于傳統有關女性命運的設定,而是大膽地挑戰父權制的安排,最終將男性統治者拉下神壇,成為中國唯一的正統女皇,掌握政權數十年。武則天用登上至尊皇位的事實打破了女性是劣等主體和從屬者的謊言,證明了她們同樣有能力做此前被認為只能由男人做的事情。作為封建禮法制度的“反叛者”和同男性爭取國家最高政權的“先驅者”,在爭取和掌握國家政權的道路上,武則天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險。前有高宗以無法控制為由,“陰欲廢之”(64)(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4,第81頁。,后有朝臣兵變試圖討伐之,一路走來的艱難險阻都注定了她“只能在刀尖上跳舞,難有一刻安穩”(65)蕭讓:《武則天:女皇之路》,第34頁。。慶幸的是,歷史沒有辜負她數十年的隱忍和持守一生的期許,武則天終于在夾縫中以英雄主義的姿態找到了屬于自己和同時代女性的一片天空。遺憾的是,在封建父權制絲毫未被動搖的情況下,這片天空終究是有限的。無論是武則天還是同時代其他女性,她們面臨的束縛均非短時間所能打破。故即便在性別意識和行動上有局限,對武則天亦不能夠太過苛責,更毋論對她“禍國殃民”“垂簾聽政”“牝雞司晨”的定罪。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在感嘆其身處父權制環境仍能盡最大可能為女性發聲的同時,考慮到女性解放是長期且艱難的事業,女皇武則天的未竟之業亦需后時代,乃至今時和未來的持續努力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