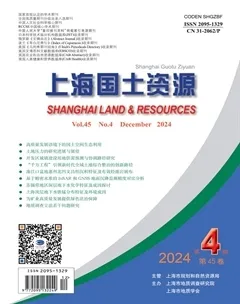宅基地改革中三方主體的演化博弈及仿真分析


關鍵詞:宅基地;三權分置;演化博弈;模擬仿真
中圖分類號:F32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5-1329(2024)04-0208-06
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鄉村人口減少約16436萬人,而農村人口減少的影響之一便是閑置宅基地與農房增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農村綠皮書顯示,2018年我國農村宅基地閑置率10.7%[1]。另外,城鄉融合與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使農民的財產性需求不斷增加。以保障功能為主的宅基地制度已難以滿足鄉村發展與農戶增收的需求,迫切需要“守正創新”。2020年底,全國104個縣(市、區)和3 個設區市獲批新一輪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地區。諸暨市作為紹興市的改革試點先行地區,積極探索宅基地“三權分置”的實踐形式,于2022年開展了“三權三票”改革,初步形成一套相對成熟的“諸暨經驗”,在全國具有創新性。在地方實踐探索的同時,理論研究也不斷發展。國內對于宅基地“三權分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宅基地“三權分置”的體系內涵、實踐路徑等方面[2-9];在農村土地改革中三方主體的行為博弈研究領域,國內學者多采用定性研究范式分析宅基地改革與征地過程中政府、村集體與村民的三方博弈[10-12];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從農戶與村干部的社會關系出發,分析其對農戶行為的影響[13-15]。
因此,目前學者多關注于宅基地“三權分置”的體系內涵與實踐路徑研究,而三權分置實踐過程中基層政府、村集體與農戶三方的行為博弈研究較少。同時,在分析宅基地改革中三方主體的博弈行為時,學者多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量化分析方法較少。此外,諸暨市“三權三票”改革作為宅基地三權分置的實踐探索,不同利益訴求的改革主體是如何達成三方共贏局面的呢?因此,本文以諸暨市的“三權三票”改革為例,采用量化分析方法,通過構建改革中基礎政府、村集體與農戶三方的演化博弈模型,并進行模擬仿真分析,探索“三權三票”改革中基礎政府、村集體與農戶三方的行為博弈過程與關鍵影響因素,以補充相關研究成果,為國家推進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提供借鑒參考。
1 模型假設與構建
1.1 模型假設
為構建博弈模型,分析各方策略和均衡點的穩定性以及各要素的影響關系,基于諸暨市“三權三票”的改革實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1)博弈主體
該博弈過程有基層政府、村集體與農戶三方主體。三方皆為有限理性,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2)策略空間
基層政府的策略空間為Sg=(資金支持、無資金支持);村集體的策略空間為Su=(積極推進、消極推進);農戶的策略空間為Sf=(退出、不退出)。
(3)行為標準化
基層政府在t 時刻選擇“資金支持”的概率為x,選擇“無資金支持”的概率為1-x;村集體在t 時刻選擇“積級推進”策略的概率為y,選擇“消極推進”的概率為1-y;農戶在t 時刻選擇“退出”策略的概率為z,選擇“不退出”策略的概率為1-z。同時,0≤x≤1,0≤y≤1,0≤z≤1。
(4)成本收益參量
當政府采取“資金支持”策略時,向村集體提供改革資金,計為成本C1;政府向村集體提供資金,村集體利用資金取得改革成效,其改革成效可計為政府的收益R1。當政府采取“無資金支持”策略時,無需提供資金,但村集體在自負盈虧的前提下仍可取得一定的改革成效,其改革成效可計為政府的收益P1。由于村集體采取“積極推進”與“消極推進”兩種策略下的收益不同,導致政府部門在村集體“積極推進”時會產生相對于“消極推進”時的額外收益,計為S。
當村集體采取“積極推進”策略時,積極推進可以取得一定的改革成效,計為村集體的收益R2;但積極推進需要村集體消耗時間、資金等資源成本,計為C2。當政府采取“資金支持”策略時,村集體會獲得一部分資金來源,可計為N。當村集體采取“消極推進”策略時,也可以獲得一定的改革成效,但成效相對較少,計為收益P2;消極推進仍需要村集體消耗時間、資金等資源成本,計為D。
當農戶采取“退出”策略時,農戶可以獲得退出補償,以權換錢、換房、換宅等,收益可計為R3;在村集體“積極推進”的前提下,退出伴隨著補償標準不滿意、補償資金不到位等風險,計為成本C3;在村集體“消極推進”的前提下,退出也伴隨著風險,風險成本可計為F。當農戶采取“不退出”策略時,不管是在村集體“積極推進”的前提下,還是在村集體“消極推進”的前提下,農戶不退出宅基地便無退出補償收益,相對于已退出宅基地的農戶來說,存在機會成本計為Q。
具體參數含義見表1。
1.2模型構建
基于上述模型假設,構建該博弈模型的收益矩陣。如表2所示。
2模型分析
2.1三方博弈策略收益函數與復制動態方程
(1)政府的收益函數與復制動態方程
(2)均衡點穩定性分析
當上述雅可比矩陣中的所有特征值(3 個)都小于0時,可認為均衡點就是演化穩定點。當雅可比矩陣中至少有一個特征值大于0 時,均衡點為不穩定點,其中,若特征值之中有正有負,則均衡點為鞍點,鞍點是一類特殊的不穩定點。均衡點及雅可比矩陣的特征值如表3所示。
結合模型假設中對參數都為正數的界定,以及演化穩定點的判定準則,從上表中可以看出,僅E1 (0,0,0),E3(0,1,0),E4 (0,0,1) 和E7 (0,1,1) 可能為演化穩定點。
當滿足d-c2<0,q-f-c3+r3<0時,E1 (0,0,0) 為三方模型的穩定均衡點。在這種條件下,系統的穩定狀態最終會收斂于(資金支持、消極推進、不退出)。當滿足c2-d < 0,q-c3+r3<0時,E3 (0,1,0) 為三方模型的穩定均衡點。在這種條件下,系統的穩定狀態最終會收斂于(資金支持、積極推進、不退出)。當滿足d-c2-p2+r2< 0,c3+f-q-r3 < 0 時,E4 (0,0,1) 為三方模型的穩定均衡點。在這種條件下,系統的穩定狀態最終會收斂于(無資金支持、消極推進、退出)。當滿足c3-q-r3<0,c2-d+p2-r2 < 0時,E7 (0,1,1) 為三方模型的穩定均衡點。在這種條件下,系統的穩定狀態最終會收斂于(無資金支持、積極推進、退出)。
3模擬仿真
3.1演化均衡點結果檢驗
通過模型的穩定性分析,可知上述動態系統中存在四個條件均衡點。為了進一步探索,本文運用Matlab 工具對政府、村集體與農戶三方的交互行為演化過程進行數值仿真,分析各參數變動對演化結果的影響。本文基于實際,在滿足上述參數條件的前提下對參數進行賦值。
具體賦值如表4所示。
第一個均衡點的參數賦值條件為:d-c2<0,-c1 < 0,q-f-c3+r3 < 0。按照第一個均衡點的賦值條件對上述參數進行修改,在滿足r3-c3-f<-q 的條件下,將C3、F 修改為10,Q 改為2。經賦值后,運用MATLAB 軟件對模型進行仿真分析。數值分別從不同初始策略組合出發隨時間演化50 次,地方政府、村集體和農戶選擇從不同的初始概率起點出發,最終的仿真結果如圖1(a) 所示。
從圖1(a) 可以看出,政府部門、村集體和農戶三方在博弈過程中一部分趨近于(0,0,0) 的均衡點,而另一部分較分散且沒有趨近于均衡點。說明該均衡點并不穩定。
第二個均衡點的參數賦值條件為:c2-d<0,-c1<0,q-c3+r3<0。基于上述分析,P1、R1、S、C1、R2、N、F 賦值保持不變,將C2 改為4,P2 改為6,D改為5,C3改為18,Q改為1。模型的仿真結果如圖1(b) 所示。
從圖1(b) 可以看出,政府部門、村集體和農戶三方在博弈的過程中并沒有穩定趨近于均衡點E3 (0,1,0)。即政府部門選擇“資金支持”策略,村集體選擇“積極推進”策略,農戶選擇“不退出”策略的策略組合不具有穩定性。
第三個均衡點的參數賦值條件為:r1-p1-c1lt;0,d-c2-p2+r2<0,c3+f-q-r3<0。基于上述分析,P1、R1、S、C1、R2、C2、N、R3、C3、F、Q 賦值保持不變,將P2修改為4。模型的仿真結果如圖1(c) 所示。
從圖1(c) 可以看出,無論政府部門、村集體和農戶三方在博弈的初期選擇多大的初始概率,在博弈過程中,博弈方都是往(0,0,1) 結果的方向趨近,經過一段長時間的相互博弈后并最終穩定在該點。
第四個均衡點的參數賦值條件為:r1-p1-c1lt;0,c3-q-r3<0,c2-d+p2-r2<0。基于上述分析,P1、R1、S、C1、R2、P2、D、N、R3、C3、F、Q賦值保持不變,將C2 修改為3。模型的仿真結果如圖1(d) 所示。
從圖1(d) 可以看出,無論政府部門、村集體和農戶三方在博弈的初期選擇多大的初始概率,在博弈過程中,博弈方都是往(0,1,1) 結果的方向趨近,經過一段長時間的相互博弈后并最終穩定在該點。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第一個均衡點與第二個均衡點并未處于穩定狀態,因此將該兩個均衡點排除。第三個均衡點E4 (0,0,1) 情形下,系統處于穩定狀態。但該情形下農戶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在政府部門“無資金支持”、村集體“消極推進”的前提下退出具有較大風險,顯然農戶會傾向于“不退出”,因此該均衡點也排除。第四個均衡點E7(0,1,1) 情形下,系統處于穩定狀態。該情形下政府部門選擇“無資金支持”策略,給予村集體自主權利,鼓勵村集體自負盈虧;村集體選擇“積極推進”策略,通過自主治理,落實集體權利,為村莊與村民提供公共物品;農戶選擇“退出”策略,利用閑置資源,滿足農戶自身需求,增進其權益。該情形下三方達成共贏局面。因此,第四個均衡點E7(0,1,1) 情形下的三方策略組合既符合改革實踐,又是容易達成的三方共贏策略。
3.2改變初始概率值時對演化路徑的影響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均衡點E7(0,1,1) 情形下的系統既處于穩定狀態又達成三方共贏,即政府部門選擇“無資金支持”策略,村集體選擇“積極推進”策略,農戶選擇“退出”策略的策略組合。因此,本文對均衡點E7(0,1,1) 的穩定狀態進行更深入的分析,研究各主體初始意愿概率值的差異對系統演化的影響。
本文分別取x0/y0/z0=0.2/0.5/0.8表示政府部門選擇“無資金支持”策略的初始意愿、村集體選擇“積極推進”的初始意愿以及農戶選擇“退出”策略初始意愿的低水平、中水平、高水平。演化結果如圖2所示。
從圖2可以看出,對于政府與農戶主體而言,不管初始意愿為低水平、中水平還是高水平,經過一段時候后,三種策略曲線都穩定趨近于均衡點。而村集體在“積極推進”的初始意愿不同的情況下,策略曲線存在差異。當初始意愿的水平越高時,策略曲線趨近于均衡點的速度越快。這表明村集體的初始意愿對于系統演化具有重要影響,村集體初始意愿越高,三方主體越容易達成共贏局面。
3.3 改變參數值時對演化路徑的影響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 本文進一步研究均衡點E7(0,1,1) 情形下村集體與農戶主體參數值的差異對系統演化的影響。對于村集體而言,主要分析其采取“積極推進”時的成本C2 的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對于農戶主體,主要分析其采取“不退出”策略時的機會成本Q的變化影響。
(1)村集體參數值變化的影響
基于均衡點的賦值條件,將C2 分別賦值為1、3、5,來表示村集體采取“積極推進”策略所花費的“低成本”“一般成本”與“高成本”。仿真結果如圖3(a) 所示。
從圖3(a) 可以看出,隨著村集體“積極推進”策略的成本C2 逐漸變大,村集體采取“積極推進”策略的意愿概率逐漸變小,農戶采取“退出”策略意愿的概率逐漸增大,政府部門采取“資金支持”意愿的概率逐漸減小。當村集體“積極推進”成本越大時,農戶感受到的退出風險也相對較少,更愿意采取“退出”策略。政府部門為了減少治理成本與風險,在看到村集體退出成本較高時,更愿意讓其自主治理、自負盈虧,因此選擇無資金支持的意愿概率更大。
(2)農戶參數值變化的影響
對于農戶而言,主要分析其采取“不退出”策略時的機會成本Q的變化影響。按照賦值條件,將Q 分別賦值為1、5、9,來表示農戶采取“不退出”策略時的“低機會成本”“一般機會成本”與“高機會成本”。仿真結果如圖3(b) 所示。
從圖3(b) 可以看出,隨著農戶“不退出”策略機會成本Q逐漸變大,農戶采取“退出”策略的意愿概率逐漸變大,村集體采取“積極推進”策略意愿的概率逐漸減小,政府部門采取“資金支持”意愿的概率逐漸增大。當農戶看到退出后補償及福利較多時,其他農戶越先得到補償時,農戶就會覺得機會成本越大,進而退出意愿提高。政府部門與村集體在推進改革時要注意退出農戶的帶頭作用,農戶之間先后退出的博弈使農戶更容易感知到機會成本,退出意愿也越強烈,村集體可利用退出農戶的帶頭作用與說服作用促進農戶退出。
4結語
本文為探究宅基地改革中多元主體間的行為博弈問題,以諸暨市“三權三票”為例,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構建了“三權三票”改革中政府、村集體與農戶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基于模型分析,運用Matlab 軟件對三方主體的行為演化過程進行模擬仿真,分析參數變動對系統演化的影響,最后得出宅基地改革中三方主體的最優行為策略組合為:“政府減少行政干預、適度績效激勵”“村集體自負盈虧、積極推進”“農戶衡量機會成本、利益最大化”。此外,村集體的初始意愿是關鍵影響因素,其初始意愿概率值越高,模型達成理想均衡狀態越快。農戶不退出時的機會成本也會影響農戶退出意愿等。
因此,政府應鼓勵村集體自主開展改革,減少政府干預,對村集體進行績效激勵。政府部門應改善績效獎金激勵機制,比如按照退出農戶的人頭數或者退出面積給予村集體一定的資金獎勵;采取多元化獎勵機制,不限于經濟獎勵,可通過“表彰大會”等形式,提高其聲譽等。村集體應“自負盈虧”,利用機會成本促進農戶退出。村集體可對積極退出的農戶進行獎勵,如越先退出的農戶抽獎次數越多等,當農戶看到其他農戶越先得到補償時,農戶就會覺得機會成本越大,進而退出意愿提高。農戶應合理考量風險與機會成本,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農戶在做出退出決策時,勿要“隨大流”與他人作比較,應從自身與家庭的利益考量出發,退出前與退出后作對比,理性分析退出前后生活各方面的變化,做出合理的退出決策。
(責任編輯:龔士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