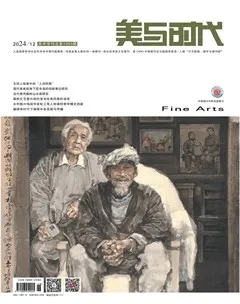奇異的世界
摘 要:從陳福善藝術風格的形成背景入手,對其作品風格的形成原因、形成過程以及藝術特點進行簡要論述。通過對其藝術風格的梳理,試圖展現一位多面立體且極富創造力的藝術家以及他的藝術世界。
關鍵詞:陳福善;超現實主義;現代水墨
一、陳福善藝術風格的形成背景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會歷史,近代香港較早接觸了西方文化,在文化傳統上形成了中西文化長期并存、相互影響的局面。經由內地的社會變革和世界局勢的動蕩,香港的人口流動影響和促進了當地的藝術發展,形成了獨特的移民文化。這種種變化,使得香港美術注定是多樣、開放、包容和雜糅的。
在20世紀初至1960年以前,香港美術一直是廣州美術的一支,深受嶺南文化的影響,1960年以后,一些內地移民藝術家將自己的觀點、創作方式帶入香港,再一次繁榮了香港的藝術創作。彼時,香港美術大體上是不再一味崇拜西方,而是在表現手法上借鑒西方,在內容上回歸東方審美趣味及傳統文化,兼容并包,形成了一股文化思潮。陳福善就是這股熱潮中的一位畫家。
陳福善作為香港現代水墨的代表人物,與林風眠、徐悲鴻、劉海粟等同處一個時代,但與三人享有的盛譽相比,陳福善在內地的關注度并不高,甚至一度被忽視。他沒有師承,自學成才,早期作品以寫實的油畫、水彩為主,有“水彩王”之稱。在九十余年的藝術生涯中,他的創作媒介、風格之豐富,創作內容、表現手法之多樣,使其在講究師承與派系的藝術脈絡中無法被分類和定位,這可能是他未能得到廣泛認識與重視的原因之一。
陳福善自五歲定居香港,其后一生從未長期離開,可以說香港是他創作的主要靈感來源。他從不強調自己的政治身份,不被戰爭和動亂裹挾,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覺和輕松樂觀的態度,在藝術創作中保有難得的自由和創造力。
二、陳福善的創作歷程
陳福善的藝術生涯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寫實期(早年至20世紀50年代)、轉型期(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和成熟期(20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80年代)。
陳福善沒有師承,沒有受過正規的藝術訓練,早年的藝術創作以設計為主,后來經過為期一年的倫敦函授課,他的繪畫技法有了一定的提升,后才轉為繪畫創作。在這一時期,陳福善也與大量畫家有了密切交集。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陳福善一直以寫實的油畫和水彩畫創作為主,描繪生活中常見的風景、靜物等。他憑借過人的天賦和積極勤奮學習的態度創作了大量優秀作品,享有“水彩王”的美譽。從小接受的雙語教育,使他能更好地吸收西方文化并與現代藝術同步,成為當時南方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在創作期間,他發表過12本繪畫理論專著及眾多評論文章,涉及內容十分廣泛。他喜歡研究和討論東西方文化關系、內地與香港的文化發展問題,也試圖對中國傳統繪畫理論進行解讀。
1962年,新建的香港大會堂中設立了博物美術館,開幕展《今日香港》直接將陳福善作品以“過時”的理由拒之門外。據說,這是導致他中期創作轉型的重要原因,由此,他決然放棄了已成就卓著的寫實手法,轉向對抽象藝術的探索。他開始嘗試學習立體主義和抽象派的創作方式和創作理念,運用西方的各種繪畫技巧進行創作。在這一時期,他發表了《從現實派到抽象派的宣言》,說:“一個寫實的畫家只能表現我們所看到的世界,可是一個新抽象畫家卻把看不到而想象到的現象形之于畫面。”在這一時期的繪畫中,陳福善漸漸擺脫了早年寫實主義的桎梏,將早期筆耕不輟的寫生訓練和理論研究都轉化為對生活的體察和感悟,在創作方面有了判若兩人的轉變。加之水墨畫當時在香港盛行,陳福善的奇幻畫風開始形成,他的山水、人物畫色彩斑斕、天真浪漫,形無常形、自由率意。夢幻與現實交織,筆觸與情感碰撞,人、物、景相互交融,似乎在隱喻這快速變化發展的新世界。在其人物畫創作中,人物形象被夸張變形,還被籠罩在五光十色的絢爛氛圍中。因為色彩的原因,畫面十分華麗,生動再現了香港眾生相和生活百態,這是畫家精心搭建的夢幻舞臺。
20世紀70年代以后,陳福善的繪畫創作進入了成熟期,繪畫形式除了紙本水墨外,還有拼貼、印拓、噴繪等,將西方的繪畫技法和水墨畫技法巧妙結合,充分體現了其在藝術創作中的融會貫通、自由無拘。他用豐富的想象力創造了自己的奇幻世界。除了技法的全面和多樣外,他表現的主題和內容也十分豐富。這一時期的作品與轉型期相比,塑造的幻境世界更為成功,構圖更為恣意,人物尺寸也更巨大,展示了一位成熟藝術家的自信,可以說是其“心象”的顯現。
陳福善最喜歡表現的還是山水、人物和動物。其山水畫中,多數是物、人、景相交織的,人的形象幻化在山形中,幻化在動物的身體里,是有依托的。當然,其也有大量單獨表現人物的作品,將人幻化成動物的形狀,五官變形,肢體夸張地擠在一起,富有裝飾感、設計感。陳福善喜歡畫長相奇怪的大魚,這些大魚有時是畫面的主體,有時是其他物象的承托。有學者稱陳福善的魚和莊子的蝶一樣,都是在一樣的自由之物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自由自在,瀟灑快活。還有一類是其晚年時期創作的抽象作品,表現為大色塊的組合、恣意潑灑的色點,完全是涂鴉式的,既受西方風格樣式的影響,又渾然天成地展現了東方的審美趣味。陳福善在創作成熟期用作品印證了自己對于抽象的定義,從畫所見所想發展為畫所知,其畫中表現的物象是從知覺中產生的,透露著畫家的人生觀和宇宙觀。在這些色彩斑斕的作品中,充滿了畫家對于生活和生命的熱愛,以及對于藝術創作、創新的熱情。
三、始知真放在精微
“始知真放在精微”是徐悲鴻為陳福善的題贈。陳福善確是一位致廣大、盡精微的藝術家,他的廣博多識和融會貫通在他的藝術創作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如其于1968年創作的紙本丙烯作品《無題·觀龍的人群》,這是一幅尺寸不大但張力很強的作品,丙烯顏料的質感和鮮明賦予畫面生猛感。畫面中主要塑造了人和獸的形象,怪獸被圍在人群中,靠近怪獸的人變形厲害,紫色、紅色的臉更像是半人半獸的形態。人們帶著從眾的心態蜂擁而上,投去好奇的目光,也有人興趣消失轉身離去。這種場景在生活的叫賣聲中屢見不鮮,畫家用詼諧的畫面再現了真實。畫面用色艷麗、對比強烈,夾雜著現代繪畫的制作技法,表現了現代社會的復雜。五光十色、擁擠喧鬧似乎是藝術家對香港社會生活的描繪,人、獸形象夸張、清晰明確,似乎是對另一種真實的再現,而非虛幻的想象。畫面中,人物形象各異,仿佛在暗示不同階層的人群,還有人的形象幻化在野獸的身體里。這樣一幅魔幻現實主義的肖像畫暗示著社會生活中復雜隱晦的一面,也表現出人與人之間密不可分的聯系,但畫中的趣味性為作品的批判意味做了掩護。
1976年所作的綜合材料拼貼作品《灣仔街景》代表了陳福善的另一種風格。在這一類風格的作品中,能夠看到許多西方藝術家的影子,但又無法明確指出究竟是誰的特點。可見,陳福善吸收眾家所長并化為己用,形成了個人具有代表性的風格。這張像是以攝影作品構圖的作品經藝術家之手變得更加有趣,畫面設計感、形式感十足,用色大膽,與同時代的作品拉開了距離。畫家用拓印的各色各狀的圖案進行拼貼,并用鮮艷明確的色塊加以連接,組成街景兩邊的建筑和所需結構。拓印的圖案以無意識的拱狀山形為主,色彩各異,畫面前方也有三塊類似山石的物體,藝術家或許是想將自然風景融入城市景觀。作品看似風格迥異,實則是藝術家對充滿變化的奇幻山水主題的另一種表達。
1983年的紙本彩墨作品《奇異的世界》已是陳福善成熟時期的作品。對于這樣一幅超現實中國山水畫,很難想象是一位近八十歲的老人所作。作品沿用陳福善代表性的三段式構圖,色調以夢幻的藍紫色為主,間以跳躍的紅、綠色,使畫面奇幻生動,神秘莫測。畫面底部是一組交錯的人物群像,他們造型簡約,色彩鮮亮,衣著圖案時髦,富有裝飾性。畫家有意把他們組織成山的形狀,以和畫面頂部的山相呼應。畫面頂部的山形更加寫實,能夠看出山體的脈絡,但畫家依舊“頑皮”地將人的形象巧妙融入其中。這一部分的人臉更加抽象和夸張,底色能夠看出吸收了單色版畫的制作技巧。在陳福善作畫的視頻資料里可以看出,他喜歡將墨涂抹在桌面上,再用宣紙拓印,以得到一些隨機的墨痕,而這些隨機產生的墨痕幫助藝術家促成了這些形狀。陳福善認為,這些隨機、潛意識下的行為有助于他的創作。上、下兩段充滿變化的山形由畫面中段的一條大魚連接,大魚直接又合理地出現在寬闊的海面,在擁擠的人群之間顯得格外氣定神閑。魚的形象是陳福善畫中最有代表性的元素之一,他在自述中曾表示,很喜歡看水族店門口魚缸里的魚,魚在水中悠然自得,和映射在魚缸上的人們匆匆而過的身影形成對比,反映了陳福善的人生態度。他喜歡在水族館駐足觀看,或買一些熱帶魚類的書籍來研究,想將畫面的主題從風景演變為海洋生物。有研究者認為,魚或許是藝術家本人的寫照,陳福善就是在這蕪雜世界中從容自得的那條發著五彩光的怪魚。大魚的上部用模仿印章的字體寫著“wonderland奇異的世界”,體現了陳福善早年的設計功底。作品右下角鈐兩方印,分別是福善、戲筆。
陳福善畫過許多以舞臺人物為主題的作品,有舞者、歌手、戲劇角色、演員、馬戲團等,這是由當時香港的文化氛圍決定的。那時正值香港影視行業的黃金年代,在電影中,人類在導演精心編織的故事的過程中滿足自己的幻想,彌補自己的遺憾,把想不到、不敢做之事統統在電影中得到滿足。電影為人類造夢,也深深吸引了藝術家的目光,所以陳福善將各種戲劇人物從舞臺搬到畫面中。在其筆下,人物形象更加夸張,本就在夢中的人物被再次放進虛構的畫面之中,更可謂“如夢之夢”,表現了這繁華世間的百態眾生相。
陳福善也畫各類展館、博物館主題的作品,其1984年的紙本彩墨作品《吃西瓜的人》就是這類主題的代表。圖中,一群人圍繞著一個放著西瓜的展示臺,但是只有站在展示臺前方、穿黃色西裝的人正在仔細端詳展示臺上的展品——西瓜,其他人都在向別的方向張望。這些觀展的人穿著各異,充滿組織感,色彩單純明麗,對比感強烈,好像在說藝術品在不懂它的人眼中就好像西瓜放在展示臺一樣可笑。可見,陳福善就像一個喜劇演員一樣,可以將悲傷的事情用詼諧幽默的口吻講出來。
四、結語
如果每個藝術家都有底色,那么陳福善的底色就是香港。他始終認為,自己就是大都市中的小市民,過著平凡的生活,感受著日新月異、城市變遷。香港城市生活的復雜和多元,使他作品中表現的香港風貌和社會生活格外豐富活潑、充滿變化。在陳福善看似聰明圓滑的外表下,是一顆對藝術堅定的心,所以其才能在同時代的藝術家中顯得分外獨特。他敏感地捕捉到社會變化和文化思潮的涌動并做出改變,更可貴的是,他雖受西方藝術影響較大,但在藝術作品中,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轉型后的作品中充滿了強烈的東方韻味和視角。
“藝術家可以利用和表現內心所需要的任何形式,藝術作品生根于神秘的內心里。”這是陳福善在文章中引述的康定斯基的話,他用一生的藝術創作誠懇踐行。他在作品中創造了一個超越時間和空間的幻象世界,那里如萬花筒一般讓人留戀,人、動物、自然山水生發轉化,樹和花隨意生長,不必遵循規律,動物隨意變形,不必遵循章法,現實與超現實結合,一派自由浪漫、光怪陸離的光景。陳福善封筆的前幾年,他的作品更是超越了之前作品中對物象的描繪,只剩下色塊和隨意潑灑的涂鴉般的筆觸,如1987年的布面丙烯抽象畫《天象圖》。畫家不再局限于對物象的表現,而是開始表現自我意識和宇宙觀,通過色彩和抽象的筆觸喚起觀者的情感和想象。他在82歲時因身體原因完全停止作畫,而這張作品正展現了一位終身學習、不斷創新直至生命終點的藝術家。在漫長的物理時間中,作品與觀者總會有對視的一刻,而藝術家的藝術生命將因觀者的目光得以延續,由此,其藝術生命便可無限延長。
參考文獻:
[1]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9.
[2]鄧海超.香港藝術概說[J].美術,1997(12):61-64.
[3]郎紹君.論中國現代美術[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88.
[4]馬敏.文化焦慮與精神失重:香港當代藝術的精神流變[D].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2008.
[5]劉瑩.滄海索珠:1960-1980年代香港現代水墨藝術研究[D].北京:中央美術學院,2016.
作者簡介:
劉紫微,哈爾濱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畫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