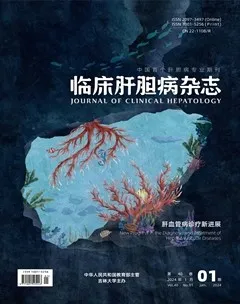胰腺導管腺癌行腹腔鏡下胰十二指腸切除術后早期復發(fā)的列線圖模型及其預測價值分析
劉 舜,謝 誠,劉亞輝
吉林大學第一醫(yī)院普通外科中心肝膽胰外二科,長春 130021
胰腺癌是全球癌癥相關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胰腺導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PDAC)是胰腺癌的主要類型。目前,PDAC 已成為美國癌癥相關死亡的第三大原因[2]。PDAC 的早期癥狀通常是非特異性的,因此大多數(shù)PDAC 患者確診時腫瘤已不可切除或發(fā)生轉移[3-4]。對于PDAC 患者,手術切除是唯一能夠提供長期生存的根治性治療,但只有約20%的患者可施行手術治療[5]。而在接受手術切除的患者中,5年生存率僅為15%~25%[6]。PDAC患者切除術后的早期復發(fā)是影響患者術后生存率的重要因素[7]。據(jù)報道[8-10],胰腺癌術后中位復發(fā)時間為10~12個月。因此,有效預測PDAC術后早期復發(fā),盡早采取針對性治療措施,對于患者預后至關重要。胰十二指腸切除術(pancreaticoduodenectomy,PD)是治療胰腺癌的標準術式,目前基于快速康復理念,腹腔鏡胰十二指腸切除術(laparoscopic pancreaticoduodenectomy,LPD)逐漸增多。與PD 手術相比,LPD 具有創(chuàng)傷更小,術后恢復更快等優(yōu)勢,因此在國內外廣泛開展,但探究PDAC 患者行LPD 術后的早期復發(fā)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仍然較少。本研究對行 LPD 的PDAC 患者進行分析總結,探究術后腫瘤早期復發(fā)的危險因素并構建早期復發(fā)預測模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收集2016 年4 月—2022 年7 月于吉林大學第一醫(yī)院行LPD且術后病理為PDAC的患者的臨床資料。納入標準:(1)術后病理確診為PDAC,術前未合并其他惡性腫瘤,可以耐受麻醉且術前未接受過針對PDAC 的各類新輔助治療。(2)術前增強CT 或MRI、PET-CT 提示,未發(fā)現(xiàn)腫瘤存在遠處轉移。術前經(jīng)血管三維重建評估腫瘤與周圍臟器解剖關系,預計病變可以完整切除的病例(腫瘤未侵犯腹主動脈、腸系膜上動脈和肝總動脈,或腫瘤未侵犯腸系膜上靜脈或門靜脈,或侵犯范圍≤180°但無靜脈邊緣不規(guī)則)[11]。(3)手術由同一術者完成。(4)患者術中快速病理與術后病理需滿足R0切除。(5)術后患者遵醫(yī)囑進行影像檢查和/或實驗室檢查形式的復查,密切隨訪。排除標準:(1)未遵醫(yī)囑復查者;(2)未能按計劃實施LPD 者(如術中轉為開腹手術或改行姑息性手術);(3)臨床病理資料、隨訪資料存在缺失者;(4)圍術期死亡患者:指患者在術后90 d 內死亡或在第一次住院期間死亡。
1.2 手術方式及圍術期管理 所有患者均由同一手術團隊完成,均采用“后入路、鉤突先行、動脈優(yōu)先”手術入路方式[12]。消化道的吻合重建采用Child 吻合方式,胰腸吻合的重建采用改良雙荷包胰腸吻合方式,并分別于胰腸、膽腸吻合口旁及腸系膜上靜脈旁各留置1 枚引流管。術后所有患者均給予抑酸,抑酶,抗炎,補液,補充白蛋白等對癥治療。
1.3 觀察指標(1)術前資料:年齡、性別、BMI、CA19-9、CA125、術前血清總膽紅素水平、是否患有高血壓、是否患有糖尿病、上腹部手術史、術前是否行膽道引流、美國麻醉醫(yī)師協(xié)會(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分級。(2)術中臨床資料:術中失血量、術中輸血情況、胰腺質地、胰管直徑。(3)術后臨床資料:胰瘺、膽瘺、腹腔感染、肺部感染、延遲性胃癱、術后出血發(fā)生情況、術后輔助化療。(4)病理學資料:腫瘤最大直徑、分化程度、是否存在淋巴結轉移、腫瘤是否有神經(jīng)浸潤或脈管浸潤。所有患者術中均未行血管切除吻合重建。術后出血[13]、膽瘺、延遲性胃癱等并發(fā)癥的定義及分級均依據(jù)相應的指南[14-16]。腹腔感染參考《胰腺術后外科常見并發(fā)癥診治及預防的專家共識(2017)》[17]診斷標準。目前,術后肺部感染判定標準尚未統(tǒng)一,本研究依照《醫(yī)院感染診斷標準(試行)》[18]及Clavien-Dindo分級[19]將肺部感染定義為:患者術后出現(xiàn)咳嗽、咳痰癥狀,影像學檢查提示肺部感染征象,實驗室檢查結果顯示白細胞計數(shù)明顯升高,和/或痰培養(yǎng)明確病原菌。依據(jù)《胰腺術后外科常見并發(fā)癥診治及預防的專家共識(2017)》[17]將術后胰瘺定義為:術后≥3 d 任意量的引流液中淀粉酶濃度高于正常血清淀粉酶濃度上限3倍以上。
1.4 術后隨訪 通過門診進行隨訪,患者前12 個月每3 個月復查一次,隨后每6~12 個月復查一次。在每次門診復查時,患者均行一次腹部和胸部CT、血常規(guī)、肝功能、腫瘤標志物等檢查,CT 平掃結果提示可疑復發(fā)時均行腹部/胸部增強CT確認病灶情況。本研究隨訪以腫瘤出現(xiàn)早期復發(fā)為終點事件。目前國內外針對PDAC術后早期復發(fā)并無統(tǒng)一標準,參考相關研究[20-24],本研究將PDAC 早期復發(fā)定義為:行 LPD 且術后病理回報為PDAC 的患者,術后規(guī)律復查過程中,通過影像檢查和/或實驗室檢查證實的手術區(qū)域新發(fā)(惡性)病變或遠處轉移,自手術后第1日起到確診復發(fā)的時間≤12個月[25]。復發(fā)的診斷以影像學檢查結果為主,同時參考腫瘤標志物(CA125和CA19-9)和臨床表現(xiàn),當臨床癥狀提示可能存在復發(fā)時,即行影像學檢查。隨訪截止日期為2023年8月31日,所有患者術后隨訪時間均>12個月。
1.5 統(tǒng)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6.0 和R 4.1.3 統(tǒng)計軟件進行數(shù)據(jù)分析。計數(shù)資料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精確概率法。Logistic 回歸分析影響術后早期復發(fā)的危險因素。采用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下面積(AUC)評估模型的區(qū)分度,AUC>0.75 為該模型有足夠的區(qū)分度。利用Bootstrap重采樣法隨機抽樣1 000次驗證,并利用驗證組再次驗證。使用校準曲線和Hosmer-Lemeshow 擬合優(yōu)度檢驗評估校準度,決策曲線(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評估臨床實用性。P<0.05為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共納入240 例患者,采用隨機數(shù)字表法,按照7∶3比例,分為訓練組(n=168)與驗證組(n=72)。其中男134 例,女106 例,年齡最大者為79 歲,最小者為27 歲,平均年齡(59.42±9.07)歲,BMI(22.8±2.9)kg/m2。所有患者均順利完成LPD,術中出血量為(263.29±131.39)mL,淋巴結清掃數(shù)目為(20.39±3.58)枚。240例患者術后均獲得隨訪,中位隨訪時間為17.23(3.10~91.70)個月。隨訪中,共102例(42.50%)術后早期復發(fā),其中腹腔內復發(fā)89例(肝轉移62例、術區(qū)轉移12例、淋巴結轉移15 例);腹腔外復發(fā)13 例(肺轉移10 例,骨轉移3例)。訓練組術后早期復發(fā)70例(41.67%),非早期復發(fā)98例(58.33%)。驗證組術后早期復發(fā)32 例(44.44%),非早期復發(fā)40例(55.56%)。兩組患者基線數(shù)據(jù)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值均>0.05)(表1)。

表1 訓練組和驗證組基線數(shù)據(jù)特征比較Table 1 Comparison of baseline data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raining group and verification group
2.2 PDAC患者LPD術后早期復發(fā)的單因素分析 在訓練組中,早期復發(fā)組和非早期復發(fā)組在術前CA19-9、腫瘤最大直徑、腫瘤分化程度、淋巴結轉移情況、術后輔助化療方面比較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值均<0.05)(表2)。

表2 PDAC患者行LPD術后早期復發(fā)單因素分析Table 2 Univariate analysis of early recurrence after radical LPD in PDAC patients
2.3 PDAC患者行LPD術后早期復發(fā)多因素分析 基于訓練組單因素回歸結果進行的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術前CA19-9 水平≥37 U/mL、腫瘤最大直徑>3 cm、腫瘤低分化、有淋巴結轉移、術后未行輔助化療是影響PDAC患者行LPD術后早期復發(fā)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表3)。

表3 PDAC患者行LPD術后早期復發(fā)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Table 3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arly recurrence after radical LPD in PDAC patients
2.4 建立列線圖模型 以術前CA19-9 水平、腫瘤最大直徑、腫瘤分化程度、有無淋巴結轉移、有無術后輔助化療為預測因素構建預測PDAC患者行LPD術后早期復發(fā)的列線圖,其中對預測復發(fā)影響最大的因素為腫瘤最大直徑(圖1)。

圖1 預測 PDAC患者行LPD術后早期復發(fā)的列線圖Figure 1 A nomogram predicting early recurrence after radical LPD with resectable PDAC
2.5 列線圖預測價值檢驗 該列線圖模型在訓練組中的AUC=0.895(95%CI:0.846~0.943,P<0.001),最佳截斷為0.270,學習率參數(shù)為0.201,敏感度為92.9%,特異度為73.5%,陽性預測為71.4%,陰性預測值為93.5%,該模型的區(qū)分度較好(圖2)。Youden指數(shù)計算列線圖最佳總分截斷值為248.894 分,≥248.894 分為早期復發(fā)高風險人群,<248.894 分為早期復發(fā)低風險人群。驗證組預測PDAC 患者發(fā)生LPD 術后早期復發(fā)的AUC=0.835(95%CI:0.741~0.930,P<0.001),最佳截斷為0.270,學習率參數(shù)為0.309,敏感度93.8%,特異度70.0%,陽性預測值71.4%,陰性預測值93.3%(圖3),表明預測模型準確度良好。

圖2 列線圖預測 PDAC患者行LPD術后早期復發(fā)的ROC曲線(訓練組)Figure 2 The nomogram predicts the ROC curve of early recurrence after radical LPD with resectable PDAC(Training group)

圖3 列線圖預測 PDAC患者行LPD術后早期復發(fā)的ROC曲線(驗證組)Figure 3 The nomogram predicts the ROC curve of early recurrence after radical LPD with resectable PDAC(Validation group)
對訓練組構建的模型行Hosmer-Lemeshow 檢驗,結果顯示擬合良好(χ2=11.529,P=0.173),驗證組Hosmer-Lemeshow 檢驗結果為(χ2=3.489,P=0.836),利用Bootstrap重采樣法隨機抽樣1 000次對模型進行驗證,校準曲線中標準曲線與校準預測曲線基本貼近(圖4、5),表明列線圖預測的早期復發(fā)與實際的早期復發(fā)的一致性良好。

圖4 PDAC患者行LPD術后早期復發(fā)的校準曲線(訓練組)Figure 4 Calibration curve for early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of radical LPD with resectable PDAC(Training group)

圖5 PDAC患者行LPD術后早期復發(fā)的校準曲線(驗證組)Figure 5 Calibration curve for early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of radical LPD with resectable PDAC(Validation group)
DCA 分析顯示該模型在訓練組及驗證組中具有明顯的正向凈收益,表明列線圖具有較好的臨床應用價值(圖6、7)。

圖6 PDAC患者行LPD術后早期復發(fā)的決策曲線(訓練組)Figure 6 Decision curve for early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of radical LPD with resectable PDAC(Training group)

圖7 PDAC患者行LPD術后早期復發(fā)的決策曲線(驗證組)Figure 7 Decision curve for early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of radical LPD with resectable PDAC(Validation group)
3 討論
雖然針對可切除胰腺癌的LPD 技術已經(jīng)成熟,但術后仍有超過50%的患者出現(xiàn)腫瘤早期復發(fā),嚴重影響患者術后生存質量[26-31]。
本研究用于構建模型的訓練組中,早期復發(fā)組患者和非早期復發(fā)組患者在年齡、性別、BMI、是否患有高血壓、是否患有糖尿病、上腹部手術史、術前總膽紅素、術前膽道引流、ASA分級、術前CA125、術中失血量、術中是否輸血、胰腺質地、胰管直徑、胰瘺、膽瘺、術后腹腔感染、術后肺部感染、延遲性胃癱、術后出血、腫瘤是否有神經(jīng)浸潤或脈管浸潤方面進行比較,其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兩組數(shù)據(jù)均衡可比。單、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術前CA19-9 水平≥37 U/ml、腫瘤最大直徑>3 cm、腫瘤低分化、有淋巴結轉移、術后未行輔助化療是影響PDAC患者行LPD術后早期復發(fā)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
CA19-9 是目前評估胰腺癌最理想的生物標志物和異常糖基化的指標,其在胰腺癌中具有生物標志物、預測因子和啟動劑的多重作用[32]。研究[33-37]表明,CA19-9升高提示腫瘤具有較高的惡性生物學行為,是PDAC 術后復發(fā)的可靠證據(jù),與本研究結果提示術前CA19-9 水平>37 U/mL 可影響PDAC 早期復發(fā)的結論一致。既往研究[38-40]表明,腫瘤大小與腫瘤預后及術后復發(fā)關系密切,隨著腫瘤體積增大,其侵襲能力及惡性程度也不斷增加,術后更易出現(xiàn)復發(fā)轉移。本研究結論中的腫瘤最大直徑>3 cm的患者表現(xiàn)出了更高的早期復發(fā)風險,亦支持上述觀點,且與Imamura 等[24]的研究結論相符。分化程度更低的腫瘤往往具有更強的侵襲性和轉移傾向,低分化的原發(fā)腫瘤也被認為是術后復發(fā)的獨立影響因素[34-41]。本研究表明,腫瘤分化程度越低,早期復發(fā)風險越高,與既往研究結論一致。因此,當術后病理報告提示低分化時,應警惕PDAC 術后早期復發(fā)可能。淋巴結轉移是公認的影響胰腺癌切除預后的重要因素[42],國際胰腺外科研究小組[43]建議胰腺癌根治術中應至少清掃15 枚淋巴結,本研究結論也表明有淋巴結轉移的患者術后早期復發(fā)風險明顯增加,因此術中徹底清掃淋巴結并確認是否存在淋巴結轉移對于患者預后極為重要。PDAC 惡性程度高且術后易復發(fā),本研究結果提示根治術后行輔助化療可有效降低早期復發(fā)風險。國內外多部胰腺癌診治指南[11,44-45]建議根治術后的胰腺癌患者如無禁忌證,均應行輔助化療,本研究結論一致。
本研究基于以上獨立危險因素建立的列線圖模型(AUC=0.895,95%CI:0.846~0.943,P<0.001)具有良好的區(qū)分度,校準曲線和Hosmer-Lemeshow 檢驗評估校準度良好,且在訓練組及驗證組中均具有明顯的正向凈收益,表明列線圖具有較好的臨床應用價值,在臨床實踐中可以綜合分析影響患者術后腫瘤早期復發(fā)的風險,有助于指導臨床醫(yī)師制訂個體化的腫瘤綜合治療方案,預防術后早期復發(fā),改善患者預后。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為單中心回顧性的非隨機化研究,研究樣本量較小,具有一定局限性,希望后續(xù)能夠開展大樣本量的多中心研究并延長隨訪時間以進一步驗證模型有效性。
倫理學聲明:本研究方案于2023 年11 月30 日經(jīng)由吉林大學第一醫(y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批號:(2023 年)臨審第(2023-708)號。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不存在任何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劉舜負責設計研究框架、數(shù)據(jù)收集、統(tǒng)計學分析、起草論文;謝誠負責數(shù)據(jù)收集、統(tǒng)計學分析、繪制圖表;劉亞輝負責擬定寫作思路,論文修改,指導撰寫文章并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