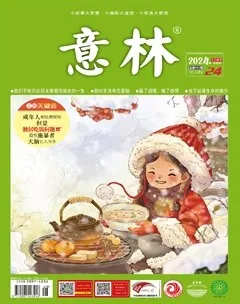為得到父母認可,我瘋狂較勁的前半生
碩士畢業(yè)后,我去了一家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畢業(yè)一年多,我實現(xiàn)了經(jīng)濟獨立,把自己的生活過得還算有聲有色,也有了回饋親人的能力,屬于“累并快樂著”。但在父母看來,選擇這樣一份離家不近又不夠穩(wěn)定的工作,我無疑是極不明智的。
前幾天視頻通話時,媽媽又用同齡人的經(jīng)歷來質(zhì)疑我的決策:“你堂姐那時候一畢業(yè)就考了編制,還有你表妹,回老家當高中老師,都很穩(wěn)定又體面……”視頻那頭,媽媽細數(shù)著“別人家孩子”的清醒與懂事,臉上寫滿了恨鐵不成鋼。
這熟悉的話語和表情與我記憶中的畫面重合了,因為從小到大,父母曾無數(shù)次用“別人家的孩子怎么就……”這樣的句式來教育我。對此,我已經(jīng)徹底“免疫”,如今的我堅信,別人選擇了怎樣的職業(yè)道路與我無關,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我要做的是專注地探索自己的人生方向。
今年25歲的我在一個熱鬧的小鎮(zhèn)上長大,光是我家所在的那條街上,就有十幾個與我年齡相仿的孩子,我的父母有一雙極其擅長發(fā)現(xiàn)孩子身上閃光點的眼睛,但不幸的是,我并不是其中一員,成長過程中,我很少得到他們的表揚。

我家屬于高期待家庭,尤其是對我的學業(yè)表現(xiàn),父母一直寄予厚望。從我踏入校門的第一天起,父母就開始將我與同學做對比,從寫作業(yè)與背書的速度,到期末的成績單與獎狀。但凡有一個人表現(xiàn)得比我好,父母便會嚴肅地對我說:“別人能做到的,你為什么不行呢?一定是沒有用心,要不然就是你比他們笨。”
被狠狠訓斥幾次之后,自尊心極強的我很不服氣,每天不完成作業(yè)以及復習、預習任務絕不休息,寒暑假就把接下來一學期的背誦內(nèi)容全部背熟,上課時也始終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我的努力很快就得到了回報,成了街區(qū)捧回獎狀最多的孩子,并且在此后的求學生涯中總是名列前茅。
本以為,這下父母一定沒有理由再用別人家的孩子來教訓我了,可他們將注意力從學業(yè)轉(zhuǎn)移到了其他方面,總是對我強調(diào):“只有學習成績好有什么用?”鄰居家的姐姐非常體貼父母,總是主動做各種家務;表姐很有藝術天賦,“隨手”一畫就能在全市的繪畫比賽中得獎;小賣部老板家的孩子口才讓我望塵莫及……在他們的口中,我的木訥與笨拙仿佛嚴重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每回聽到這些話,我內(nèi)心都會有一種強烈的挫敗感:“難道我就沒有獨特的閃光點嗎?為什么總是拿我和別人比?”他們的回答總是:“人要有上進心,當然要和優(yōu)秀的人比。”
希望得到父母認可的我決定采取“逐個擊破”的戰(zhàn)略,他們夸獎誰,我就向誰看齊,努力做得和他們一樣好。如果沒有,我就會陷入懊惱和自我懷疑。
記得我讀小學五年級時,家對面搬來了一戶新鄰居。這家有一對雙胞胎女兒,她們的父母也很嚴格,要求她們每天早上六點半起床早讀。目睹這一情況的父母自然毫不吝嗇對她們的表揚,并表達了對我的不滿:“你怎么就沒有人家的那份毅力?”
于是,很不服氣的我也開始早起。每天一睜開眼,如果發(fā)現(xiàn)時間已經(jīng)超過六點半,我的瞌睡蟲就會瞬間消失。寒假時,我非常不想離開溫暖的被窩,但一想到父母可能又會念叨我不如她們有毅力,起床的動力立刻就滿了。直到有一次,我們的父母聚在一起閑聊,我才得知,在她們家,我也是“別人家的孩子”,總被她們的父母拿來鞭策她們。
后來,這對姐妹轉(zhuǎn)到了市里讀初中。做了長達一年多的鄰居,我們并沒有說過幾句話,而是在父母的比較之下把對方當作假想敵,互相較勁,看向彼此的眼神總是很復雜。我還有一位非常要好的玩伴,也是因為她的父母總夸獎我而貶低她,逐漸與我疏遠了。這些經(jīng)歷讓我明白,成為“別人家的孩子”很多時候并不是一件令人驕傲和愉快的事,它同樣會讓我們感到尷尬和苦惱。
這些年來,關心我的老師和好朋友對我的評價高度一致:非常要強、力爭上游、總是焦慮。升入高中,我所在的重點班優(yōu)等生很多,父母的目光都會集中在前幾名的身上,感嘆他們的聰明與努力。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開始急躁和懷疑自己,甚至對成績優(yōu)于我的同學產(chǎn)生一種微妙的敵意。
被這種情緒困擾的我意識到,自己不能再保持這種不健康的心態(tài),于是下定決心改變。復盤這些年的經(jīng)歷,我發(fā)現(xiàn),父母的比較是永無止境的,而我根本無法成為一個十項全能的人,完美契合他們對我的期望。我理解他們“望女成鳳”的心理,也知道為了我的成長,他們付出了很多心血。但人生不是一場競技比賽,如果永遠活在與別人的比較中,我會過得非常疲憊。
父母用“別人家的孩子”來激勵我,初衷自然是希望我能蛻變成更好的自己。不可否認的一點是,為了求得他們的認可,我養(yǎng)成了良好的學習和生活習慣,勇于嘗試很多新技能。但在這個過程中,一次次被否定的失望和委屈讓我覺得,自己是不被父母接納的,與他們的心理距離越來越遠。其實,如果他們能夠用更加平和與積極的方式表達對我的期望,一定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好在,想清楚以后,我再也沒有和父母眼中“別人家的孩子”較勁過,而是專注于自己的成長。前者對我來說好像在攀一座沒有頂峰的山,一心只想著往上走,無暇停下來欣賞沿途的風景;后者卻像養(yǎng)一株花、種一棵樹,耐心施肥澆水等待花繁葉茂的過程,比任何人的認可都讓我更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