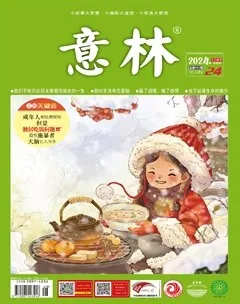我們不能只在朋友圈看完彼此的一生
上周末,一個研究生同學來找我。離開了校園,我們兩個的生活方式也漸漸變得不太一樣。她性格外向,愛與人相處。她問我一般周末都是怎么過。我說,我一般周末就一個人在家,看書或者看電影。她問:“你沒有朋友嗎?”這個問題真是把我難住了。
說沒有吧,我覺得有些難為情,對年輕人來說,交友關系是證明自我存在的重要表現。說有吧,我又有些心虛,到底什么樣的關系才能稱為“朋友”呢?
或許是性格的原因,我是那種看起來友善,卻總是獨來獨往的人。待人友善是修養,獨來獨往是性格。修養可以假裝,性格卻很難改變。
當然,知心的朋友也有幾個,但他們就像“隱形人”一樣,平時感覺不到他們的存在,只有當我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們才會現身。然而,我的生活中并沒有太多急需別人幫忙的時刻,所以,獨自一人就成了我生活的常態。
隨著年齡的增長,很多問題已經不愿意多做解釋,所以,對于這樣的問題,我只是回答:“有啊,但是他們都很忙。”
她對這個答案好像并不滿意,但也沒有深究下去。
中午,我在廚房做飯,她在客廳參觀我的書架。參觀之后,她的評價是:“你看的書很消極,你寫的文章也很消極。”她所謂的消極,是指我的書架上沒有標題很正能量的書,相反,書的標題都透著一股“喪”的氣息。說我看的書太“喪”我無法反駁;說我寫的文章消極,我倒是可以辯解幾句。
首先要說這幾年來我的生活過得確實不太如意,每當我有寫作沖動的時候,往往都是我遇到坎坷的時候。
寫作對于一個人來說意味著什么?在《芒果街上的小屋》中,有一位快死的嬸嬸這么告訴特蕾莎姑娘——寫下去,一定要寫下去,那會使你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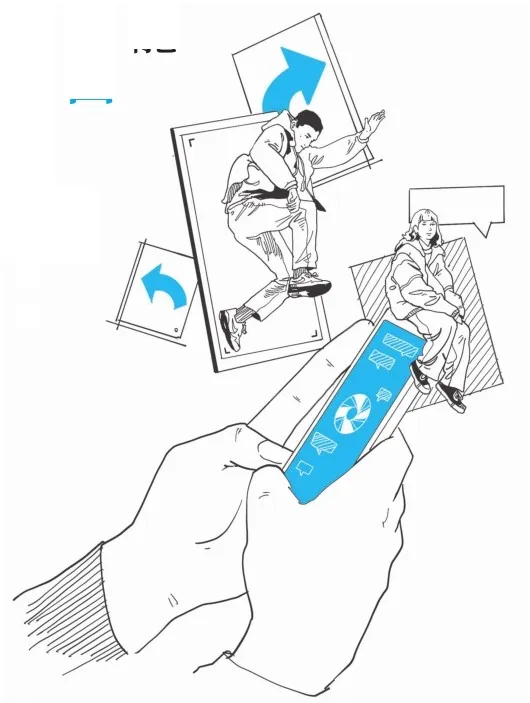
在一個沒有記憶和沒有夢想的地方,文字,是“那一小撮”人拯救自我的唯一方式。
是的,我當然希望成為一把砍向內心大海的冰鎬,通過寫作給周圍的人帶來鼓勵,不是通過記錄生活中那些偶爾發生的讓人高興的事,而是通過那些時常發生的不怎么讓人愉快的事。
吃完飯,我們自然去了學校。畢業之后,我幾乎沒有離開過校園,對它的一草一木非常熟悉。雖然她離學校也只有一個小時的路程,卻一次也沒回來過。我一路給她介紹校園發生的變化,她像個孩子一樣興奮,不停地拍照,也不停地讓我幫她拍照。走出校園的時候,我們兩個的手機里都是她的照片。回到家,她開始整理照片,選出一些滿意的發朋友圈。我從她的朋友圈里選了幾張存在了手機里。
她問我為什么不發朋友圈。我說不知道該說點啥。于是,她又得出一個結論:你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狀態分享給朋友。一天被她揭露了兩次,真的心好累。
消極,獨來獨往,不知道其他的朋友對我是不是也是相同的評價。其實我也沒有那么凄慘。不發朋友圈的日子,我花了很多時間跟家人交流,一個人的時候就看書、健身、看想看的電影,豐富自己的生活。回過頭來看,我的朋友圈識別度確實太低,從中完全勾勒不出一個人生活的樣子。也難怪關注我朋友圈的人有些擔心。
只是我們什么時候開始用朋友圈去定義一個人了呢?有了朋友圈之后,我們似乎對朋友了解更多,但也有可能更少。我們不能只在朋友圈看完彼此的一生。有時候我也會擔心那些淡出朋友圈的人現在過得好不好,他們越是不發朋友圈,我越是對他們牽掛,也越在意他們發出的只言片語。
很多人覺得,每一個不發朋友圈的人背后,都會有一個故事。其實也未必,或許他們只是懶而已。熱愛生活,沉浸于生活本身的人和事,才是生活的真諦,這與發不發朋友圈并沒有太大的關系。
《頭號玩家》最后的結局是,綠洲每周關閉一天,人們在那一天里遠離網絡,跟朋友在一起。朋友圈似乎也應該學一學,每周至少有一天,你的朋友不再只是朋友圈里的一個符號。
所以,不要通過網絡判斷我過得好不好,有本事來我家親自確認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