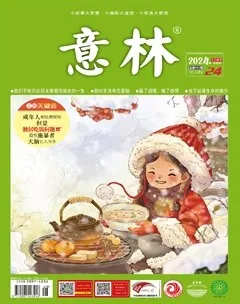回鍋肉:歸家的號角
日劇《我,到點下班》的開篇,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的白領(lǐng)東山結(jié)衣就迎來了一個頓悟時刻。
結(jié)衣下班后常去公司附近的上海飯店喝特價啤酒,總會碰見在另一張桌子上吃回鍋肉的大叔。這天老板娘對著空蕩蕩的桌子告訴她,回鍋肉大叔每次吃完飯都要回公司加班,前些天干了個通宵,早上同事在工位上發(fā)現(xiàn)了他的尸體。
總是加班的大叔,愛吃回鍋肉這樣油脂豐盛、咸香帶辣的下飯菜,結(jié)衣看到的是職場苦主的灰暗人生,我卻像是在照鏡子。同樣視回鍋肉如命的我,回憶起這段故事,都會提醒自己,要珍惜還能享用回鍋肉的這條小命。
回鍋肉大叔在“中華料理”館子吃的那份“回鍋肉(ホイコーロー)”,肉片粗厚硬挺,精瘦無神,盤中汁水橫溢,汪在一起,大叔卻吃得津津有味。回鍋肉作為當初川渝袍哥初一十五打牙祭的家常菜,本不拘一格,但還是有下限。有的菜雖然在字面意義上也能稱作回鍋肉,但在食物分類學上應(yīng)該劃為不同的物種。

媳婦學做過一次回鍋肉,像模像樣的,后來自信心爆棚便開始超常發(fā)揮。她不知是自己琢磨出來的,還是看美食博主花了眼,信奉了“萬物皆可回鍋”的假說,不時將吃剩的排骨、醬肘子、豬頭肉或者牛肉均按回鍋肉的工藝流程炒制,雖然沒有浪費肉,但浪費了充當配菜的無辜蒜苗。
汪曾祺在西南聯(lián)大念書時有“刀子一樣的胃口”,也對食堂半生不熟、極多豬毛的回鍋肉難以下咽。炒制雖繁,食材不彰,物力不齊,做法潦草,都算不得佳肴。
我時常幻想等將來發(fā)達了,我也要像回鍋肉大叔那樣天天吃、頓頓吃。肉要來自四川內(nèi)江一帶出產(chǎn)的黑毛豬,肥四瘦六的豬臀尖,絕對不用五花肉,因為五花肉入口綿黏化不了渣。煮肉去腥還是要靠漢源貢椒,六成熟起鍋。配菜只用初秋時節(jié)成都溫江的軟葉蒜苗,此時香味最濃郁,佐料千萬不能少郫縣的豆瓣醬和犀浦醬油。炒的時候,肉切薄爆炒至卷曲,豆瓣醬炒熟后先下蒜苗頭再下蒜苗葉,才能青翠分明,紅火得當,筷頭拈起來忽閃忽閃,搖曳生姿。這樣一份有鄉(xiāng)愁有節(jié)氣的米其林三星回鍋肉,吃完能讓我義無反顧地加班。
別看我從小看《中華小當家》動畫片、玩《料理媽媽》的電子游戲長大,能用文字翻炒回鍋肉,用御廚思維收羅天下食材,真拿起鍋鏟,只會出產(chǎn)黑暗料理。
單位食堂有時也會做一盆所謂的“川香回鍋肉”——“川香”完全靠老干媽實現(xiàn),肉過油太猛變成肉干,混著芹菜、甜椒和木耳,放入口中如同嚼柴火。
我曾在全北京城探尋最完美的那一例回鍋肉,幾家知名的川菜館子拋卻傳統(tǒng)、擁抱創(chuàng)新,四季換著“俏頭”(配菜)炒回鍋肉,春天用竹筍,夏天配苦瓜或子姜,秋季放藠頭,冬季又回到冬筍,就是不見老搭檔蒜苗的影子。
后來,我終于在一家“巴蜀酒樓”找到了“夢中情味”,專程吃了幾回。在我快把這家飯店當作食堂之際,不料風云突變,有記者去那家飯店臥底了個把月,寫了篇讓人倒盡胃口的曝光長文。飯店后廚的衛(wèi)生狀況令人作嘔不說,他們還給暖氣片開了口子,冬天用添加了防腐劑、抗垢劑的暖氣水清洗餐具,為回鍋肉們添加了獨家秘方。
追尋完美的食物到底是鏡花水月,所謂“食無定味,適口者珍”,完美的回鍋肉只存于一時的心境,一地的風物,以及取決于食客的饑餓程度。我的孩子們在北京長大,熱衷于牛羊肉,不嗜麻辣,媳婦又減鹽控糖,我與回鍋肉也漸行漸遠,只求一年中能偶遇兩回,解解心饞。
尋來找去,驀然回首,我也迎來我的頓悟時刻,世上是否真的存在“完美”的回鍋肉?如果有,它在哪里?
日本大叔吃的那款回鍋肉據(jù)傳是四川籍的廚師陳建民創(chuàng)制的,其中放包心菜而不是蒜苗,是因為當初陳大廚在日本很難買到蒜苗,口味方面也減輕了辣味,加了甜面醬,成了甜咸口。
人對食物頑固的偏好類似小雞小鴨“印隨”的行為模式,味覺第一次得到刺激的記憶能相伴永遠。電影《美食總動員》里,讓毒舌的美食評論家科隆瞬間夢回童年的蔬菜雜燴(ratatouille),也是再普通不過的法式一鍋燉,廚師可按個人喜好選用蔬菜,增減香料。可只有小鼠大廚這一款,能讓科隆回到那個遙遠的黃昏,放學途中和小伙伴干了一架,自己落敗回家,沮喪不已,幸好還有媽媽的疼愛和蔬菜雜燴的安慰。
完美的回鍋肉不過是小時候的味道。在學校迷迷糊糊學了一整天,在嬉戲打鬧中耗盡卡路里,放學歸家,腹內(nèi)空空,一盤蒜苗回鍋肉上桌,我能埋頭先橫掃一碗米飯,盤底積油拌飯再干一碗,蛋白質(zhì)、熱量、維生素、膳食纖維,全部滿足,味道、心境、時機、人和,也一樣不缺。
可惜,如今媽媽遠在四川老家,那完美的回鍋肉雖是催促我歸家的號角,卻也是始終求之不得的狂喜和無窮無盡的遺憾。套用紀錄片《早餐中國》里的一句解說詞:“我自問這輩子沒做過壞事,除了忽略媽媽做的回鍋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