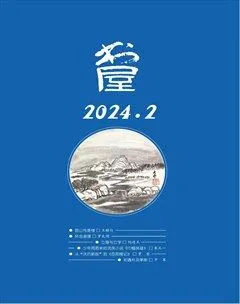揮斥風云 陶熔眾妙
鹿耀世
張正宇,1904年出生于景色秀麗的江蘇無錫。孩提時期,家鄉那異彩紛呈的民間美術和敦厚樸實的風情習俗就吸引著、陶冶著他的性靈,于是他很早就顯出了藝術天賦。后天的博覽苦學、孜孜以求,又使他無師自通,具有了獨具一格的創作能力。他的老朋友黃苗子曰:“正宇于二十年代隨其兄光宇在上海學徒,旋以漫畫名,其后從事為裝飾藝術、為舞臺設計、為山水窠石小品,晚年為篆隸、為擘窠狂草,莫不超凡出眾,卓然成家。”
張正宇的書法,先以隸字打下堅實的筆法基礎,而后,又辛勤地跋涉于真行草篆各種書體之中。他認為,書家離不開研讀、臨摹碑帖,但只有善于由“生”到“熟”而又敢于由“熟”到“生”的人,方能陶冶百家,獨辟蹊徑,自成格局。如果泥古不化,以精熟某種書體為滿足,必然落入前人窠臼。為了避開墨守古人成法、不越雷池一步的“俗書”小道,張正宇不追求一筆一畫酷似哪家家數,不囿于某種字體定型的間架結構,而是以“筆墨當隨時代”為座右銘,敢于熔各種書體于一爐,并以繪畫的經營位置、骨法用筆和民間藝術的裝飾手法,豐富了書法的布局結構與用筆,形成了險峻雄奇、豪放不羈的風格,表現出難能可貴的開拓精神。
我國的書法起源于象形文字,歷來亦有“以書入畫”“書畫同源”之說,張正宇是深知個中三昧的,他的字既有繪畫中俊逸流暢的線條、雄渾濃重的酣墨,又有筆筆送到的書寫功力。他書寫的石濤詩句“畫法關通書法律,蒼蒼莽莽率天真,不然試問張顛老,解處何觀舞劍人”,用筆遒勁、結體灑脫自如,布局既顯得毫不經意,又確實妥帖舒展,毫無刻板之弊。篆書聯“山隨畫活,云為詩留”的“山”字結體巋然不動,“隨”字運筆活潑輕捷,“畫”字氣勢凝練厚重,“活”字造型流動感強。下聯與上聯的對仗、呼應十分講究,八個字的安排輕重疾徐有致、濃筆枯墨相間,形成了鮮明的節奏和韻律,使人們得以領會書畫大家的寫意手筆。
他的草篆集鐘鼎、甲骨等書體的凝重、剛健、峭拔于一身,廣采旁糅、融會貫通,在前人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突破。他常常書寫的“江山多嬌”“山舞銀蛇,原馳蠟象”“高山流水詩千首,明月清風酒一船”等名句,都酣暢淋漓地發揮了每個字體的象形特點和整體的豐富內涵,賦予了古老的篆字以嶄新的生命。有的擘窠大字,宛若奇峰迎面,具有“勢崩騰兮不可止”的氣概。
張正宇有此成就,有人認為是“天分高”,可至近的朋友們都知道,他的勤奮不是常人所能比的。為了揣摩一種書體的間架,他往往伏案幾個小時反復揮毫,以至于積稿盈尺;為了捕捉小動物的形態,他在速寫的基礎上進行墨色暈染、線條勾勒、裝飾變形等多次實踐,才拿出初稿。在他七十余高齡的時候,有時還像個小學生一樣,用元書紙伏案臨寫《張黑女碑》。這正如黃苗子在他作品上的題記:“張正宇書畫不純出于天賦,古今中外凡藝有一長而為正宇服膺者,必苦探窮索、務擷其神髓以為己用。其鉆研甚苦,然論者謂正宇畫往往一揮而就,謂之天分高。正宇時亦昂頭白眼謂‘絕藝無關于學力’。實則正宇此言乃故作狡獪以戲無識者耳。近者天才論大白于天下,正宇亦不為是妄言矣。正宇畫能汲前人之長然必破古人以代替一己之創造。”張正宇還有這樣的習慣:在他寫字作畫時,喜歡摯友在左右圍觀,自己則高談闊論、旁若無人。揮毫至得意處,常常情不自禁地高呼:“贊格!”(無錫方言妙哉的意思)場面十分活躍,旁觀者興趣更濃,自己下筆也得心應手、極有神采。
張正宇的花鳥、動物、山石等寫意小品也風格鮮明、自成天趣。他雖師承徐青藤、齊白石,但銘記著白石老人“似我者死,學我者生”的名言,執著地走自己的路。他畫的貓,筆墨簡約豪放,但不粗疏怪異,不論是怒眼圓睜、昂頭遐想,還是笑容可掬,都有著獨特的藝術性和令人喜歡的稚拙的詩意美。他畫的《墨荷》《葫蘆》等小品不僅構圖、落墨大膽潑辣,墨色暈染也極有層次、有法度,一掃陳陳相因的平庸習氣。在落款、印章的安排上,也和畫面緊緊相依、相得益彰,很有裝飾美感。張正宇所作十二生肖水墨畫、剪紙及其他裝飾小品均構思奇絕、變形新穎、韻味十足。
在我國藝苑中,能純熟地掌握傳統筆墨技法的書畫家并不鮮見,但像張正宇先生那樣既師傳統又師造化,更從傳統和造化的法則中解放出來,在一系列作品中獨樹一幟地表現自己的藝術個性,則是非常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