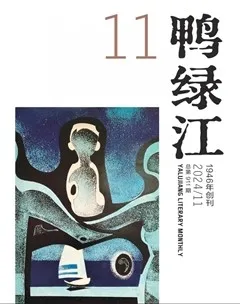郭沫若考察殷墟及安陽工作站題詩賞析
1899年甲骨文的發現,是中國古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節點。甲骨卜辭的相關研究證明,河南安陽小屯一帶即商王盤庚徙殷之所在。卜辭中的稱謂亦與典籍記載的商王世系相合,殷代王統得到地下出土文物的證明,這將中國的信史時間大大提前,從而對當時的“中國文化西來說”及近代疑古之風形成了有力反駁。1928年,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組,開始對殷墟進行系統的發掘、研究,這也標志著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誕生。新中國成立后,殷墟考古進入全新時期。1958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建安陽工作隊,并于1959年在小屯村修建了工作站。同年4月份,工作隊在安陽后岡南坡發現了一個圓形殉葬坑,“圓坑葬”系首次發現,這引起了歷史學家郭沫若的注意。
1959年5月29日,郭沫若出京參觀,歷經安陽、鄭州、洛陽、西安、太原等地,7月11日返京,其間得詩若干,輯為《豫秦晉紀游二十九首》發表。其中關于6月30日殷墟之行者有兩首:《訪安陽殷墟》《觀圓形殉葬坑》。第一首《訪安陽殷墟》手稿現藏安陽殷墟博物館,詩及小注內容如下:
我來洹水憶殷辛,統一中州賴此人。
百克東夷身致殞,千秋公案與誰論?
——一九五九年六月來安陽書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考古調查隊 郭沫若
此詩有多種版本,文字略有差異。《豫秦晉紀游二十九首》小輯最初發表于1959年7月18日《光明日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的《郭沫若年譜長編》誤寫為《人民日報》),其中,《訪安陽殷墟》第二句為“統一中州始此人”。1959年收入《潮汐集》,差異更大:“偶來洹水憶殷辛,統一神州肇此人。”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時,則為“偶來洹水憶殷辛,統一神州賴此人”。2017年版《郭沫若年譜長編》則為“我來洹水憶殷辛,統一中原賴此人”。如上,各版本差異主要集中于詩的前兩句,是“我來”還是“偶來”?是“中州”“神州”還是“中原”?是“賴此人”“始此人”還是“肇此人”?殷墟博物館所藏為手稿祖本,而各發表出版本出現訛誤,或是同一作品有不同手稿而出現多種異文?這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學術問題。
詩中的“此人”“殷辛”,即商朝末代君王帝辛,其人多以暴虐的“殷紂王”形象存在于歷史文獻中,如酒池肉林、炮烙酷刑、剖腹取心、鹿臺自焚等負面事件,皆與之有關,歷史上口誅筆伐者甚眾。但郭沫若此詩卻意在作翻案文章:帝辛征服東夷,統一中州,是對中國歷史有巨大貢獻的人物。1958年11月,毛澤東也表達過類似觀點:“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錯誤的,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58頁)當然,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的影響只是一方面,郭沫若對古史素有專門研究,早在1945年出版的《青銅時代·駁〈說儒〉》中,已經設專節《殷末的東南經略》為帝辛抱不平了:“這人被周及以后的人雖說得來萬惡無道,儼然人間世的混世魔王,其實那真是有點不太公道的。人是太愛受人催眠,太愛受人宣傳了,我們是深受了周人的宣傳的毒。”郭沫若不僅肯定紂王自焚的英雄氣概,而且根據殷墟卜辭的研究,以歷史學者的“持平”態度肯定紂王經營東南對于中華民族的意義:“中國南部之得以早被文化,我們是應該紀念殷紂王的。”
《豫秦晉紀游二十九首》組詩的第二首長詩《觀圓形殉葬坑》,基本上重述了《殷末的東南經略》一文中的觀點,也可以說是對《訪安陽殷墟》一詩的注釋。相關詩句如:“勿謂殷辛太暴虐,奴隸解放實前驅。東夷漸居淮岱土,殷辛克之禍始除。……武王克殷實僥幸,萬惡朝宗集紂軀。中原文化殷創始,殷人鵲巢周鳩居。但緣東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漸開化,國焉有宋荊與舒。……殷辛之功邁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須。殷辛之名當恢復,殷辛之冤當解除。……方今人民已作主,權衡公正無偏誣。誰如有功于民族,推翻舊案莫踟躕。”詩語流暢直白,不難見出,郭沫若高度肯定殷辛對于中國版圖一統的奠基功績,也對周人滅商、鳩占鵲巢后又詆毀殷辛的行為進行了批評與反思:新興政權往往極言前王之惡,后世附會侈陳,遂致臆說失真,這可以說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
1959年前后,郭沫若做的翻案文章實在不少,為紂王翻案只是其中之一。1959年2月3日至9日,郭沫若完成歷史劇《蔡文姬》,將“白臉”曹操塑造成一個愛惜人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3月14日做文章《替曹操翻案》,主張“今天我們要從新的觀點來追求歷史的真實性,替曹操翻案;而且還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歷史人物,如殷紂王,如秦始皇,翻案。只有在人民做了主人的今天才有可能。”7月1日郭沫若考察洛陽龍門石窟、白馬寺等地后,賦詩曰:“武后能捐脂粉費,文章翻案有新篇。”1960年1月10日完成話劇《武則天》,果真將武則天塑造成一個具有杰出政治才能的正面人物,而初唐四杰之一駱賓王,則被塑造為“徒有才藝而無器識”的無行文人。郭沫若為系列歷史人物翻案,固然源自其辨偽求真的史學精神,另一方面也是時代精神的體現:新的時代主體自信掌握了科學的歷史觀,睥睨古今,改地換天。
盡管爭議頗多,郭沫若不失為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卓越人物,他在文學、史學、考古學諸領域都有重要貢獻。在豐厚學養的滋潤之下,郭沫若在書法上也有巨大成就,可稱大家。解放后,郭沫若身為國家文化、教育、藝術諸領域的領導人,經常到各地考察,為名勝古跡、機構團體留下了大量墨跡,其書跡幾乎遍見于全國。郭沫若書法以行草見長,世人譽為“郭體”。《訪安陽殷墟》手稿系行草寫就,風格蒼老古樸。觀其筆法,線條腴潤,屈曲波磔,如“辛”之豎畫及“人”之捺畫,行筆過程中輔以振宕,欲行不行,給人以遲澀凝重之感。藏露互用,如“中”之豎畫,起止皆用露鋒;“案”之撇、捺,皆于收筆時以筆腹略頓,戛然快提,無鋒而止,用筆轉換自如。筆畫粗細有致,結字亦大小錯落,如“我”之下諸字,由小變大,對比鮮明,最突出者如“千”與“案”二字,大小粗細對比到夸張的程度。整體上筆意縱恣,有鐘鼎文字的奇致和爛漫,這也符合郭沫若骨子里的浪漫主義精神。不過,此手跡似非郭沫若書法中的上品,偶有瑕疵,如“夷”字之撇畫,既欲一筆左下出鋒,又欲彎而上翹,處理得并不成功。或情怠手闌,或紙墨不稱,郭沫若書寫時應未處于最佳狀態。
作者簡介gt;gt;gt;gt;
王增寶,文學博士,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從事文藝理論、近現代文學文獻等研究。著有《清末民初小說藝術身份的確認》《〈作家〉復刊履痕:1978—2018》。
[責任編輯 胡海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