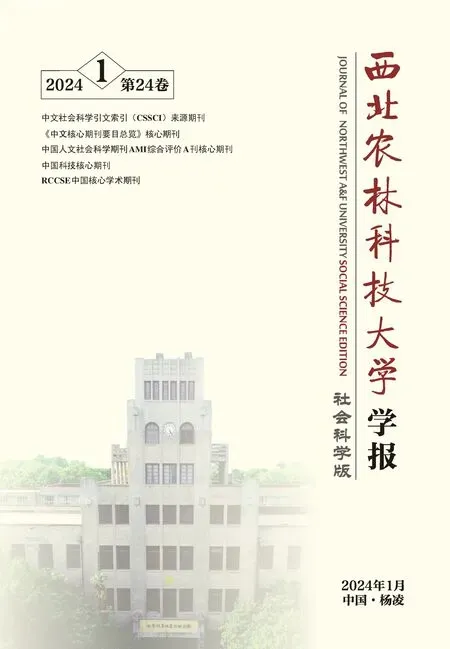農業生產者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的收入效應
王建華 周瑾 任敏慧



摘? 要:以有機肥和生物農藥兩類綠色投入品為例,運用內生轉換回歸模型,實證分析農業生產者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的收入效應,并運用無條件分位數回歸進行異質性分析。研究表明:(1)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受到內外部因素的影響,不同綠色生產要素的投入行為影響因素有所差異;(2)不同綠色生產要素投入決策條件下農業收入的影響因素有較大差異,新型農業經營類型能夠顯著提高農業收入;(3)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具有正向收入效應;(4)有機肥投入隨著農業收入的提升,影響程度有逐漸遞減趨勢,生物農藥投入對農業收入的影響程度呈現“倒U”型特征,不同主體類型和地理區域對不同農業收入水平的影響程度存在顯著差異。
關鍵詞:綠色生產要素;收入效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內生轉換回歸模型;無條件分位數回歸
中圖分類號:F323.6;S14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24)01-0110-14
收稿日期:2023-04-25?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4.01.12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20&ZD117)
作者簡介:王建華,男,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業經濟管理。
隨著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快速推進,長期環境污染問題給農業綠色發展造成了巨大阻礙。從農業污染來看,農業面源污染范圍廣、檢測難度大、監管成本高,不僅影響水土質量,而且容易促使農業生產者以掠奪環境為代價獲得農業收入,造成污染程度的加深[1]。傳統的資源高消耗、化學品高投入的生產要素投入模式無以為繼,需實現農業生產要素配置轉型升級。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促進農業經營增效,切實保障農民利益”“推進農業綠色發展,加快農業投入品減量增效技術推廣應用”。未來農業發展不僅要持續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加快集成推廣化肥農藥減量增效的綠色高效技術模式,而且要全面推動農業生產方式綠色轉型。自2015年農業農村部開展化肥農藥使用量零增長行動以來,我國化肥農藥減量增效成果顯著,2020年,水稻、玉米、小麥三大糧食作物化肥利用率為40.2%,農藥利用率為40.6%。2020年有機肥施用面積超過5.5億畝次、比2015年增加約50%,高效低風險農藥占比超過90%。但從農業生產者角度,經濟收益是激勵其采取綠色生產行為的關鍵驅動力。為此,本文從農業生產者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視角,以有機肥與生物農藥為例,通過實地調研數據,實證檢驗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所帶來的收入效應,并從農業經營主體類型和區域特征方面分析其異質性,進而提出相關建議。
一、文獻回顧與評述
從要素投入視角來看,我國農業生產方式在經歷主要依靠勞動力等傳統生產要素轉變為主要依賴化肥、農藥等化學農資之后,近年來化學生產資料提供給農業產出和經濟增長的動力逐漸減弱,其施用成本或已高于產出效益,且同時給環境帶來了負外部性的社會成本[2]。綜合調整要素配置,從而形成新的綠色化生產方式,是在保障農產品安全的前提下保護農業生態環境、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的必要途徑,也是新一輪經濟效益提升的重要契機[3]。
宏觀層面上,現有研究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一是農業要素稟賦結構與制度變遷。從演化方向來看,羅浩軒認為,統一于農業工業化進程,我國農業要素稟賦結構沿循勞動要素、資本要素、技術要素不斷豐裕升級,同時以農業反哺制度、多功能農業制度方向演化完善農業制度[4]。在變遷路徑研究方面,孔祥智等認為我國農業技術變遷路徑是以土地要素為基礎變量,以勞動力要素為最核心、最能動變量,其他要素(農業機械、化肥、農藥)以勞動力價格的變動為中心,實現各類資源的優化配置[5]。另外,農業生產資源的配置與利用效率不光取決于政治經濟制度,也與具體的經營制度具有密切聯系[6]。二是投入要素與生產率對農業經濟的作用。已有研究發現,農業生產要素對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增長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且不同生產要素對收入作用機制存在一定差異[7]。針對農業技術創新,龔斌磊利用增長核算表解析了農業增長的內部結構,結果表明,投入要素對我國農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逐步減弱,其中,化肥與農機的貢獻率高于勞動力和土地,而生產率,尤其是技術貢獻率在不斷提高[8]。此外,農業技術創新[9]、人力資本積累[10]等因素在促進農業經濟增長中亦起到了積極作用。三是生產要素轉化機制與驅動因素。熊桉提出了農業技術作為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和市場化配置、構建要素收益分享與風險共擔的技術研發和成果轉化的內生機制、建立經營性、公益性和準公益性科技成果轉化的內生模式[11]。驅動因素方面,Huang等研究得出,技術進步是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關鍵驅動力[12]。趙明正等以化肥使用量變化特征為例,對其驅動因素進行LMDI分解,研究發現,施肥強度變化和種植結構調整是化肥使用量下降的主要驅動因素,變化規律如環境庫茲涅茨倒U形曲線[13]。
微觀層面上,現有研究圍繞不同農業生產主體展開了豐富的討論。從行為決策角度的研究主要分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綠色生產行為的影響因素,包括技術采納與農藥化肥減量行為。如從測土配方施肥技術[14]、農藥化肥減量[15]等方面對分析生產者行為影響因素。研究表明,生產者綠色生產行為不僅受到個體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影響[16],而且受到鄉村規章制度和正規環境規章等外部環境的影響[14]。二是綠色生產技術采納行為效應。陳雪婷等研究發現,生產者對技術的感知易用性是顯著影響其生態種養模式采納和采納強度提高的重要因素,同時生態農業模式的采納能夠顯著提高農業收入[17]。Li等研究結果表明,綠色生產技術的采用提高了水稻產量的18.8%~24.5%[18]。也有研究證明,技術采納主要通過獲得更高的市場溢價,并擴大種植規模和增加投入成本,得以改善生產者經濟收益[19]。三是農業生產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機制。李江一等實證結果表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農地流轉起到直接拉動效應和間接帶動效應的作用,進而能夠提高農地資源配置效率和農業生產率[20]。另外,因農地要素和勞動力要素的屬性差異,不同農地產權強度中的國家賦權和社會認同對農業生產要素配置存在差異化影響,行為能力起到調節作用[21]。
已有研究從宏微觀視角對農業生產要素的積極探索,為實現農業綠色生產轉型研究提供了理論參考,尤其是對農業生產者微觀主體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不同生產要素投入的環境與經濟效應,其差異性主要源于研究背景、理論基礎、研究方法、要素類型、收入類型、主體類型、初始稟賦等方面的異同。縱觀現有文獻,雖然已有部分學者關注到綠色投入品這類生產要素,但僅在投入行為的影響因素層面分析其誘因[22-23],對其投入行為的結果變量展開探討的研究則相對較少。但對于農業生產者來說,收入效應往往是其持續從事農業綠色生產的關鍵。除此之外,對于不同收入水平下不同綠色生產要素的增收效應,尚未有學者將其納入同一研究框架進行比較分析。鑒于此,本文擬運用內生轉換回歸模型(ESRM)和無條件分位數回歸(UQR),將不同綠色生產要素納入同一研究框架,實證檢驗其收入效應,并在不同農業收入水平下分析其增收效應的異質性,對補充現有研究內容、了解農業綠色生產轉型推動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農民收入問題一直是“三農”問題研究的重點和難點,少數小農的生產多以“自用口糧”為驅動,更注重糧食安全,而大多數農業生產者的生產具有明顯的“市場化”特征,更注重高產和增加土地收入[24]。農業領域的綠色生產投入要素在參與原有生產要素替代性調整和資源稟賦結構變化過程中,為生產高品質農產品、推進綠色生產結構轉型提供內源動力,主要表現在減少化學品投入、耕地保護、資源節約等方面,形成資源節約和保護環境的生產方式、產業結構和空間格局。基于要素稟賦分析農業生產活動和模式變化,農業生產者對土地和勞動兩種初級資源的相對稟賦和累積狀態是決定農業技術變革模式的關鍵因素,消除無彈性土地和勞動供給對生產施加的約束作用,即可實現農業增長[25]。
農業生產要素的流動能夠引起生產方式的變化,而綠色生產要素的投入主要通過要素間的替代效應帶動農業生產綠色化,產生農業產品結構變化,主要表現在通過高效優質多抗新品種、環保高效肥料農藥等要素投入提高土地生產率,從而實現對土地的替代[5]。從行為決策過程來看,農業生產者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實質上是其根據自身稟賦特征、外部環境條件,以及對未來收入預期所做出的生產資源再配置過程[26]。Schultz的理性農民假說認為,農業生產者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生產目標,并依此進行農業生產投入行為決策[27]。那么只有當綠色生產要素投入所帶來的預期收益增長幅度高于投入成本,或預期凈收益高于當前收益時,生產者才會選擇投入。對此,可構建農業生產者期望收益最大化函數[28]:
Maxk,n E(U)=Maxk,n E[π1(k)+ν1(k)θ-C]n+(N-n)π0-F (1)
式(1)中,U表示收益,則E(·)表示生產者對收益的期望;k、ν1(k)分別為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與投入風險;π1與π0分別為投入和未投入綠色生產要素的單位收益;θ是隨機變量且均值為0;C、F分別為單位成本、固定成本;N、n分別為總生產規模、投入綠色生產要素的生產規模。那么,只有當[π1(k)+ν1(k)θ-C]n+(N-n)π0-F≥Nπ0時,生產者才會投入綠色生產要素。以收益最大化目標為條件,生產者對綠色生產要素的風險函數θ(·)需滿足:
θ(·)≥[C+π0-π1(k)]ns+Fν1(k)ns(2)
式(2)中的ns為最佳生產規模,假設滿足(2)的θ(·)為常數ξ0,則生產者投入綠色生產要素的風險條件為:
ri=1,θ(·)≥ξ00,θ(·)<ξ0(3)
由式(3)可得到生產者對綠色生產要素的投入行為決策方程為:
Ti=lnP(θ≥ξ0)P(θ<ξ0)=lnri=1ri=0=α0+α1Di+Ψi+ωi(4)
式(4)中,Ti為生產者i選擇投入綠色生產要素的概率;Di表示影響生產者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的矩陣變量;Ψi為不可觀測變量;α0、α1、ωi分別為常數項、待估參數和誤差項。
雖然初始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取決于未來預期收入,但若實際收益無法達到預期,生產者可能會改變投入行為,這對綠色生產要素的持續投入至關重要。鑒于此,本文進一步從收入效應角度分析。一是消費端,消費者食品安全觀念的提升、需求升級、高端消費市場空間擴大,綠色優質農產品市場需求不斷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的市場溢價能力得到逐步提高。二是政策導向,2022年,農業農村部發布《“十四五”全國農產品質量安全提升規劃》,提出“‘十四五大力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的規劃目標。當前的市場需求和政策導向均為生產者生產綠色優質農產品,以獲得更高的農業收入提供了契機。三是已有研究表明,生產者利用綠色防控技術,能夠提升農產品品質,增加了農產品市場競爭力,實現綠色優質農產品溢價,從而促進生產者農業增收[29]。現有文獻對多種綠色生產要素的收入效應已經進行了一定研究,綠色生產要素投入對農業收入的提升效應得到了肯定結論[30]。傳統農業生產對化學投入品的過度依賴,不僅容易增強病蟲害抗藥性,使生產者過量施用化肥農藥行為頻頻發生,導致化肥農藥的使用量和生產成本增加,而且如果化肥農藥施用不當,對農產品品質會造成嚴重影響,如農藥殘留超標,也會對環境產生很大的負外部性[31]。同時,農業生產者化肥施用強度加大在一定程度上會提高農藥單位用量[32]。基于此,本文選擇有機肥與生物農藥兩類綠色投入品作為研究的生產要素,其主要原因有:首先,有機肥與生物農藥同屬于綠色生產過程的中間投入品,是典型的“土地節約型”綠色生產要素;其次,有機肥與生物農藥分別對化學肥料和化學農藥具有替代效應,增加有機肥與生物農藥的投入有利于減少化肥農藥的使用量;最后,相對于傳統化肥農藥,有機肥和生物農藥能夠在改善農業生態環境的情況下,顯著提升農產品品質,對實現農作物標準化和綠色化生產、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具有積極作用,并且,綠色優質農產品較高的市場溢價為生產者增收提供了必要條件。因此,從減少施用化肥農藥的成本、提升農產品品質以獲得更高市場溢價等方面考慮,本文認為有機肥與生物農藥可以有效提升農業收入,并提出如下假說。
H1:有機肥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能夠顯著提升農業收入,即存在正向收入效應。
H2:生物農藥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能夠顯著提升農業收入,即存在正向收入效應。
三、數據來源、模型構建與變量設置
(一)數據來源與特征描述
本文數據來自課題組于2021年7-8月對江蘇省部分地區主要從事種植業的農業生產者綠色生產經營狀況進行的實地調查。調研采取分層逐級抽樣與隨機抽樣結合的方法。首先,參考地區生產總值、農業產值、農作物播種面積等指標,根據地理位置分布,選取了蘇南(無錫)、蘇北(宿遷、淮安)、蘇中(泰州)4個代表性城市作為初級抽樣單位;其次,根據各市的種植地區分布、農業產值和相關農業生產情況公開信息,分別選取2~5個縣(區),隨機選取對應鄉鎮和行政村;最后,由專項人員進行入戶詢問,在每個村隨機選取5~20個農戶,以問卷調查和面對面訪談相結合的方式,深入了解生產者農業生產經營的基本情況與現實問題。共發放并回收問卷813份,經統計與整理,剔除存在關鍵信息缺失、前后回答矛盾等問題的問卷,最終獲得有效問卷708份,問卷有效率87.08%。
表1呈現了調查區域樣本的綠色生產要素投入情況。總樣本有機肥的投入率為69.49%,略高于生物農藥的63.56%投入率。從各市樣本來看,無錫市樣本生產者對有機肥的投入率最高,為86.47%,其次為淮安市70.74%,宿遷市與泰州市分別為61.63%和64.19%。對于生物農藥的投入情況,各市樣本生產者也呈現出較大差異,淮安市樣本中75.53%的生產者會投入生物農藥,24.47%未投入,無錫市樣本生產者對生物農藥的投入率為70.68%,泰州市為58.14%,宿遷市僅為51.74%。
有效樣本的生產者基本特征如表2所示,主要呈現了多個方面的統計特征。個體特征方面,受訪者以男性居多,男女比例約為3∶2,符合當前我國農業生產勞動力以男性為主的社會特征;已婚狀態受訪者占比90.40%,結合年齡分布來看,主要集中在30~60歲的年齡段;80%以上受訪者的受教育程度處于高中及以下。因農業生產依靠較強的體力勞動,為此調查了生產者的身體健康狀況,通過自評健康狀況等級可以看出,選擇“較好”以及“很好”的頻數較高,近10%身體“很差”和“較差”的被調查者在從事農業生產。從社會身份來看,樣本生產者中具備黨員身份的比例為22.88%,具有村干部經歷的生產者比例為19.21%。生產經營特征方面,農業勞動人數主要以2人為主,占53.95%,5人及以上的勞動人數僅為5.08%;耕地總面積在5畝及以下占比最高,為44.63%,說明此次調查對象中小農戶占有較大比例。年農業收入方面,47.46%的樣本生產者農業收入處于5萬元以下,這與耕地面積分布具有較強聯系,20萬元以上的樣本生產者僅為12.57%;從生產經營類型來看,本次調查以傳統小農戶為主,小農戶比例達69.63%,符合當前我國仍是以分散的小規模農戶為主的農業生產特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中,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農業企業樣本占比分別為11.72%、12.71%、2.82%、3.11%。
(二)模型構建
1.內生轉換回歸模型(ESRM)。根據前述分析,綠色生產要素的投入行為可能會產生收入效應,此外,農業收入可能還受到生產者個體特征、家庭特征、生產經營特征、外部環境特征等因素的影響。為準確評估收入效應,綜合考慮影響農業收入的內外部因素,同時避免選擇性偏差、遺漏變量偏差和反向因果等問題,本文采用內生轉換回歸模型(ESRM)進行綠色生產要素收入效應的評估[33]。
構建如下收入效應模型,以分析綠色生產要素的投入行為對農業收入的影響:
Yi=β1Xi+β2Tij+εi(5)
式(5)中,Yi為生產者 的農業收入;Xi為影響農業收入的各類控制變量,包括生產者個體特征、家庭特征、生產經營特征、外部環境特征等,且可與式(4)的Di一致;Tij為生產者i是否投入綠色生產要素j的行為決策虛擬變量(j=1,2),Tij=1表示投入,Tij=0表示未投入;β1、β2為待估參數,分別描述了控制變量對農業收入的影響大小和綠色生產要素投入對農業收入的影響大小;εi為隨機誤差項。
根據ESRM兩階段估計的思路,第一階段,采用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計(FIML)對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決策方程進行回歸,設定是否投入綠色生產要素的行為決策模型為:
Tij=γZij+ηIi+μi(6)
式(6)中,Zij為影響生產者是否投入綠色生產要素的各類因素,Zij與Xi可一致;Ii為工具變量,對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具有直接影響,但不直接影響農業收入;γ、η分別為各類因素和工具變量對行為決策影響大小的待估參數;μi為決策方程誤差項。
第二階段,運用第一階段計算的逆米爾斯比率(λ)和協方差,引入農業收入結果方程進行參數估計,在投入和未投入兩種情境下,分別定義農業收入結果方程為:
Yi1=φ1Xi1+σiμ1λi1+εi1??? Ti1=1(7)
Yi0=φ0Xi0+σiμ0λi0+εi0??? Ti1=0(8)
式(7)和(8)中,引入的λi1和λi0分別控制了投入與未投入情況下未觀測變量所產生的選擇性偏差問題;εi1和εi0為結果方程誤差項;σiμ1、σiμ0為協方差,如果決策方程和結果方程協方差相關系數顯著,則表明未觀測變量導致了模型選擇性偏差問題,需要消除內生性,以保證處理效應的無偏估計。
最后,計算處理組和控制組樣本的平均處理效應,即投入和未投入綠色生產要素的平均處理效應,如式(9)和(10):
ATT=E(Yi1|Tij=1)-E(Yi0|Tij=1)=(φ1-φ0)Xi1+(σiμ1-σiμ0)λi1(9)
ATU=E(Yi1|Tij=0)-E(Yi0|Tij=0)=(φ1-φ0)Xi0+(σiμ1-σiμ0)λi0(10)
2.無條件分位數回歸(UQR)。為進一步分析不同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對于農業收入在不同分位點上的異質性影響,本文擬采用Firpo等提出的再中心化影響函數(RIF)進行無條件分位數回歸(UQR)[34],計算要素投入對農業收入變化的邊際效應,并分析主體類型、區域特征對農業收入影響的異質性。UQR基于對條件分位數的擴展,避免了過多不必要的控制因素,能夠更加全面地描述在不同分位數條件下要素投入對農業收入的作用機制,且UQR對誤差項的要求假設不嚴格,不易受極端值影響,估計結果較為穩健[35]。設定Y的τ分位數RIF方程為:
RIF(Y,Qτ,FY)=Qτ+τ-I{Y≤Qτ}fY(Qτ)(11)
式(11)中,Qτ表示Y的無條件τ分位數,τ=FY(Qτ);I{Y≤Qτ}為指示函數;fY和FY分別為Y的密度函數和分布函數。對RIF(Y,Qτ,FY)求條件期望可得到無條件分位數的邊際效應,如式(12):
UQPE(τ)=∫d{E[RIF(Y,Qτ,FY|X=x)]}dxdFX(x)(12)
(三)變量設置
本文的研究變量分為四類:被解釋變量、關鍵解釋變量、工具變量和控制變量。各變量的定義、賦值與描述性統計如表3所示。
1.被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為農業收入。使用年農業種植總收入作為主要被解釋變量,并取自然對數納入模型估計。同時,參考李亞娟等的研究[35],使用單位面積農業收入即畝均農業收入,更換被解釋變量,用以檢驗結果的穩健性。
2.關鍵解釋變量。關鍵解釋變量為是否投入綠色生產要素。以有機肥和生物農藥兩類綠色投入品為例,將是否投入有機肥或生物農藥進行農業生產作為衡量投入行為的指標,投入賦值為1,未投入賦值為0。
3.工具變量。考慮到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問題,選取“技術獲取渠道”作為工具變量。以往研究選擇“鄰里效仿”“技術培訓服務”等相關變量作為工具變量[17,36],目的在于選擇的工具變量能夠充分影響行為決策因變量,且與被解釋變量無直接相關關系。本文工具變量的選取基于外部環境因素,利用生產者能夠獲取綠色生產技術的渠道數量表征工具變量“技術獲取渠道”,其一定程度上能夠決定生產者是否獲取到有機肥或生物農藥,又不會直接影響其農業收入,但工具變量有效性仍需進一步檢驗。
4.控制變量。控制變量的選取涵蓋生產者各類生產要素投入,特別將勞動力、土地等關鍵要素投入情況納入,主要包括個體特征、生產經營特征、認知特征和環境特征四類可能影響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和農業收入的內外部因素。個體特征包含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的基本人口特征,以及是否為黨員、是否為村干部的社會身份特征。農業生產依靠較強的體力勞動,生產者的身體健康程度反映了個人勞動力水平,因此納入身體健康狀況作為控制變量。生產經營特征包括農業勞動人數和耕地面積。經驗表明,勞動力與土地投入往往對技術選擇和農業收入具有重要影響[37]。認知特征主要涉及對農業資源與經濟收益的認知,已有研究驗證生態認知[22]、效益認知[38]對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的積極作用。環境特征包括市場信息獲取難易度與生產要素獲取便利性兩個方面。生產經營行為不僅受到主體特征影響,而且往往離不開外部環境條件的約束作用[39],同時,由環境影響的生產行為可以適應市場主導,形成自下而上“拉動”模式[40]。生產經營類型分為傳統小農戶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同主體類型的生產模式有所差異,有研究表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農業生產率和農戶收入提高的有效抓手[20]。納入該虛擬變量,一方面探究不同類型農業生產者在生產行為方面的差異,另一方面控制不同類型生產者的農業生產模式對農業收入的影響。區域特征變量根據樣本數據地區來源分為無錫、宿遷、淮安和泰州四個城市,以此控制地理區域的影響。
(四)內生性問題與工具變量有效性檢驗
前文理論分析表明,收入效應模型中可能存在選擇性偏差、遺漏變量偏差和反向因果等問題,因此選用ESRM進行實證分析。其中,工具變量要求與內生性解釋變量高度相關,但與隨機誤差項不相關。鑒于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是在球形擾動項的情況下能體現出工具變量實質的最有效率工具變量法,因此本文使用2SLS對模型進行估計,以檢驗工具變量的有效性,結果如表4所示。模型1是有機肥投入行為對農業收入的影響模型,第一階段聯合顯著性檢驗的F值為17.410,在1%水平上拒絕所有解釋變量外生的原假設,工具變量在1%水平上對有機肥投入行為具有顯著影響,說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第二階段回歸結果顯示,在緩解內生性問題后,影響效應依舊顯著,由此說明工具變量的有效性。同理,模型2估計結果依舊表明工具變量有效。為進一步檢驗工具變量的可靠性,本文借鑒Conley等所提出的工具變量“近似外生”的觀點,在放松外生性條件下,利用近似于零方法(LTZ)進行額外分析[41]。結果得出是否投入有機肥和生物農藥的變量估計系數分別為1.982和2.055,結果顯著為正,表明在近似外生的情況下,技術獲取渠道作為工具變量得到的估計結果是穩健的。
四、實證結果與討論
表5為綠色生產要素投入對農業收入影響的ESRM估計結果。模型3和模型4分別以有機肥和生物農藥投入作為決策方程的被解釋變量,農業收入為結果方程的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的結果,Wald檢驗結果顯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決策方程與結果方程相互獨立的原假設,對數似然值表明模型擬合狀況良好,ln σ與ρ均在1%或5%水平上顯著不為0,說明不可觀測變量同時影響了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與農業收入,需要對選擇性偏差進行修正,運用ESRM進行估計較為合理。
(一)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影響因素結果分析
模型3和模型4的決策方程估計結果顯示,有機肥和生物農藥投入行為受到不同內外部因素的影響,影響因素存在一定差異。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對綠色生產要素投入決策沒有顯著影響,該結果與部分以往研究結果較為一致[35];身體健康狀況顯著影響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且對于有機肥和生物農藥,分別在5%和1%水平上具有負向影響;無論是黨員還是村干部的社會政治身份,均無法對有機肥和生物農藥投入行為產生顯著影響。生產經營特征方面,有機肥和生物農藥的投入行為受到農業勞動人數和耕地面積的正向影響,且在5%或1%水平上統計顯著,表明農業勞動人數越多、耕地面積越大,生產者越可能投入有機肥和生物農藥。經濟收益認知作為投入行為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在1%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有機肥和生物農藥投入行為,但農業資源認知并無顯著影響。該結果表明,生產者對綠色生產要素的不同效益認知對其投入行為具有不同影響效應[38]。生產要素獲取便利性顯著影響有機肥投入行為,有機肥作為由原料加工形成的商品有機肥料,生產者往往需要通過市場購買獲得,生產要素獲取便利性越好,越容易獲取有機肥,從而有利于生產者投入有機肥進行生產。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有機肥和生物農藥投入行為方面無顯著差異,而地理區域變量對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具有一定影響,無錫地區生產者更可能投入有機肥和生物農藥。技術獲取渠道能夠顯著影響有機肥和生物農藥投入行為,但在技術獲取渠道數量越多的情況下,生產者選擇投入綠色生產要素的概率反而降低。其可能原因在于,生產者面對多種渠道選擇時,對渠道因素的考慮范圍越廣,越難以作出綠色生產要素投入決策,造成投入的可能性越低,但這僅是本樣本選擇下所產生的特定結果,同時,技術獲得渠道與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為該工具變量的有效性提供了基本依據。
(二)農業收入效應影響因素結果分析
模型3和模型4的結果方程估計結果顯示,投入與未投入有機肥和生物農藥進行農業生產的生產者,其農業收入的影響因素表現出較大差異。個體特征方面,婚姻狀況僅對投入生物農藥的生產者農業收入具有一定影響;身體健康狀況僅對未投入有機肥的生產者農業收入具有顯著影響;受教育程度在未投入有機肥和生物農藥的情況下,均對農業收入具有顯著影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農業收入越高;黨員和村干部的身份對未投入有機肥和生物農藥的生產者農業收入具有差異性的影響,其中,黨員相較于非黨員,生產者農業收入更低。農業勞動人數僅對投入情況下的農業收入產生顯著正向影響;耕地面積在四種不同投入決策情況下均對農業收入呈現顯著提升作用;農藥資源認知、經濟收益認知與投入情況下的農業收入有顯著相關關系;不同的新型農業經營類型均對投入情況下的農業收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其中農業企業的農業收入提升效率最高;外部環境特征中市場信息獲取難易度在四種不同投入決策情況下均在5%或1%水平上顯著,越容易獲取外部市場信息的生產者,可能在及時獲取農產品價格信息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促使其農業收入越高。地區特征中,淮安為對照組,宿遷和泰州對不同投入決策下的農業收入差異影響顯著區別于無錫。模型3與模型4結果方程估計結果比較可知,無論是否投入有機肥和生物農藥,耕地面積均對農業收入具有顯著影響,其中對未投入有機肥的生產者農業收入影響程度最高;專業大戶生產經營類型對提升農業收入具有顯著作用,且對未投入生物農藥的生產者農業收入影響程度高于其他生產者。
(三)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對農業收入影響的平均處理效應
基于ESRM,反事實估計下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對農業收入影響的平均處理效應結果如表6所示,有機肥和生物農藥投入的平均處理效應(ATT)分別為0.702和0.774,差異性t檢驗顯示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由此說明有機肥和生物農藥投入均能夠顯著提高農業收入。從變化率來看,對于實際投入綠色生產要素的生產者來說,生物農藥所帶來的收入效應相對更高,投入有機肥與生物農藥可使農業收入水平分別提高6.61%和7.31%。對于實際未投入有機肥和生物農藥的生產者,其平均處理效應(ATU)分別為1.325和1.159,相較于反事實狀況下的農業收入,實際農業收入降低了12.66%和11.01%。由此進一步說明投入有機肥和生物農藥能夠顯著提升農業收入,即為正向收入效應,且對于未投入生產者在投入后的收入效應更明顯。該結果可能原因在于,綠色生產要素能夠降低農產品化學殘留,進而改善農產品品質,提升農產品價格,從而實現農業增收。此外,江蘇省作為本次調研地區,在高標準農田建設、化肥農藥減量行動、農產品市場與農業品牌等方面的工作成效顯著,為生產者綠色生產提供了良好外部環境的同時,也給生產者經濟效益帶來了更大的提升空間。假說1和2得到了驗證,這與以往研究結論存在部分一致性,綠色生產技術的采納能夠顯著促進生產者農業增收[29],但本文從綠色投入品的不同角度,為綠色生產要素的經濟效益提供了新的證據。隨著農業面源污染治理力度的不斷加強、農業綠色可持續發展的持續推進,以有機肥和生物農藥代替傳統化肥和農藥,提升綠色生產要素的投入水平,不僅是提高生產者農業收入的有效路徑,而且是切實加強環境保護、加快農業綠色發展的關鍵途徑。
(四)穩健性檢驗
1.多種方法模型估計。為檢驗ESRM估計結果穩健性,本文運用多方法進行比較研究,表7為ESRM、PSM、Heckman兩階段和OLS方法對模型的估計結果。PSM方法平均處理效應估計值與ESRM稍有差異,且生物農藥投入行為對農業收入的影響效應顯著性較低;Heckman兩階段估計回歸系數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進一步說明有機肥與生物農藥投入的收入效應顯著;OLS方法估計結果中,有機肥和生物農藥投入行為均對農業收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由此可見,在多種方法檢驗下,有機肥和生物農藥投入的收入效應結果較為穩健。然而,OLS估計可能會忽視生產者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的內生性問題,導致估計結果有偏,使用ESRM可以嚴謹客觀地評價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的收入效應。
2.更換被解釋變量模型估計。為進一步檢驗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的收入效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更換被解釋變量為畝均農業收入再次進行ESRM估計,結果如表8所示。模型的Wald值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再次說明不可觀測變量引起的樣本選擇性偏差問題有必要通過ESRM進行糾正。綠色生產要素投入對畝均農業收入影響的平均處理效應結果均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上述實證分析結果穩健。
(五)農業收入效應異質性分析
不同類型的農業經營主體的經營績效存在顯著差異,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相較于傳統小農戶,在生產、加工和銷售等環節具有明顯的優勢[42],不同的地理區域特征對生產者綠色生產行為和農業收入水平也存在一定影響[30]。前文實證結果表明,不同綠色生產要素、生產經營類型和區域特征對農業收入的影響效應存在顯著差異,值得深入探究。為進一步描述不同綠色生產要素投入對農業收入影響程度的差異,比較分析不同農業經營主體和地理區域對農業收入影響的異質性,采用UQR對有機肥與生物農藥的投入行為、主體類型、區域特征,分別在農業收入的10、25、50、75、90分位數點進行收入效應異質性分析,結果如表9所示。
首先,有機肥投入對不同農業收入水平均存在顯著正向影響,尤其對低收入水平(τ=0.1)影響程度最高,隨著收入提升,影響程度具有遞減趨勢,生物農藥投入對農業收入的影響呈現“倒U”型,其中對中等農業收入水平(τ=0.5)的影響程度最高。該結果顯示出兩種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收入效應的異質性,即有機肥和生物農藥分別在不同農業收入水平下的影響程度并不一致,同時,在各個農業收入水平下,兩種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之間的收入效應也存在顯著差異。其次,在多個分位數條件下,傳統小農戶主體類型對不同水平的農業收入均存在負向影響,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和農業企業均對農業收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其中農業企業對高收入水平(τ=0.9)影響不顯著。該結果表明,新型農業經營類型在不同程度上可以促進農業增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引領農業高質量發展、加快綠色農業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43]。最后,從區域特征影響來看,農業收入受區域影響較大,其中泰州區域的收入水平均顯著偏低,淮安、宿遷和無錫區域在不同農業收入水平下的積極作用存在差異性。該結果驗證了以往部分研究的結論,即區域因素對生產者綠色生產行為的影響存在異質效應[44]。
五、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主要結論
當前我國農業面臨綠色生產轉型,而提升綠色生產要素投入水平是促進農業綠色發展、加快綠色生產轉型的重要手段。鑒于此,本文以有機肥與生物農藥為例,從微觀農業生產者視角,基于江蘇省708份實地調研數據,運用內生轉換回歸模型(ESRM),實證檢驗了有機肥與生物農藥投入行為的收入效應,并進一步運用無條件分位數回歸(UQR)展開異質性分析,得到如下結論。(1)綠色生產要素投入行為受到內外部因素的影響,有機肥與生物農藥投入行為的影響因素具有一定差異,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相較于傳統小農戶,更容易投入有機肥和生物農藥綠色生產要素。(2)不同投入決策下,農業收入的影響因素也具有較大差異。耕地面積、市場信息獲取難易度在任何情況下均對農業收入具有顯著提升作用;在未投入情況下,個體特征是造成農業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在投入情況下,農業勞動人數、農業污染認知與經濟收益認知是顯著影響因素;新型農業經營類型能夠顯著提高農業收入,不同主體類型對農業收入的提升效果存在差異。(3)不同綠色生產要素的投入均對農業收入產生影響,且為正向收入效應,表現為:在反事實假設條件下,實際投入有機肥與生物農藥的生產者農業收入比未投入情況分別提高6.61%和7.31%,而實際未投入如果選擇投入,其農業收入會分別提高12.66%和11.01%。(4)有機肥投入對低收入水平的生產者農業收入影響程度最高,且隨著收入提升,影響程度具有遞減趨勢;生物農藥投入對農業收入的影響呈現“倒U”型特征,其中對中等農業收入水平的影響程度最高。不同主體類型和地理區域對不同農業收入水平的影響程度存在顯著差異,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類型對提高農業收入的積極作用得到驗證。
(二)政策建議
若要實現農業收入增長,生產要素必然是核心概念之一,綠色生產要素對傳統生產要素配置的動態調整是實現農業收入增長和綠色發展的必要途徑。結合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是加快農業生產要素配置調整,促進綠色生產要素投入。整合科研力量,設立產學研合作項目基金,加強基礎性科學技術研究,如加大對有機肥、生物農藥等綠色投入品研發資金投入和研發力度,突破性研發更為高效、低成本的綠色生產要素。加快建設技術研發集成平臺,對土地、技術、勞動力等傳統要素進行組合優化,依靠創新綠色生產要素驅動生產要素配置調整,提高綠色生產要素投入水平,加快農業綠色化發展和現代化進程。鼓勵研發人員定期開展下鄉調研項目,以充分田間試驗為支撐,根據區域差異化的農業生產需求,制定專業化的農業生產要素配置調整策略。此外,針對綠色生產技術供應商建立有效的綠色生產要素供給政策,提高生產企業和銷售商對綠色生產要素的市場供給水平。
二是注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多種方式整合土地資源。著力推進農業生產組織多元化,構建農業生產區域差異性產業結構和組織安排。注重培育農業企業、專業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針對性開展“通識教育”和“專業培訓”的雙重培訓課程,使其帶動小農戶的生產模式規范化和綠色化,促進綠色生產轉型。提升傳統專業合作社作用,通過組織綠色生產培訓、提供綠色生產資料、幫助形成企業協作模式等方式,充分發揮組織參與對生產者綠色生產轉型的積極作用。通過多種方式整合土地資源,盤活土地要素,開展新型農業生產要素“研發制造推廣應用一體化試點”工作。建立信息化農業生產的社會服務體系,提高社會化服務水平,實現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化、專業化、集約化和規模化。
三是優化綠色生產要素推廣模式,提升農業生產者認知水平。以生產者農業需求為導向,優化綠色生產要素推廣模式,如借助新媒體平臺豐富綠色生產資料獲取和農產品銷售渠道,為生產者提供便利條件。同時,加強綠色優質農產品市場體系建設,完善綠色優質農產品認證制度。結合市場與政府力量,借助線上線下多種信息傳播渠道,拓寬生產者信息獲取方式,提升其對綠色生產的認知水平。通過加大多種政策的執行力度,如組織技術宣傳活動、提供技術培訓,使生產者主動或被動學習綠色生產知識、了解綠色生產技術效益。此外,利用多種組織嵌入模式,拓寬生產者社會關系網絡,增強組織成員間溝通交流,如發揮組織內優秀成員模范作用,定期開展經驗分享與組織交流會等,促進更多的生產者投入綠色生產要素。
參考文獻:
[1]? 楊芷晴.教育如何影響農業綠色生產率——基于我國農村不同教育形式的實證分析[J].中國軟科學,2019(08):52-65.
[2]? 高晶晶,史清華.中國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遷探究——基于微觀農戶要素投入視角[J].管理世界,2021,37(12):124-134.
[3]? 龍如銀,葉景,楊家慧.生產要素價格對產業結構優化影響的空間分異研究[J].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21(01):57-71.
[4]? 羅浩軒.農業要素稟賦結構、農業制度安排與農業工業化進程的理論邏輯探析[J].農業經濟問題,2021(03):4-16.
[5]? 孔祥智,張琛,張效榕.要素稟賦變化與農業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對1978年以來中國農業發展路徑的解釋[J].管理世界,2018,34(10):147-160.
[6]? 鐘甫寧.從要素配置角度看中國農業經營制度的歷史變遷[J].中國農村經濟,2021(06):2-14.
[7]? 李谷成,李燁陽,周曉時.農業機械化、勞動力轉移與農民收入增長——孰因孰果?[J].中國農村經濟,2018(11):112-127.
[8]? 龔斌磊.投入要素與生產率對中國農業增長的貢獻研究[J].農業技術經濟,2018(06):4-18.
[9]? ZHANG F,WANG F L,HAO R Y,et al.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Spatial Spillover and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Taking 30 Province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J].Applied Sciences, 2022,12(02):845.
[10]? 袁冬梅,金京,魏后凱.人力資本積累如何提高農業轉移人口的收入?——基于農業轉移人口收入相對剝奪的視角[J].中國軟科學,2021(11):45-56.
[11]? 熊桉.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從外生向內生轉變的機制與模式研究[J].農業技術經濟,2019(11):83-92.
[12]? HUANG X Q, FENG C, QIN J H, et al. Measuring Chinas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Its Drivers During 1998-2019[J].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22:154-477.
[13]? 趙明正,趙翠萍,李天祥,等.“零增長”行動背景下中國化肥使用量下降的驅動因素研究——基于LMDI分解和面板回歸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2019(12):118-130.
[14]? DU S C,LIU J,FU Z T.The Impact of Village Rules and 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Farmers Cleaner Production Behavior:New Evidence From Chin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21,18(14):7311.
[15]? LIU T S,WU G.Does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embership Help Reduce the Over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s?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J].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2022,29(05):7972-7983.
[16]? LI F N,ZHANG J B,MA C B.Does Family Life Cycle Influence Farm Households Adoption Decisions Concerning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J].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2022,25(01):121-144.
[17]? 陳雪婷,黃煒虹,齊振宏,等.生態種養模式認知、采納強度與收入效應——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稻蝦共作模式為例[J].中國農村經濟,2020(10):71-90.
[18]? LI C Q,SHI Y X,KHAN S U,et al.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Green Production on Farmers Technical Efficiency:Evidence From China[J].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2021,28(29):38535-38551.
[19]? 李后建,曹安迪.綠色防控技術對稻農經濟收益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21,31(02):80-89.
[20]? 李江一,秦范.如何破解農地流轉的需求困境?——以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例[J].管理世界, 2022,38(02):84-99.
[21]? 仇童偉,羅必良.農地產權強度對農業生產要素配置的影響[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8,28(01):63-70.
[22]? 張紅麗,李潔艷,史丹丹.環境規制、生態認知對農戶有機肥采納行為影響研究[J].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21,42(11):42-50.
[23]? LU H,ZHANG P W,HU H,et al.Effect of the Grain-growing Purpose and Farm Size on the Ability of Stable Land Property Rights to Encourage Farmers to Apply Organic Fertilizer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9,251:109621.
[24]? LIU T T,BRUINS R J F,HEBERLING M T.Factors Influencing Farmers Adoption of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A Review and Synthesis[J].Sustainability,2018,10(02):432.
[25]? 速水佑次郎,弗農·拉坦.農業發展的國際分析[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26]? 陳飛.農戶生產投入選擇行為及其收入效應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16(09):113-122.
[27]? ?SCHULTZ T W.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32-57.
[28]? 侯曉康,劉天軍,黃騰,等.農戶綠色農業技術采納行為及收入效應[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9(03):121-131.
[29]? 黃炎忠,羅小鋒,唐林,等.綠色防控技術的節本增收效應——基于長江流域水稻種植戶的調查[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20,30(10):174-184.
[30]? 黃騰,趙佳佳,魏娟,等.節水灌溉技術認知、采用強度與收入效應——基于甘肅省微觀農戶數據的實證分析[J].資源科學,2018,40(02):347-358.
[31]? 于曉華,陳曉福,宋玉蘭.農業政策向可持續食物政策的轉型與公平“食物環境”的創造:德國的設想[J].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20(04):18-26.
[32]? 高晶晶,史清華.農戶生產性特征對農藥施用的影響:機制與證據[J].中國農村經濟,2019(11):83-99.
[33]? LOKSHIN M,SAJAIA Z.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of 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Models[J].Stata Journal,2004,4(03):282-289
[34]? FIRPO S,FORTIN N M,LEMIEUS T.Unconditional Quantile Regressions[J].Econometrica,2007(77):953-973.
[35]? 李亞娟,馬驥.科學施肥技術的收入效應差異分析——基于糧農初始稟賦的實證估計[J].農業技術經濟,2021(07):18-32.
[36]? 王學婷,張俊飚,童慶蒙.參與農業技術培訓能否促進農戶實施綠色生產行為?——基于家庭稟賦視角的ESR模型分析[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21,30(01):202-211.
[37]? GAO J J,GAI Q G,LIU B B,et al.Farm Size and Pesticide Use:Evidence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hina[J].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2021,13(04):912-929.
[38]? 楊彩艷,齊振宏,黃煒虹,等.效益認知對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采納行為的影響——基于不同生產環節的異質性分析[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21,30(02):448-458.
[39]? 陳轉青.政策導向、市場導向對農戶綠色生產的影響——基于河南865個農戶的實證分析[J].管理學刊,2021,34(05):109-125.
[40]? 周曙東,李幸子.農戶特征、外部環境與科學施肥[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0(01):50-58.
[41]? CONLEY T G,HANSEN C B,ROSSI P E.Plausibly Exogenous[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2,94(01):260-272.
[42]? 高鳴,習銀生,吳比.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經營績效與差異分析——基于農村固定觀察點的數據調查[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05):10-16.
[43]? ZHONG S,XU X T,LI J W,et al.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nancing Behavior of Large Professional Households Engaged in Gree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hina[J].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22:13.
[44]? 林珊,于法穩.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戶綠色生產行為的影響因素——基于全國10省(區)2 448個農戶家庭的調查證據[J].改革,2023(01):128-143.
Research on Income Effect of Green Production Factor Input Behavior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s:Empirical Analysis of ESRM and UQR for Organic Fertilizer and Biopesticide
WANG Jianhua1,ZHOU Jin2,REN Minhui1
(1.School of Business,Jiangnan University,Wuxi,Jiangsu? 214122;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income effect of green production factor input behavior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s.Taking organic fertilizer and biopesticide as two green inputs,the 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In addition,the Unconditional Quantile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heterogeneity.The results show that:(1) The input behavior of green production factors is affected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put behavior of different green production factors are different;(2)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income under different input decision conditions of green production factors.The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agricultural income.(3) The input behavior of green production factors has positive income effect.(4) Organic fertilizer input has the highest impact on low level agricultural income.With the increase of income,the degree of influence has a gradually decreasing trend.The degree of impact of biopesticide input on agricultural income showed an inverted “U” shape.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subjects and geographical regions on different levels of agricultural income.
Keywords:green production factors;income effect;main body of new agricultural operation;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model;unconditional quantile regression
(責任編輯: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