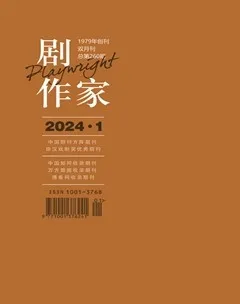管窺怪誕戲劇
張夢婕
二十世紀(jì)的技術(shù)革命以及兩次世界大戰(zhàn)對西方戲劇美學(xué)的影響是巨大的,尤其體現(xiàn)在表現(xiàn)主義和象征主義等新思潮的爆發(fā)上。“象征表現(xiàn)戲劇范型”的出現(xiàn)就是彼時(shí)多種思想與文化變革沖擊交匯后的產(chǎn)物,表現(xiàn)主義是最先脫胎成型的創(chuàng)作方法之一。德國表現(xiàn)主義運(yùn)動(dòng)代表埃德施密特聲稱:“僅僅復(fù)制世界毫無意義,要表現(xiàn)事物本質(zhì)就需要進(jìn)行再塑造。”[1]P472這是對“模仿再現(xiàn)戲劇范型”最激進(jìn)的拒絕,之后阿爾托的殘酷戲劇和荒誕派則將這一范型走到了極致。仍主張寫實(shí)手法才能揭示事物本質(zhì)的馬克思主義美學(xué)家盧卡契對表現(xiàn)主義的批判引發(fā)了三十年代著名的“形式主義論戰(zhàn)”。布萊希特反對盧卡契全盤否定的態(tài)度,認(rèn)為現(xiàn)實(shí)主義應(yīng)該隨著時(shí)代的發(fā)展并根據(jù)現(xiàn)實(shí)語境的要求主動(dòng)進(jìn)化,表現(xiàn)主義能夠豐富戲劇的表現(xiàn)手段,對創(chuàng)造新的美學(xué)有很大的助益。他也用敘述體戲劇的實(shí)踐證明了跨范型能取得的巨大突破。怪誕戲劇是另一個(gè)成功的跨范型類別。二十世紀(jì)四十年代巴赫金提出了怪誕風(fēng)格的兩條發(fā)展路線——現(xiàn)實(shí)主義怪誕和現(xiàn)代主義怪誕,實(shí)際上溯其源頭就是“模仿再現(xiàn)”與“象征表現(xiàn)”這兩大戲劇范型交融后的產(chǎn)物。按照學(xué)者丁羅南對于怪誕戲劇的四個(gè)分類,本文選取迪倫馬特的《物理學(xué)家》和皮蘭德婁的《尋找自我》進(jìn)行比較,分別就代表寫實(shí)的怪誕劇和元戲劇式的怪誕劇來談一談現(xiàn)實(shí)主義怪誕這種藝術(shù)創(chuàng)作方法在呈現(xiàn)和連接現(xiàn)實(shí)上的不同力量。
怪誕戲劇的動(dòng)態(tài)界定
李夢博士在《論視覺藝術(shù)中的怪誕》一文中對“怪誕”縱延兩千多年的理論語境進(jìn)行了梳理,用動(dòng)態(tài)、發(fā)展的眼光予以審視和考察,與本文在“戲劇范型與方法”的大框架下分析怪誕戲劇有著相似的文化學(xué)根源。幾乎每篇涉獵到怪誕詞源考證的文章都提到了,“怪誕”是羅馬古典主義建筑師維特魯維亞在考古羅馬皇帝尼祿宮殿地下室的時(shí)候?qū)σ环N因悖離當(dāng)時(shí)人們熟悉的藝術(shù)圖式而無以名狀的壁畫裝飾風(fēng)格的指稱,后綴“esco”表示事物的來源。李夢注意到意大利文“grotta”指地下一個(gè)深邃的空間,有“洞穴、洞窟、人工洞室”等不同含義,但中譯的時(shí)候幾乎都取了“洞穴”的意思,而忽略了“洞室”才真正指涉人類主動(dòng)建構(gòu)并賦予文化意義的空間。這個(gè)新的指稱最初始的語義是因?yàn)榛祀s而造成的陌生感,也在長達(dá)好幾個(gè)世紀(jì)的流傳中不斷與一些其他的藝術(shù)特征混合交纏,形成了不同階段各有偏重的理論軌跡,比如“反常”“滑稽”“兇險(xiǎn)”和“狂歡”等學(xué)說。因此,研究任何時(shí)期的怪誕都應(yīng)結(jié)合其時(shí)代地域背景和歷史語境,研究怪誕劇亦是如此。
二十世紀(jì)發(fā)生的兩次大戰(zhàn)改變了世界的格局和面貌,殘酷的戰(zhàn)爭、戰(zhàn)后支離破碎的現(xiàn)實(shí)圖景、畸形混亂的價(jià)值觀及病態(tài)異化的人性也對藝術(shù)創(chuàng)作者們造成了深刻的影響。反理性思潮席卷西方世界,美學(xué)上以“各種對立因素的奇妙混合及轉(zhuǎn)化”[2]P113為特征的“怪誕”作為一種藝術(shù)創(chuàng)作方法和審美思維成為最適合呈現(xiàn)當(dāng)時(shí)悖謬社會(huì)和精神廢墟的手段之一。回望歷史,西方戲劇中的怪誕元素實(shí)際上貫穿了全程,尤其在古希臘、中世紀(jì)、文藝復(fù)興、狂飆突進(jìn)及浪漫主義時(shí)期都有較為突出的表現(xiàn),但從來沒有一個(gè)時(shí)代像二十世紀(jì)這樣給予“怪誕”一個(gè)恰逢其時(shí)的舞臺(tái)使其得以大展拳腳,從一種創(chuàng)作技巧發(fā)展成一種獨(dú)具風(fēng)格和巧思的戲劇類型。怪誕戲劇之所以能具有跨越世代的生命力而不僅僅倚靠某個(gè)歷史節(jié)點(diǎn)的存在,是因?yàn)殡x不開其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內(nèi)核。現(xiàn)實(shí)主義是西方戲劇經(jīng)典的基石,比起單一范型,跨范型更能聚合優(yōu)勢、多元發(fā)展。當(dāng)下,始終是最強(qiáng)的凝聚力,能將各種創(chuàng)作技巧的能量聚合以發(fā)出時(shí)代的最強(qiáng)音。
皮蘭德婁的怪誕世界:人格面具
梁惠君在《皮蘭德婁戲劇中的“面具”功能研究》一文中提到,皮蘭德婁在作品中使用面具的淵源來自于其對意大利即興喜劇的繼承和革新,其中面具作為一種藝術(shù)手段由外轉(zhuǎn)內(nèi)、作為一種創(chuàng)作思維從具象到無形的變化尤其值得關(guān)注。如英國戲劇理論家斯泰恩所說:“歸根結(jié)底,皮蘭德婁戲劇思想的演變只能由他自己對周圍世界所抱有的世界觀的發(fā)展來予以解釋。”[3]P341這位有著扎實(shí)哲學(xué)社科學(xué)術(shù)背景的劇作家在創(chuàng)作初期的作品是詩歌和小說,并且已經(jīng)有所建樹,他首次投入戲劇創(chuàng)作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皮蘭德婁曾說“戰(zhàn)爭使我發(fā)現(xiàn)了戲劇”[4]P6,一戰(zhàn)為其家庭帶來的深重苦難及戰(zhàn)后千瘡百孔的現(xiàn)世生活使他認(rèn)識(shí)到,只有戲劇這一藝術(shù)形式才最適合傾泄自己的痛苦。“瘋癲”與“假面”是皮蘭德婁戲劇的重要關(guān)鍵詞,在他看來,世界是瘋癲的,所以每個(gè)人都需要戴上面具來抵御荒謬對個(gè)體的異化,來對抗殘酷對心靈的吞噬。
皮蘭德婁不但是個(gè)劇作家,還組建過劇團(tuán),排演過劇目。所以好幾個(gè)重要?jiǎng)”镜奈枧_(tái)提示都表現(xiàn)出他具備舞臺(tái)思維。比如在《六個(gè)尋找作者的劇中人》的舞臺(tái)提示中,他就對面具造型進(jìn)行了明確的說明:“要使這出戲取得舞臺(tái)效果,必須用一切辦法使這六個(gè)角色不與劇團(tuán)演員混淆,最有效和穩(wěn)妥的辦法就是給角色戴上面具……面具有助于表現(xiàn)文藝創(chuàng)作的人物形象和基本情感:父親的悔恨、兒子的憤怒、母親的痛苦。”[4]P70在這個(gè)階段,皮蘭德婁使用面具的目的已經(jīng)不再是傳統(tǒng)的遮擋和變形功能或者說是類型化的外在顯現(xiàn),而是貼近角色情感的“表情面具/臉譜面具”,具有趨向內(nèi)心化的符號(hào)功能。如果說戲中戲三部曲(《六個(gè)尋找作者的劇中人》《各行其是》《今晚我們即興演出》)是皮蘭德婁在文本和舞臺(tái)創(chuàng)作過程中對虛幻與真實(shí)、戲里與戲外的辯證思考與呈現(xiàn),那創(chuàng)作于1932年的《尋找自我》就是其后期對于人的自我在現(xiàn)實(shí)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間互相拉扯、迷惘掙扎所作的進(jìn)一步探索。
皮蘭德婁通過這部作品的主人公女演員朵娜塔表達(dá)了自己對于“人格面具”的理解和困惑,充滿哲理與思辨。就像他對自己的定位是“賦有哲學(xué)秉性的作家”[4]P1,皮蘭德婁在多部代表作中都呈現(xiàn)過其以辯證眼光看待現(xiàn)實(shí)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立場。在生命的最后時(shí)期,他作品中的面具已經(jīng)趨于無形——“人格即面具”。皮蘭德婁曾說:“每個(gè)人都無法確認(rèn)自己或別人只有一個(gè)自我、一個(gè)面孔……現(xiàn)代人有十萬個(gè)自我、十萬個(gè)面孔,因?yàn)橹車娜硕家愿髯圆煌姆绞綄徱曃覀儯總€(gè)人都只看到我們身上的一個(gè)方面,而這一個(gè)方面在每一瞬間又都處于不停歇的運(yùn)動(dòng)與變化中。”[4]P8劇中的朵娜塔亦是如此迷惘焦灼,苦惱于無法分辨舞臺(tái)上下哪一個(gè)自我才是真實(shí)的,因此在不斷地尋找自我中逐漸絕望,甚至意圖結(jié)束生命。這也是皮蘭德婁對于創(chuàng)作和表演的哲學(xué)觀:劇作家在文本中孕育了角色,角色是鮮活、永恒而獨(dú)立的,而舞臺(tái)“給了我們什么樣的面孔去演活人的角色呢?面具,面具 ”[5]P239。人們走上舞臺(tái)戴起面具——是用瞬間凝固的自我來演出角色,人們走下舞臺(tái)也依然戴著面具——是用千人千面的自我來抵御現(xiàn)實(shí)。這兩者的共性顯而易見,也因此顯得真實(shí)與虛幻的邊界前所未有地模糊,而自我與面具的沖突似乎也難以回避,那么這個(gè)“假面”難題是否有解決之道呢?劇中的女演員最后在舞臺(tái)上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答案:“是的,歸根結(jié)蒂,只能找到孤獨(dú)的自我。”[4]P302在作品創(chuàng)作的同一時(shí)期,皮蘭德婁恰好與一位女演員陷入愛河,頻繁書信,這很難不讓人將此歸結(jié)為對一種現(xiàn)實(shí)的影射。落幕前的獨(dú)白“這是真的……又一點(diǎn)兒也不是真的……唯有需要自我創(chuàng)造和創(chuàng)造的東西才是真的。僅僅在那個(gè)時(shí)候,才能找到自我”[4]P306,是否說明劇作家最后的結(jié)論是人人皆假面,唯有角色才能擁有自我呢?曾宣稱“正是借助于面具,戲劇作品的深刻意蘊(yùn)才得以展現(xiàn)”[6]P13的皮蘭德婁在不斷的創(chuàng)作中尋找、懷疑和否定自我,他的人生與作品在此意義上本身就是“后設(shè)”和“戲中戲”的呈現(xiàn),達(dá)成一種極致的多重怪誕。這也是劇作家對于他所身處的那個(gè)時(shí)代最為振聾發(fā)聵的發(fā)聲和最具現(xiàn)實(shí)主義精神的疾呼。
迪倫馬特的怪誕世界:心靈的迷宮
弗里德里希·迪倫馬特的創(chuàng)作始于二十世紀(jì)四五十年代,也就是戰(zhàn)后初期。他在1955年發(fā)表的《戲劇問題》一文中曾提出“當(dāng)今的國家成了一個(gè)匿名的官僚機(jī)構(gòu)”“人不再是自己行為的主體”等觀點(diǎn),顯露出他認(rèn)為很多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是被異化了的,是充滿怪誕感的。而創(chuàng)作于1962年的《物理學(xué)家》是以當(dāng)時(shí)熱火朝天的核軍備競賽作為故事背景,迪倫馬特用扭曲荒謬的怪誕手法呈現(xiàn)出一種世界局勢的鏡像感,其中充滿了他用喜劇思維“感知一個(gè)面目全非的世界”并以此巧妙地建構(gòu)其現(xiàn)實(shí)性和悲劇性的獨(dú)特創(chuàng)作方法。
縱觀迪倫馬特的幾部重要作品如《羅慕路斯大帝》《密西西比現(xiàn)生的婚姻》《天使來到巴比倫》《老婦還鄉(xiāng)》,無論是否取材于現(xiàn)實(shí),都著眼于戰(zhàn)后西方的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問題及對技術(shù)和理性的反思。中外學(xué)者都曾探究過迪倫馬特的“迷宮原型”。比如海因茲·路德維希·阿諾德在《戲劇作為迷宮世界的映像》中提出:迷宮是迪倫馬特為這個(gè)世界所做的神話象征。”[7]P12廖俊博士也在《迪倫馬特戲劇中的迷宮世界》中專門梳理了迪倫馬特對迷宮神話的理解及其作品中豐富的迷宮意象。當(dāng)這種看待現(xiàn)實(shí)世界如同看待一個(gè)心靈迷宮的思維被運(yùn)用到戲劇創(chuàng)作中時(shí),作品顯示出亦真亦幻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怪誕感也就變得順理成章了。迪倫馬特認(rèn)為自己所身處的世界就是一個(gè)巨大的迷宮,并將之投射到筆下,用他所理解的怪誕——即“合乎邏輯的在現(xiàn)實(shí)中必然遇到的矛盾體”[8]P7呈現(xiàn)戰(zhàn)后西方的精神夢魘。理性和科學(xué)的發(fā)展究竟會(huì)推動(dòng)人類走向何處?他在《物理學(xué)家》中提出的:“我們的科學(xué)已變得恐怖,我們的研究已變得危險(xiǎn),我們的認(rèn)識(shí)已成為致命的了”[9]P605,反映出其具備的世界意識(shí)和作為人類一員的全局觀。通過講述這樣一個(gè)充滿絕望感的故事,他站在現(xiàn)實(shí)與虛幻的邊界發(fā)出警示,雙重迷宮及不知身處迷宮內(nèi)外的環(huán)套結(jié)構(gòu)足以讓讀者也陷入莊子夢蝶的悖謬中。
巴赫金曾表示:“怪誕風(fēng)格的本身在假面中得到鮮明的展示。”[10]P47《物理學(xué)家》中的四個(gè)主要角色也都以假面示人,三個(gè)物理學(xué)家扮演著瘋子,瘋狂的女院長扮演著精神病專家,雙方的假面互為影射。劇中的瘋?cè)嗽阂睬∷埔粋€(gè)迷宮,自恃高尚的角色們懷揣著各自的“救世理想”,按照自己對這個(gè)世界運(yùn)行規(guī)則的理解,企圖“以惡行,換善果”。他們拋妻棄子、濫殺無辜、巧取豪奪,迷宮里處處是謊言、狂妄和瘋癲構(gòu)成的隱絆,因此只能通向無盡的黑暗——亦即在心靈和感知上的悖謬。這也是作家對“怪誕”的理解①。
迪倫馬特在《關(guān)于〈物理學(xué)家〉的二十一點(diǎn)說明 》中連續(xù)提到:
十一,故事是悖謬的。
十二,劇作家同邏輯家一樣不能避免這種悖謬。
十三,物理學(xué)家同邏輯家一樣不能避免這種悖謬。
十四,一個(gè)描寫物理學(xué)家的劇本必須是悖謬的。
這四點(diǎn)說明直接點(diǎn)出了劇作家與角色、劇本與故事分別在現(xiàn)實(shí)與虛幻層面的一體兩面性。科學(xué)本應(yīng)造福于世界,世界卻因科學(xué)而面臨致命的威脅;技術(shù)本應(yīng)服務(wù)于人類,人類卻因技術(shù)而異化扭曲。作者眼中的現(xiàn)實(shí)因此而顯得怪誕不經(jīng)。反過來明明是虛構(gòu)的故事,人物與情節(jié)同樣未因其怪誕離奇的設(shè)定而喪失現(xiàn)實(shí)感。在思慮周密的計(jì)劃中置入偶然與轉(zhuǎn)折是非常典型的喜劇創(chuàng)作手法,但故事卻導(dǎo)向一種喜中透悲的復(fù)雜情緒、一種虛中帶實(shí)的浸入體驗(yàn)。現(xiàn)實(shí)性在怪誕的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下被撕扯開皮囊、榨取出血肉,更顯露其赤裸本質(zhì)。
迪倫馬特的迷宮式創(chuàng)作思維為現(xiàn)實(shí)主義怪誕提供了豐富的營養(yǎng),人們開始意識(shí)到即使是取材于當(dāng)下,也能夠在充滿故事性、想象力和娛樂性的同時(shí)給予讀者咀嚼哲理、辯證思考的樂趣。作者也以身示范了身處迷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自己正陷迷途。現(xiàn)代人的心靈需要在戲劇中被激活、被刺醒,從而看見自己的迷惘與恐懼。
具有現(xiàn)實(shí)主義內(nèi)核的怪誕戲劇很顯然能發(fā)揮跨范型的聚合效應(yīng),集各種創(chuàng)作技巧的能量于一身,煥發(fā)出跨越世代的生命力。恰如二十一世紀(jì)的今天,俄烏沖突正在重演《物理學(xué)家》呈現(xiàn)的科學(xué)恐怖,肆虐全球近三年的新冠疫情導(dǎo)致全球性割裂,使現(xiàn)代人再陷前所未有的隔絕與苦悶,《尋找自我》中的身份悖論也因此產(chǎn)生了新的語境。可見,現(xiàn)實(shí)主義怪誕這種創(chuàng)作手法在呈現(xiàn)和連接當(dāng)下上的強(qiáng)大力量值得藝術(shù)家們思考和借鑒。
參考文獻(xiàn):
[1]陳世雄:《現(xiàn)代歐美戲劇史(中)》,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10年
[2]陳世雄:《布萊希特戲劇中的怪誕》,《戲劇》,1998年第四期
[3]斯泰恩:《現(xiàn)代戲劇理論與實(shí)踐》,劉國彬譯,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2年
[4]皮蘭德婁著,呂同六等譯:《高山巨人——皮蘭德婁劇作選》,廣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
[5]柳鳴九:《二十世紀(jì)文學(xué)中的荒誕》,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
[6]梁惠君:《皮蘭德婁戲劇中的“面具”功能研究》,華中師范大學(xué)碩士論文,2016年
[7]廖俊:《迪倫馬特戲劇中的迷宮世界》,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博士論文,2007年
[8]弗里德里希·迪倫馬特:《迪倫馬特戲劇集(上)》,葉廷芳等譯,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9年
[9]弗里德里希·迪倫馬特:《迪倫馬特戲劇集(下)》,葉廷芳等譯,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9年
[10]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錢中文等譯,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注釋:
①迪倫馬特曾在《戲劇問題》一文中界定“怪誕”不過是“一種感知的悖謬”。
(作者單位:上海戲劇學(xué)院 )
責(zé)任編輯 岳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