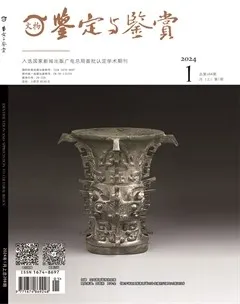廣西地區兩晉南朝墓分期研究

摘 要:根據對墓葬形制及隨葬器物的類型學分析,結合墓葬紀年及相鄰地區同時期墓葬研究成果,將廣西地區兩晉南朝墓分為西晉、東晉、南朝早中期、南朝晚期四期,并歸納墓形與隨葬器物的總體特征及演變特點,指出桂東北、西江地區、合浦三地存在的區域差異。
關鍵詞:廣西地區;兩晉;南朝;墓葬分期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4.01.024
廣西地區迄今已發表的兩晉南朝時期墓葬材料,主要分布于桂林、陽朔、靈川、興安、全州、永福、融安、恭城、平樂、鐘山、賀州、昭平、梧州、藤縣、蒼梧、貴港、合浦等市縣,墓葬形制及隨葬器物既有一般兩晉南朝墓的特征,又明顯帶有嶺南乃至廣西地方特點。學界迄今暫未有對廣西兩晉南朝墓進行系統的類型學及分期研究。本文不揣谫陋,試對相關材料進行分析及論述。
1 墓葬類型學分析
1.1 墓葬形制分析
根據墓葬材質、平面形狀及墓內結構等特征,將墓葬分為三類八型(圖1)。
1.1.1 第一類:磚室墓
A型:平面呈“中”字形,由甬道、前室、后室構成,前室寬度明顯大于后室。根據有無帶側室,分為Aa、Ab兩個亞型。Aa型,不帶側室,墓長約7米,規模較大。甬道及前室比例變大、后室變小,墓底由不分級到前后分級,可分兩式:Ⅰ式,墓例梧州富民坊墓①;Ⅱ式,墓例融安安寧M4②。Ab型,帶側室,墓長約5米,墓例貴港梁君垌M11③。
B型:平面呈“凸”字形,由甬道及棺室構成,墓長一般4~6米,規模中等。根據棺室形狀以及磚柱分室情況,分為Ba、Bb、Bc三個亞型。Ba型,棺室前后寬度不一,略呈梯形,墓內無磚柱。甬道變短,可分兩式:Ⅰ式,墓例鐘山西門嶺墓④;Ⅱ式,墓例陽朔龍盤嶺M25⑤。Bb型,棺室呈長方形,墓內無磚柱。墓底由不分級到前中后分級,并形成后室,可分兩式:Ⅰ式,墓例興安羅家山M1⑥、興安陽西嶺M2⑦、恭城大灣地M2⑧;Ⅱ式,墓例融安安寧M2⑨。Bc型,墓內以磚柱將棺室略分為前后室。墓底由不分級到前中后分級,規模顯著增大(墓長可達10米),可分兩式:Ⅰ式,墓例合浦羅屋村M5a⑩、恭城大灣地M3k;Ⅱ式,墓例貴港梁君垌M3l。
C型:平面呈長方形。根據墓葬規模、墓頂類型、墓內分室等情況,分為Ca、Cb、Cc三個亞型。Ca型,券頂,不分室,墓長一般3~4米,規模較小,墓例合浦電廠M4m。Cb型,疊澀頂或小平頂,墓形窄長,墓長一般約2米,規模甚小,墓例賀州鳳凰嶺M16n。Cc型,券頂,墓內以磚柱及承券分成甬道、前室、過道、后室等部分,墓長近8米,規模較大,墓例藤縣跑馬坪M1o。
D型:平面呈“甲”字形,由前室及后室構成,前室寬短。根據墓葬規模及墓頂類型,分為Da、Db兩個亞型。Da型,券頂,墓長約5米,墓例合浦羅屋村M9p。Db型,疊澀頂,后室窄長,墓長約2~4米,墓例賀州鳳凰嶺M8q。
1.1.2 第二類:土坑墓
A型:平面呈長方形,墓長3~5米,墓例陽朔龍盤嶺M13r、融安安寧M5s。
B型:平面呈“凸”字形,帶甬道(短墓道),墓長5~7米,規模較大,墓例賀州芒棟嶺M2t。
1.1.3 第三類:石室墓
A型:平面近正方形,墓長3~5米,墓例賀州鳳凰嶺M1u。
B型:平面呈“凸”字形,帶甬道(短墓道),墓長4~5米,墓例昭平篁竹M11v、平樂銀山嶺M140w。
1.2 隨葬器物分析
隨葬器物以青瓷器為主,常見器型有帶系罐、碗(盞)、缽(盂)、盤(碟)、雞首壺、唾壺、盤口壺、硯,部分早期墓葬常見陶敞口罐與陶釜。少量帶系罐為陶或釉陶,應系青瓷帶系罐的早期形制,演變規律較明顯,故歸入青瓷器同類器型中一并分析(圖2)。器名前如無特別指明質地,皆為瓷器。
帶系罐,大部分帶四系,也有雙系及六系,根據罐身形態,分為A、B、C、D、E、F、G七型。
A型,圓腹罐,器身變高,下腹逐漸內收,可分三式:Ⅰ式,器例賀州鳳凰嶺M8∶1x;Ⅱ式,器例平樂銀山嶺M140∶8y;Ⅲ式,器例藤縣跑馬坪M1的“四耳罐”z。
B型,溜肩罐,下腹逐漸內收,可分兩式:Ⅰ式,器例貴港梁君垌M11∶擾8;Ⅱ式,器例桂林橫塘農場M1的“四耳罐”、藤縣跑馬坪M2的“四耳罐”。
C型,桶形罐,腹部漸鼓,下腹內收,由陶質變為瓷質,可分兩式:Ⅰ式,器例鐘山張屋村M2∶1、賀州鳳凰嶺M17b∶1;Ⅱ式,器例恭城大灣地M2∶24。
D型,卵形罐,最大腹徑下移,器身變矮,可分兩式:Ⅰ式,器例興安羅家山M1∶1;Ⅱ式,器例陽朔龍盤嶺M25∶16。
E型,扁腹罐,據器身高矮及陶質比例,分為Ea、Eb兩個亞型。Ea型,矮身,四系,瓷質。腹部漸扁,可分兩式:Ⅰ式,器例梧州北山M1∶7;Ⅱ式,器例陽朔龍盤嶺M25∶19。Eb型,高身,由陶質變為瓷質,由雙系變為四系,可分兩式:Ⅰ式,器例昭平篁竹M11∶8;Ⅱ式,器例興安陽西嶺M2∶11。
F型,大口罐,由雙復系變成了四系,下腹漸內收,可分為兩式:Ⅰ式,器例梧州北山M1∶2、合浦羅屋村M5a∶20;Ⅱ式,器例恭城長茶地M1∶3。
G型,雙唇罐,敞口雙唇,鼓腹。器身變高瘦,由四系變為六系,可分兩式:Ⅰ式,器例陽朔龍盤嶺M25∶6、陽朔龍盤嶺M13∶11;Ⅱ式,器例恭城大灣地M1∶7。
碗(盞),敞口略直、淺腹。根據底部或足部形態,分為A、B、C、D四型。
A型,平底,腹部漸深,口沿凹槽消失,可分兩式:Ⅰ式,器例賀州鳳凰嶺M6∶9、賀州鳳凰嶺M17b∶1;Ⅱ式,器例桂林橫塘農場M1的“平底碗”。
B型,餅足,腹部漸深,碗口變窄小,口沿凹槽消失,餅足變高窄,可分兩式:Ⅰ式,器例鐘山紅花永嘉六年墓、賀州鳳凰嶺M16a∶1;Ⅱ式,器例賀州鳳凰嶺M40∶2、恭城長茶地M3∶19。
C型,假餅足,器例鐘山張屋村M2∶12。
D型,高圈足,腹部變淺、圈足變高,可分兩式:Ⅰ式,器例賀縣芒棟嶺M2∶29;Ⅱ式,器例永福壽城墓的“高足盤”。
缽(盂),斂口,深腹。根據底部形態,分為A、B兩型。
A型,圈足,肩部帶弦紋。器例昭平篁竹M11∶1、陽朔龍盤嶺M25∶3。
B型,平底。腹部變深、底部變小,可分三式:Ⅰ式,器例鐘山張屋村M2∶51;Ⅱ式,器例賀州鳳凰嶺M4∶1、陽朔龍盤嶺M23∶1;Ⅲ式,器例恭城長茶地M1∶47。
盤(碟),敞口淺腹。根據底部形態,分為A、B、C三型。
A型,平底。據底部大小分Aa、Ab兩個亞型。Aa型,大平底,斜直腹。器例梧州北山M2的“洗”、桂林橫塘農場M1的“盤”。Ab型,小平底。由斜直腹變為弧腹,可分兩式:Ⅰ式,器例貴港梁君垌M11:擾9;Ⅱ式,器例藤縣跑馬坪M1的“盤”。
B型,餅足,器例融安安寧M5∶11。
C型,圜底,器例恭城長茶地M3∶6。
雞首壺,盤口,雞頭形流,帶把。器身變高瘦,下腹漸內收,可分三式:Ⅰ式,器例梧州北山M2;Ⅱ式,器例桂林橫塘農場M2;Ⅲ式,器例藤縣跑馬坪M2。
唾壺,盤口,矮餅足,腹部漸扁,頸部漸束,盤口漸窄,可分三式:Ⅰ式,器例合浦羅屋村M5a∶13;Ⅱ式,器例恭城長茶地M2∶5;Ⅲ式,器例藤縣跑馬坪M1。
盤口壺,盤口,四系或六系,按整體形態分為A、B兩型。
A型,寬口,鼓腹,平底。頸部變長,器身變高,可分三式:Ⅰ式,器例陽朔龍盤嶺M25∶33;Ⅱ式,器例恭城大灣地M2∶20;Ⅲ式,器例恭城長茶地M3∶42。
B型,窄口,溜肩,短頸,餅足。腹部變鼓,可分兩式:Ⅰ式,器例恭城大灣地M2∶8;Ⅱ式,器例恭城長茶地M3∶40。
硯,根據底部及壁緣形態,分為A、B兩型。
A型,底部平,斜直壁,三錐足。器例陽朔龍盤嶺M23∶5。
B型,底部向內隆起,子母壁。隆起幅度加劇,由三足變為五足再到七足,足部形態由錐足變為蹄足再變為乳足,可分三式:Ⅰ式,器例陽朔龍盤嶺M25∶30;Ⅱ式,器例恭城長茶地M1∶4;Ⅲ式,器例融安安寧M2。
陶敞口罐,敞口,鼓肩。器身的拍印紋消失,由無系變為四豎系,可分兩式:Ⅰ式,器例鐘山西門嶺墓的“Ⅱ式陶罐”;Ⅱ式,器例陽朔龍盤嶺M13∶2。
陶釜,敞口,圜底,表面拍印方格紋。根據口沿有無附耳,分為A、B兩型。
A型,無附耳,器例鐘山張屋村M2∶52。
B型,帶雙耳,器例賀州鳳凰嶺M8∶3。
2 分期與年代
根據墓形、隨葬品型式的組合及共存情況,結合紀年材料,并參考南方地區特別是廣東晉南朝墓分期研究成果,可將廣西兩晉南朝墓分為四期:
2.1 第一期西晉
磚室墓流行AaⅠ、Ab、BaⅠ、BbⅠ、Db等形制,以中等規模墓葬為主;土坑墓形制單一;石室墓有一定比例。隨葬器物方面,帶系罐各型皆為Ⅰ式(除G型未出現);碗常見A型、B型,皆為Ⅰ式;缽亦較常見;盤出現AbⅠ(杯盤)。C型和D型碗、陶敞口罐、陶釜為本期特色器型。總體而言,本期器類相對單一,陶器又有一定占比。雙系或四系的陶桶形罐、雙系陶扁身罐以及陶敞口罐、陶釜等,在廣西已發現的東漢晚期至三國墓中較常見,高圈足陶碗亦見于東漢墓中。本期的CⅠ帶系罐造型比東漢晚期至三國的桶形帶系罐稍顯圓潤,EbⅠ雙系罐以及DⅠ碗部分施加青釉,加上與其他青瓷器的共存組合,可以判斷本期的上限基本進入西晉,至少亦在吳晉之交。
另外,根據部分隨葬器物型式,本期又可分為前后兩段:EbⅠ帶系罐、陶敞口罐、B型陶釜僅見于前段,BⅠ、EaⅠ、FⅠ帶系罐、BⅠ碗、AbⅠ盤僅在后段出現,而D型碗、B型缽在前后兩段也存在式樣的演變。
本期四座紀年墓葬的隨葬器物型式風格均屬后段,最早為元康八年(298年,貴港梁君垌M11),最晚為永嘉六年(312年,鐘山紅花墓),據此可將后段年代大體劃定為西晉中晚期,前段則為吳晉之交至西晉中期。
2.2 第二期東晉
磚室墓以中小型墓為主,A型消失,B型形制豐富,其中Ba型發展為Ⅱ式,并出現加砌磚柱進行分室的形式(BcⅠ),出現C型墓,Da型出現,Db型消失;土坑墓及石室墓大量減少,石室墓僅見B型。隨葬器物方面,帶系罐A、D、E型均發展為Ⅱ式,新出現G型;碗A、B型變化不大,C、D型消失;新出現Aa型盤、雞首壺、唾壺、盤口壺、硯等青瓷器型。陶敞口罐、陶釜消失。
本期兩座紀年墓,年代分別為泰元四年(379年,興安界首墓)及義熙五年(409年,興安陽西嶺M2)。綜合隨葬器物,特別是出現雞首壺、唾壺、盤口壺、硯等兩晉常見器物,加上墓內未見南朝以后大量出現的加砌磚柱、承券、墓底分級等現象,可將本期年代基本定為東晉時期。
2.3 第三期南朝早中期
磚室墓以中型墓為主,Aa型發展為Ⅱ式,BbⅠ、BcⅠ繼續出現,C、D型墓消失。土坑墓僅見A型,持續至第四期。石室墓消失。總體而言墓葬形制趨向單一,而延續的墓形未見明顯復雜化趨勢。隨葬器物方面,帶系罐器型明顯減少,D、E型消失,B、C、F型發展為Ⅱ式;A型和B型碗、雞首壺、唾壺、A型盤口壺、硯發展為Ⅱ式,B型缽發展為Ⅲ式,新出現B型盤口壺。
本期缺乏有效紀年墓,但與第四期墓葬及隨葬器物形制中的南朝晚期特點有明顯差別,因此年代大致定為南朝早中期。
2.4 第四期南朝晚期
磚室墓Bb、Bc發展為Ⅱ式,連同新出現的Cc型,反映了墓內設施的復雜化,甚至出現大型墓。隨葬器物方面,帶系罐Aa型發展為Ⅲ式,鼓腹及下腹部內收明顯;G型發展為高瘦的Ⅱ式。碗僅見BⅡ,餅足高窄。盤新出現C、D型,且D型盤內常見印花。雞首壺、唾壺、盤口壺、硯均存在式的變化。
本期帶系罐鼓腹內收、盤內出現印花等特點,見于廣東地區南朝晚期墓;乳狀足硯見于廣東隋墓中;AⅢ盤口壺頸部較廣西灌陽隋大業七年(612)墓的盤口壺略短,年代應在隋之前。本期紀年墓葬見融安安寧M2的“己亥”年(579)。因此,可將本期年代大致定為南朝晚期。
3 墓葬總體特征及區域差異
3.1 總體特征及演變特點
在墓葬構造及形制方面,兩晉時期以略呈梯形的“凸”字形磚室墓及石室墓最具地方特色。前者暫不見于嶺南以外地區,兩晉后墓壁逐漸變平直,向普通“凸”字形磚室墓發展;后者從東漢后期開始出現,在西晉中晚期由方形穹隆頂變為長方形券頂,應系模仿普通“凸”字形或長方形券頂磚室墓的形制,以石料取代磚塊做筑墓材料。從數量上看。磚室墓以普通“凸”字形墓數量最多,而南方地區常見的長方形墓數量較少。西晉時仍流行東漢及三國時期常見的“中”字形磚室墓,至東晉后消失。墓內裝飾承券或磚柱的做法在東晉時零星出現,到南朝中期,普通“凸”字形墓的承券稍變復雜,臺階出現,有的墓葬墓底分級。承券等墓內設施的出現與其他地區相比,出現的較晚,亦較為簡單,僅在貴港發現有復雜的南朝晚期大型墓。
隨葬器物方面,西晉時陶器仍有一定比例,陶桶形罐、陶扁腹罐、陶印紋敞口罐等在廣西東漢晚期至三國墓中已經出現,或為嶺南兩漢以來的陶提桶、陶瓿、陶甕在器型上的發展。陶扁腹罐、陶桶形罐在吳晉之際由雙系發展為四系,并分別在東晉、南朝前期完成由陶質到青瓷的變化。東晉以后,最重要的變化當屬四系雙唇罐、雞首壺、盤口壺、唾壺、硯等青瓷器物群的出現,唾壺、硯、雞首壺、盤口壺是兩晉時期長江下游的常見器物;四系雙唇罐造型獨特,僅見于廣西。南朝以后,器物造型明顯變高變長,雞首壺、盤還出現了蓮花紋。總體器物的變化趨勢略同嶺南其他地區。
3.2 區域差異
3.2.1 桂東北地區
在桂東北地區(桂林、陽朔、靈川、興安、全州、永福、融安、恭城、平樂、鐘山、賀州、昭平),未見典型的“中”字形墓,以“凸”字形墓為主,尤其是略呈梯形的“凸”字形墓,為該地區所獨有。普通“凸”字形墓不流行磚柱、承券進行分室,但在融安地區,后壁的頭龕向進深發展,以致脫離棺室而形成獨立的后室,或通過墓底分級形成后室,形成另一種“中”字形三室墓,實際上是“凸”字形墓的進一步復雜化。疊澀頂長方形窄長小墓集中見于賀州,亦同時見于廣東的深圳、韶關等地。該地區也是廣西石室墓集中分布區域,石室墓亦見于貴州中部,應與西南地區的石灰巖地貌有關。土坑墓也較多。西晉時期,雙系扁腹帶系罐、高圈足碗、陶敞口罐、陶釜為該地區特色器物。東晉以后,雙唇罐、盤口壺為該地區特色器物,盤口壺肩部帶橫系,造型與同時期兩湖地區的盤口壺較為相似,而與江西地區肩置豎耳的盤口壺有所不同。此外,該地區滑石器種類遠比其他區域豐富,這也與當地自然環境密切相關。
3.2.2 西江流域地區
在西江流域地區(梧州、藤縣、蒼梧、貴港),墓葬形制及隨葬器物與廣東除北部外的大部分地區面貌極為相似,是廣西大中型分室構筑墓的集中分布區,南朝后墓內設施常見復雜化。疊澀頂小墓僅在梧州發現。不見石室墓,土坑墓也極少。
3.2.3 合浦地區
在合浦地區,目前晉墓發現較少,缺乏南朝時期墓葬。從現有材料看,該地區晉墓以中型墓為主,東晉時期已流行砌磚柱,“甲”字形券頂墓為該地區獨有(廣西以外還見于廣東的廣州地區)。不見石室墓,土坑墓亦較少。隨葬器物常見陶器、高溫釉陶與青瓷并存,陶器中缺乏桂東北地區常見的雙系扁腹帶系罐、陶敞口罐、陶釜等,以無系幾何印文陶罐為主。青瓷器型較少,不見雞首壺、盤口壺、硯等典型器物。總體來說,與西江流域地區及廣東大部分地區有一定相似性,同時東漢及三國墓因素較為濃厚。
4 余論
廣西地區兩晉南朝墓所分四期,與兩晉南朝政權更替基本一致。總體而言,西晉時期嶺南本地東漢三國墓葬元素仍較強勢,長江下游政治中心文化元素未能進入廣西,因此西晉墓中新舊因素并存。東晉以后,隨著大量流民南遷入嶺,大量長江下游常見的隨葬器物通過鄂、湘經靈渠—漓江傳入桂東北地區,繼而影響桂東南地區。南朝以后贛江—大庾嶺逐漸使用,江西地區的墓內復雜化筑造傳統影響了廣東,繼而通過西江流域影響梧州、貴港等地的大中型墓。合浦在兩漢時期是最重要的對外港口,漢墓極其豐富,晉以后其交通地位逐漸衰落,一定程度上影響其兩晉南朝墓的數量及規模。桂東北地區、西江流域地區、合浦地區墓葬面貌存在的區域差異,除受上述人群遷徙、交通區位原因影響外,還受其長期分屬湘州、廣州、交州(越州)三個不同的政區管轄有關。
注釋
①李乃賢.廣西壯族自治區梧州市富民坊南朝墓[J].考古,1983(9):859-860.
②s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融安安寧南朝墓發掘簡報[J].考古,1984(7):627-635.
③l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貴港市博物館,中山大學.廣西貴港馬鞍嶺梁君垌漢至南朝墓發掘報告[J].考古學報,2014(1):67-108.
④莫測境.廣西鐘山縣西門嶺發現六朝墓[J].考古,1994(10):952-953.
⑤r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桂林市文物工作隊,陽朔縣文物管理所.2005年陽朔縣高田鎮古墓葬發掘報告[C]//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廣西考古文集(第三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132-225.
⑥⑦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全州至興安高速公路沿線兩晉南朝墓發掘報告[C]//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廣西考古文集(第四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258-275.
⑧k俸艷.廣西恭城縣黃嶺大灣地南朝墓[J].考古,1996(8):45-48.
⑨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壯族自治區融安縣南朝墓[J].考古,1983(9):790-792.
⑩mp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合浦縣文物管理局.2009—2013年合浦漢晉墓發掘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324-348.
nqux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賀州市博物館.賀州鳳凰嶺古墓群考古發掘報告[C]//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廣西考古文集(第五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138-252.
oz吳柱盈.廣西藤縣跑馬坪發現南朝墓[J].考古,1991(6):569-572.
t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賀縣兩座東吳墓[J].考古與文物,1984(4):9-12.
v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昭平縣文物研究所.昭平縣篁竹、白馬山古墓葬發掘報告[C]//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廣西考古文集(第三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386-411.
wy蔣廷瑜.平樂銀山嶺漢墓[J].考古學報,1978(4):467-495.
桂林市文物工作隊.桂林市東郊南朝墓清理簡報[J].考古,1988(5):457-459.
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鐘山縣文物管理所.廣西鐘山縣張屋村漢、晉墓發掘簡報[J].四川文物,2018(1):32-44.
黃鴻植.廣西梧州市晉代磚室墓[J].考古,1981(3):285-286.
王振鏞,覃圣敏.廣西恭城新街長茶地南朝墓[J].考古,1979(2):190-192.
莫測境.廣西鐘山縣發現一座西晉紀年墓[J].考古,1988(7):669.
黃啟善.廣西永福縣壽城南朝墓[J].考古,1983(7):612-613.
李乃賢.梧州市北山東晉墓[C]//文物編輯委員會.文物資料叢刊(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129-130.
韋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馬啟亮.廣東兩晉南朝墓葬分期研究[J].文博學刊,2019(1):30-41.
興安縣博物館.興安縣界首東晉紀年墓清理簡報[J].廣西文物,1990(2):68-70.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執信中學隋唐墓發掘簡報[C]//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羊城考古發現與研究(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147-160.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灌陽縣文物管理所.廣西灌陽縣畫眉井隋代紀年墓[C]//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考古文集:第二輯:紀念廣西考古七十周年專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381-388.
該墓紀年為“己亥”,原報告推斷為南朝中期梁天監十八年(519),但該墓出土的乳狀足硯明顯具有更晚期的特征,在廣東發現的同類硯甚至已到隋代。考慮到該墓總體仍為南朝晚期特征,本文將“己亥”定為南朝末的5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