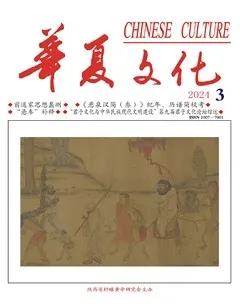從漢代解經模式小議肩水金關 漢簡《孝經》殘簡
肩水金關漢簡73EJT31:44A+ T30:55A有“上而不驕者,高而不危;制節謹度而能分施者,滿而不溢。《易》曰:‘亢龍有悔。9言驕溢也。亢之為言”一段文字,諸家對此段文字的性質爭議頗多。張固也、田雅寧統計說:“劉嬌認為簡文大部分‘應屬經文,自“亢之為言”起才是“說”的內容9 ,其中引《易》與今本章末引《詩》不同,‘簡文所反映的《孝經》跟今傳本《孝經》有可能屬于不同的傳本9。黃浩波認為‘簡文與《孝經》經文異文頗多9 ,‘不宜再以經文視之9。常燕娜認為‘從語氣、文意來看,顯然是對《孝經》的解說9。魏振龍也贊同‘此簡是對《諸侯章》相關語句的傳注或解說9。但根據本文隨后的分析,‘而能分施者9不必為漢人之辭,所以前四句當為經文;漢簡此章與今本同樣引《詩》,所以自‘《易》曰9以下當為傳注或解說。”(張固也、田雅寧:《地灣漢簡〈孝經〉殘文考論》,《出土文獻》2024年底2期,第83頁。)這一現象的緣由,實際上是因為這段文字中既有見于《孝經》的內容,又有不見于《孝經》的內容。我們認為,劉嬌、常燕娜、魏振龍等認為這是一個經文和解文相兼的《孝經》文本,是比較接近客觀事實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了解漢代的解經模式。


漢代解《孝經》則兩種方式并存,《文選.彥宏〈三國名臣序贊〉》注引《孝經援神契》:“得萬國之歡心,人說喜,無怨聲。”“得萬國之歡心”見《圣治章》,采用經文加疏通大義方式。《禮記.玉藻》正義引《援神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闊,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大微,于辰爲巳,是以登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亦見《圣治章》,采用經文加訓沽文字的方式。金關漢簡《孝經》中“而能分施”及引《易》以后文字,均屬于疏通大義類解文,直接插入經文之中。
此處還有個關鍵問題,“亢之為言”明顯為闡釋“亢”字含義的文文,與直接解釋《孝經》的內容存在一定距離,其何以嵌入此中。這同樣與漢代的解經模式有關,漢代解經不僅只有解經的文字,還有解解經的文字(對注解的再次闡釋) ,乃至解解解經的文字(對注解闡釋的進一步解釋) ,疊床架屋,形成了多層次、遞歸式的解經體系,正是漢代今文經學的一大特點。《漢書.儒林傳》:“自武帝立《五經》博±,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余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一經說至百余萬言”不是說對經文的解釋至百余萬言,而是指師傳過程中,學生對老師所傳進行解說,學生的學生復對老師所傳進行解說,導致其內容層層累積。《藝文志》曰:“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后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后能言。”“后進彌以馳逐”即是此意。《藝文志》說“破壞形體”,即是因為兩句經文中間,可能間隔了數萬字的解文,導致閱讀起來很不方便。今文經學繁繽冗雜的特點,也最終導致其在歷史的長河中消亡。這種解中有解的模式,今僅在《白虎通》中多有遺存。如《禮樂篇》:
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
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膳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焉。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舖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
《弟子職》:“暮食復禮。”士也。食力無數。
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飢即食,飽即作,故無數。(陳立:《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118—119頁。)
《禮樂篇》討論的是王者禮樂,此處首句“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是屬于王者樂的范疇,尚切合標題。第二段“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承上復論王者日四食,第三段承第二段引《論語》論天子、諸侯、卿大夫日食之差別,第四段因第三段論±、庶人之食,第五段因第四段論何以庶人“食力無數”。自第二段以下,已經與“樂”無關。金關漢簡《孝經》“亢之為言”以下,即是這種情況。
(作者:山東省濟南市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博士后,郵編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