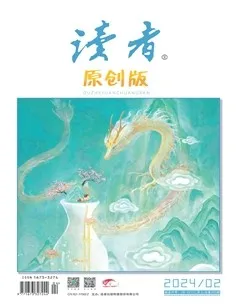老年小姨的星辰大海
肖遙
一大早,小姨烙了蔥油餅,叫我和表妹一會兒去西島時帶上。想想這畫面,多么炫酷—在文藝又浪漫的西島,別的女孩都在趕海,拎著小桶撿海蠣子、皮皮蝦;而同為淑女的我和表妹坐在礁石上,吹著海風,啃著“鍋盔”,宛如征戰途中的秦軍士兵……
我小姨說你們別笑,出去就知道了,還是咱家鄉飯實在、頂飽!前幾年在海南,小姨和姨父只要去附近旅行,無論是去海花島還是去呀諾達,走前都會烙個蔥油餅,再帶兩個蘋果上路。小姨和姨父如今定居在海島,老兩口每天做的還是家鄉飯—臊子面、包子、紅豆稀飯、三鮮湯、土豆絲、漿水攪團……
他們未曾改變的除了飲食習慣,還有對鄉音的執著。聽說姨父剛來的時候,在小區里溜達,用手機放秦腔,“哇哇呀呀”的老生唱腔聽上去嘔啞啁哳,一個大姐追著姨父批評:“大哥,咱這兒可是文明小區,您這也太吵了吧!”小姨把這件事當笑話逢人便講,還揭發說姨父其實聽不懂秦腔。盡管小姨把這事當笑話,但我還是聽出了姨父的些許寂寞—他的懷鄉之情無處抒發,潛意識里是想讓自己周圍多些鄉音。
對小姨在海南買房這件事,我媽認為是她妹妹這輩子干過最離譜的事—老了老了,背井離鄉跑到天涯海角,過著舉目無親的生活。親戚們包括小姨的兒女也覺得有點突兀。那幾年,小姨常外出游玩,她旅行的目的地越來越遠,直至五年前,她跟著房屋中介旅行團到處看房,在這個山清水秀的縣城定居下來。在親戚朋友眼里中規中矩的小姨,忽然“事了拂衣去”“片葉不沾身”,干了件這么有想象力的事情,畢竟,在這么一個小縣城買房,完全沒有投資價值,但她還是做了,哪怕僅僅是為了享受陽光、沙灘、海浪、椰汁。這件事對節儉勤懇了一輩子的小姨來說,多少有點兒任性。
小姨有這么一個星辰大海的夢,細細追溯是露過端倪的。

小姨19歲就嫁人了,小姨和她的女兒,頭發從來都紋絲不亂。每次小姨給我扎辮子,我頭皮都要疼好幾天。小姨的婆婆是村里有名的“歪(厲害)老太太”,在那個黃土高原上的村莊,小姨的婆家是村里唯一保持一塵不染的,因此老太太對兒媳也高標準、嚴要求。我小姨作為大兒媳,只能比婆婆更勤快、更努力,種地種菜、養豬養雞、洗衣做飯、養兒育女,她一手包攬。記得我年幼的時候看到小姨做飯,跑去幫倒忙,會被小姨習慣性教導:“揉面要三光,面光、手光、盆光,不光的話婆婆會罵的。”小姨如此聰慧、自律,即便這樣嚴厲苛刻的婆婆也挑不出啥刺兒來,更讓她獲得了“個子碎碎(小),人還挺麻利”的好評。
但被柴米油鹽淹沒的小姨,骨子里是不甘心的。小姨曾說自己婚后恰逢恢復高考,看見小叔子天天揣著書進來了,出去了,她心里有點兒不是滋味—自己要不是這么早結婚,也能考大學啊。
沒能參加高考的小姨有著比我媽這個大學生還深厚的愛書情結。記得兒時每到過年,我從位于山里的廠子回到老家,在親戚家暫住,被叫“小書蟲”的我最喜歡去小姨家,因為她家床底下藏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閑書”。我經常跟小姨擠在一張床上,深夜還開著燈看書,當看到一些滿是駭浪驚濤或令人心旌搖蕩的片段,我面紅耳赤,擔心被不知睡著沒有的小姨發現。但她從來都是裝作熟睡,任憑我看到天亮。
后來小姨家所在的城中村改造,不用種地了,小姨就開辦了一所幼兒園。年近不惑的小姨考取了幼教資格證,學習了幼兒心理學,小姨自豪地說,她的幼兒園的口碑在附近是最好的。她鉆研了很多教學方法,什么啟發教學法、情境教學法、活動操作法、暗示教學法,可是什么方法都頂不上一個字—愛。她愛帶孩子們唱歌、跳舞、做游戲,她也愛給孩子們做好吃的,幾乎所有從小姨幼兒園畢業的孩子上小學后,都會吵鬧著要回幼兒園找“蓮媽媽”。我印象里,那個階段的小姨是最精神煥發的,孩子們的天真爛漫深深地感染了她,他們天馬行空的想象也給了她很多啟發,讓她對人生有了無窮的憧憬和幻夢。
對此,我媽的解釋是,小姨青年困守家庭、中年創業,一直沒怎么出過遠門,不像她的兄弟姊妹們不停地在社會上流動,對外面的世界沒有執念。相形之下,我小姨就像安徒生童話《海的女兒》里最小的人魚公主,心懷對外面世界最強烈的向往,就連她的兒女們的名字里都有一個“海”字。這個叫“海”的種子在合適的時機就會發芽。
我們在吃漿水攪團的時候,鄰居老頭兒來串門,他讓姨父開著“三蹦子”拉他去買東西,被姨父拒絕:“五點不行,五點我要送蓮(小姨)跳廣場舞。”我姨父拒絕鄰居的時候,我小姨掩飾不住她的得意。看樣子,現在的姨父變乖了,和從前愛喝酒、打牌,不著家的姨父判若兩人。姨父如今天天想著法兒給小姨做飯,騎著三蹦子送小姨去縣城中心跳廣場舞。這個轉變,或許也有住在海島、遠離誘惑的影響,但不管咋樣,小姨覺得自己勝利了。這份勝利來之不易,這也是小姨在遙遠的海南買房的另一個不足為外人道的原因吧。
現階段小姨對自己的人生非常滿意,就像她的手機彩鈴唱的“讓我們紅塵做伴,活得瀟瀟灑灑,策馬奔騰,共享人世繁華……”如今,我小姨會極力向親戚們證明自己在海南買房的正確性:“讓你爸媽也過來!這里空氣多好,我們來了五年,一次感冒也沒有過!水管里的自來水,比礦泉水還甘甜新鮮!”
其實小姨不必自證什么,與很多患得患失的同齡人相比,與年輕時“不敢多走一步路,不敢多說一個字”的焦慮卑微的她相比,與中年時期負重前行的她相比,步入老年的她活出了真實的自我,實現了很多人生夢想,比如“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比如“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年少時的我一直以為小姨拿的是“田螺姑娘”的劇本,任勞任怨卻沒有回報,反而成了苦守寒窯的王寶釧。沒想到老年的小姨把自己過成了小龍女,帶著楊過,放下俗事,遠離江湖,奔赴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