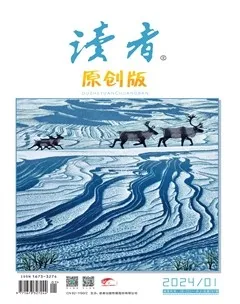2024,祝我們如愿以償
李帆
2023年10月中旬,作為顧問律師,我在街道的法律援助處值班,接待咨詢的群眾,遇到了一個讀研的小姑娘。事情并不復雜,她想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論文,有線上代理機構承諾提供文字潤色、與編輯溝通的服務。但將錢從微信上打過去后,對方立馬把她拉黑了。
我還沒來得及開口,她就接著說:“我錯了,不該輕信別人,給大家添麻煩,以后會注意。”態度誠懇得讓人心疼。
好吧,這種鬧心事我也遇到過,跟人溝通后非但沒有得到安慰,反而讓我反省“為什么偏偏欺負你”。
幫她分析案情,打錢過去的賬戶和當時溝通的人未必是同一個主體—可能對方事先做了籌劃。穩妥起見,決定以不當得利為案由起訴對方。最后,我還是沒忍住說道:“這不是你的錯,板子不該打到你身上。”嗯,時代就是這樣一點一滴進步的。
梳理材料時看了一下流水,總共40000多元,她分成十來筆轉過去,有零有整。看來,湊齊這個數,對她來說不容易。
11月底,在廣州見了位當事人,準確地說,是見了當事人和他的家屬,浩浩蕩蕩一大家子,從吉林趕來。當事人在船廠打工,修船時被機器夾了,我去看他的時候他還在重癥監護室昏迷著,一個腦袋兩個大,眼睛腫成一條縫,根本睜不開。后來,家屬回東北了。200多斤的大塊頭,生活起居全靠萍姐照料。
萍姐是個特別直爽的姐們兒,見我第一句話是:“我老公本來就不聰明,腦袋被夾后就更笨了。”
用工關系復雜,證據也不夠,不好定工傷,幾個老板都不愿意出醫藥費,互相推來推去。萍姐氣壞了:兒子讀高三,正是最關鍵的一年;還得瞞著公公婆婆,從家里出來一趟已經夠難了,結果這伙人愣是沒一個愿意承擔責任。
萍姐一罵,那些人更不想出錢了。怎么辦?打官司時間漫長,交醫療費迫在眉睫。我建議這東北一家人去街道辦事處尋求幫助。工作人員打了幾個電話后,之前怎么都喊不動的各方,乖乖坐在一張桌子前商量如何解決此事。工作人員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協調著湊了幾萬塊錢,畢竟治療不能停。
12月初,我去北京培訓,每天往返于賓館和教學樓。很幸運趕上了京城初雪,一夜之間,校園銀裝素裹,路上堆著大大小小的雪人。傍晚,有個女生過生日,她站在雪地里,和朋友一起給路過的陌生人送禮物,讓夜晚生出溫暖,用善意填滿寒冬。我拿了個小手工工藝品,并衷心祝福她順利畢業。
回賓館刷抖音,看到萍姐幾乎天天更新視頻。“老公的頭逐漸消腫了,能開口說話了,努力一把,還能翻身。”當然,還是需要她幫忙。忙碌如她,有心思更新視頻,說明老公病情好轉。
培訓結束返程,先落地廣州,去看萍姐和她老公。醫院門診部樓前面有個公園,綠樹香花,碧波蕩漾。經歷了北國的冰天雪地,讓嶺南的暖風一吹,心也化開了。這么好的天氣,勸萍姐多住一段時間,加速病人恢復。
萍姐的態度很堅決,等病情好轉,馬上把老公帶回老家。一是老家有人幫襯著照顧病人;二是小孩讀書吃緊,得回去盯著。還有就是一直沒敢跟老人說實話,只是含含糊糊說來廣州。但是,老人也會多想—后方傳來線報,二老一直懷疑兩口子受騙了。所以他們得趕緊回家,以正視聽。
“律師,就全委托你了,姐相信你。”說這話時,萍姐“大姐大范兒”十足。
之前看過身份證,萍姐比我小4歲。
接下來的事兒,主要集中在核對各種費用、和老板協商、走保險理賠,核定不了的費用就立案讓法院判定。老板出錢摳摳搜搜,還好,至少為她老公買了份意外保險。
再回到深圳,把讀研的那個小姑娘約出來。年底,她要去北大參加博士面試,臨走前想把自己的案子再梳理一遍。
就在我們一起看材料、一樣一樣核證據時,法官來電話了。是的,有時候就是這么巧,和電視上演的一樣。
手機按了免提,傳出來法官的聲音:“訴狀我看了,先打電話問問對方,要是他們也是受害者,我就移送公安機關;要是對方不能提供證據,就安排線上出庭。”
這番話如同定心丸,議題旋即變成訂哪天的機票最劃算。不出意外,她應該能心無旁騖地參加面試了。
年尾的兩件事,還停留在未完成的階段,卻都在向好的方向推進:和萍姐素昧平生,卻能取信于她,肩負重托,后續協調理賠,我一分錢都不敢算錯;以小姑娘的情況,申請不了法律援助,只能私下幫忙,好讓她不要因為上當就對生活充滿戒備,而我們本應該信任彼此。
“要是面試成功了,記得告訴我。”我在微信上留言。
希望我們都如愿以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