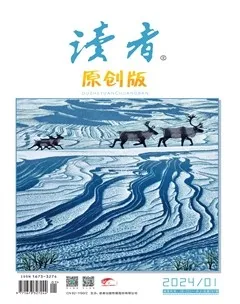再見了您哪
馬拓
1980年,北京南站還叫永定門火車站,和北京站中間由20路公交車相連,因為車上多是出差、看病、換乘的旅客,所以扒手橫行。這位老刑警那年剛滿20歲,單位就在北京站旁邊,經常在這路公交車上抓賊。
有一天,他在車上抓了一個毛賊,當場起獲20塊錢贓款。被偷的是位姑娘,模樣俏麗,穿一件鑲著荷葉領的束腰襯衫,下身是條特流行的闊腿牛仔褲。那會兒年輕人都愛趕時髦,他們這些抓賊的為了工作之便卻依舊土里土氣的。看見這么個漂亮的事主,他第一反應是有點兒自卑。
令他難堪的還在后頭,姑娘死活不承認錢是她丟的。
好說歹說去了派出所,他苦口婆心勸姑娘:“我眼瞅著他從你褲兜里掏出錢,你咋說不是你的呢?你不承認,賊處理不了不說,這錢也給不了你啊!”
過了一會兒姑娘才憂心忡忡地攤牌,說自己怕被報復,說她坐車都不敢穿裙子。他信誓旦旦地敲著桌子說:“看誰敢!我天天在這趟車上,你只要不怕凍腿,三九天穿裙子我都保你沒事!”
倆人聊開心了,嘻嘻哈哈地做了筆錄,晚上他送她回家。路上她跟他說,自己是商場賣布料的,他過年要扯布的話,可以給他留好料,起碼能湊出一件大氅呢。他嘴上說好好好,心里想的卻是—我沒病吧,穿著大氅去抓賊?
想著以后還能經常在車上碰見,倆人也就無牽無掛地告別了。他心里其實挺稀罕對方的,但人家是商場里的售貨員,豈是自己這成天灰頭土臉在車上鉆的“小捕快”可以攀上的?
但他又有點兒不甘心,想著來日方長,說不定多碰見幾次就對上眼兒了呢。
他只想對了一半。倆人的確能經常在20路公交車上碰見,但真沒機會套近乎。比如有一次,他和師父正在車上瞄著嫌疑人,冷不丁與坐在車窗邊的她目光相撞,驚喜升騰的瞬間便被理智澆滅,他抬起食指放在嘴邊,暗示自己在執行任務,先別打招呼。
姑娘賊機靈,好似受過訓練一般,立刻扭頭看窗外。

還有一次,姑娘剛花枝招展地擠上車,他在人影縫隙中使勁嘶氣、努嘴,示意她這邊有賊,趕緊往前頭走。姑娘挪走之后沒多久,他把賊按趴下了,好多人在給他鼓掌。他環顧四周,發現她早就下車了,頓時興致索然,薅起賊的衣領子匆匆退場。
最令他心動的是夏天那次。他跟著師父剛上車,就發現她站在前門的“大氣包”前,穿了一條藕荷色的豎褶長裙,裙擺隨著汽車行駛微微飄動。她在斑駁的車廂光影中好像下凡的仙女。他依然不敢過去打招呼,只是用低垂的手向她豎了個大拇指。
對方秒懂,莞爾一笑,又去看別處。
他下意識借著車玻璃打量起自己:剃得有些發禿的平頭,皺巴巴的的確良汗衫一側掖在褲腰里,一側支棱在胯骨外,怎么看也不是和仙女登對的人。
唉,悸動之后總會涌上一大波失落。
春去秋來,他從徒弟變成師父,永定門火車站也變成了北京南站。后來北京西站建成,地鐵也通了一條又一條,他帶著徒弟們滿北京城抓賊,20路公交車去得越來越少了。再后來他成了家有了娃,驀然間聽人提起這路公交車,才發現自己已經很多年沒有坐過了。
記憶的角落里,那車上有嬌羞的慌亂、耀眼的長裙、隱蔽的笑容,歲月的陽光順著車窗照在臉上,明亮滾燙,好像一班童話中的公交車。
前些年,他快退休了,去單位辦事。剛出胡同沒多久,他發現路邊有個和他歲數差不多大的女人一直盯著自己看。倆人互望了一眼,對方大步跨上前來,問道:“你早前是不是抓過賊?”
“哈哈,是你!”他的聲音沒變。
她燙著微微泛黃的卷花頭,臉上皺紋并不太多,耳朵上墜了兩個喜氣洋洋的金耳環,眼神里跳動著令他熟悉又陌生的光。
她說自己嫁人之后就搬走了,如今也兒孫滿堂了,前些天家里老太太去世了,這邊老房子有些事情需要料理,就過來得勤一些。今天看他從胡同里出來,那走路姿勢太熟悉了,還晃著肩含著胸呢,是怎么做到這些年一點兒沒變的。
“您記得夠清楚呀!”
他們在路邊匆匆而過的年輕旅人中笑嘻嘻逗話兒。
大媽說:“還記著那年過小年,你在20路公交車站下面啃江米條嗎?我一下車就看見你了,怕你又跟著賊呢,不敢上前去跟你打招呼,就想著這大冷天怎么吃得下去那個呀,拐彎就去買了個驢肉火燒,正想著怎么塞給你呢,到車站就看見你人消失啦。”

大爺放聲一笑,用煙酒嗓大聲抱怨:“嘿,那臭賊,害我那么好的東西都沒吃著!”
聊到差不多了,倆人拜別,各說一句:“再見了您哪!”隨后各自消失在風中。
老刑警講完,欲說還休地看著我。
他問道:“這有什么可寫的?啥也沒有發生。”
“不,我覺得很有意思。”
他輕輕搖頭:“其實那天在車站,我明明沒有跟著賊啊,怎么就走了呢?”
我一時不知該說什么。
窗外風聲沙沙作響,陽光照在他蒼老的面龐上,讓人感到時間的流逝。
他突然撲哧笑了:“嘿嘿,是有點兒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