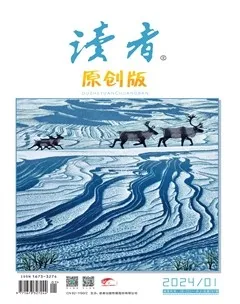尋找蘆葦
牛旭斌
重來祁村,正當立秋的黃昏。
一進祁村,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片蘆葦地。這是一個離我的村莊后村僅七八里地遠,同屬一座山系,只有七八百人的小山村。它與我的村莊背靠背,我們在大山之陽,祁村在大山之陰。
和所有村寨一樣,坡場相連的山腰山腳,樹林掩映的半路上,潺潺流淌的山泉清冽甘甜,供路人解渴,夏天還擺有蕎粉面皮攤。
那個年代,家家戶戶的屋檐下、場院里都堆放著成卷成卷的葦席、成捆成捆的葦稈。祁村盛產蘆葦,最出名的手工藝就是編葦席,就連打麥場上也擺放著幾輪石碾子,人們挈婦將雛,正忙著破篾子、碾篾條、編席子。
草本蘆葦,本是古代《詩經》里蒼蒼的“蒹葭”,屬于禾本科蘆葦屬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本應生于江河湖澤,但在成縣,蘆葦或生于池塘,或長在溝渠,或依于沿岸,或附于低洼草灘。

在山的角落,若不是汛期雨季,水是稀罕物。少年時期,頑皮的我們走遍溝溝岔岔,試圖尋找一條水流洶涌的像樣的河,但愿望最終落空,我們沒有找到一片能呈現蘆葦倒影的水澤。
祁村之所以有大片大片的濕地,又天然生長著茂盛的蘆葦,可能由于大量山林涵養的旺盛水源匯聚在這里,形成豐沛的地下水,從而滋養著叢生的蘆葦,水生根,根發根,蔓延生長。
對漫山遍野旱渴的黃土地而言,一壟壟蘆葦地,一片片郁郁蔥蔥的蘆葦林,宛如曠野上的一片片綠洲,棲息著麻雀、野雞、蟋蟀、螞蚱……萬物有靈且美。
蘆葦留給我們的生活記憶,除了用來編席織簾、做風箏,每年包粽子必備的粽葉也采自祁村到羽子川一帶的蘆葦,這是成縣最茂密的蘆葦蕩了。
芒種至夏至的十多天里,熙熙攘攘的小鎮集市上,集中大量收購這種葉舌肥寬、清香翠綠的蘆葦葉,連夜整車發往外地。
普通而野生的葦草全身是寶,這種于濕地中密密麻麻生長的草本植物,個頭高比玉米,花穗如絮,從春天萌芽抽節,到夏天葉茂成林,到秋天蘆花滿天,再到冬天葦稈收獲,一年四季都聚集著麻雀。
走訪席地而坐編曬席、編炕席的老手藝人,他們用木柴架火,煨上陶罐,煮著清茶,藍煙隨風飄散在場院里、屋檐下,裊裊升騰的煙火氣,吸引著成群結隊的城里人和攝影藝術家慕名前來游玩、觀賞和采風,絡繹不絕。
往日的生活,在歲月的推移和農事的消磨中,化身迷人的風景。
我們邊走邊看,搜腸刮肚又絞盡腦汁地回想著花草田禾的名字,一抬腳就走到了村西頭,一群叔嬸正坐在土地廟旁的樹林里納涼。
多少年來,不管生活怎么變遷,鄉親們農閑的聚會方式依舊,嘮家常的地方依舊,大家隨意坐在一塊石頭或一個土坎上,不用排序,無須站隊,誰想坐哪里就坐哪里,想說什么就說什么,不用深思熟慮,可以說哪一塊坡上的玉米先成熟,可以說誰家要拆瓦房蓋樓房,可以胡扯些八竿子打不著的話,可以談論著悲歡離合、陳芝麻爛谷子的往事,可以相約去趕酒席和大集,可以奔廟會去看戲,可以推著孫子的嬰兒車滿村游走,也可以端一碗飯串幾家門……
即使村里的人走了一茬又一茬,新媳婦迎進一門又一門,莊稼收種了一季又一季,茶余飯后大家自發集結的地方,還是這人來人往的村頭。他們從年幼時在這里玩耍,到年老后坐在這里消磨時光,即使牙掉了,耳聾了,身體縮了,飯量變小了,這些飽經風霜、本分寡言的篾匠的后代依然相聚于此。
我們回到這里時,叔嬸們的目光齊刷刷投向我們,充滿慈愛。我們永遠是蘆葦蕩里的一員,可隨著讀書求學,從幼苗長到茁壯后,又注定得離開這片鄉土。
山河入秋,蘆葉將在秋風中蒼黃。我剝開一株蘆葦,空心的蘆莖上敷著一層白色的薄膜,它可以當笛子和嗩吶的音膜。人間最美妙的樂聲,全靠這層蘆葦內壁的葭莩跟隨氣流振動。走在山村外,迎面吹來飄過蘆葦蕩的微風,我情不自禁踏入收割完小麥后泥土被耕耘翻熟的土地,綿綿的黃土淹過腳面,等待白露過后野菊花像燈帶開遍地坎的時候,種下來年的小麥。
放眼望去,野生的蘆葦蕩一望無垠。一座遠離村莊的瓦屋旁,一棵高大的老辣子樹上野藤纏繞樹干,樹葉在陽光下熠熠閃爍。
我拿出手機,對著無人的野徑,拍攝遠山群巒,拍攝羊腸山路上販蘆葦回村的收葦人,記錄烈日下在農田里耕作的農人—他戴著草帽,聽著秦腔,毫不停歇地揮舞著鋤頭,似乎全然不知自己已汗流浹背。面朝黃土背朝天的人,啥時候都不會對別人訴說他的疲憊。不向生活叫苦,就是他的體面。
我緩慢地走近坡腰的桔梗地,盛開的花兒在風中蕩漾成一片紫色的海。我輕撫過蒿草中的野棉花、眼睛草,摘下土坎上熟得通紅的覆盆子,然后對著一個個梯田塄坎上用蘆葦稈扎綁的稻草人深深致謝,把親親的黃土地和綠油油的山野,還有飛翔的鳥群與草叢中的蟲兒,全部裝進我離鄉后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心里。
徐徐山風輕輕吹過黃土地上的蘆葦蕩,沙沙的聲響似它們傾訴衷腸。在樹林里的土路上擔水的男孩已經挺起了脊梁,兩桶泉水被他穩穩挑在肩上,腳步穩當,夕陽從他的后背映照到臉龐。
黃昏將近,晚風呼喚著,已經明顯有了些許涼意,三伏天栽種的荏子已經換苗成活,感陰而鳴的蟬兒降低了聲調,嘶啞而經久地聒噪著,像在報訊,像在傳頌,像在慶祝,聲音回蕩在山村上空。
此時此刻,我想起帕斯卡的觀點:人是一根會思考的蘆葦,因為思考而通向無窮。他對人和蘆葦的哲學闡釋,正如故鄉人對命運的理解:山窮水盡的地方,只有人低頭彎腰耕耘,在泥土里打滾,生活才會更加熱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