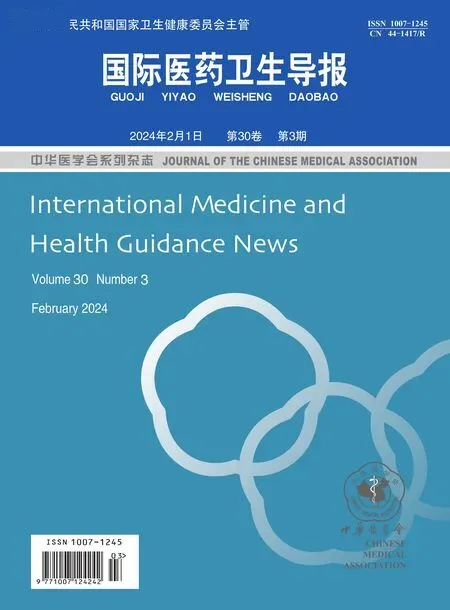可視化針刀輔助非甾體抗炎藥治療頸型頸椎病患者的應用研究
仵萌 劉春巖
南陽醫學高等專科學校第一附屬醫院仲景苑,南陽 473000
頸椎病為一種頸椎退行性病變引發的臨床綜合征,此類患者多伴有頸背疼痛、僵硬、四肢麻木或無力等典型癥狀,部分重癥者還可出現頭暈、視物模糊、心動過速及吞咽困難[1-2]。頸型頸椎病為頸椎病常見分型,也是各類頸椎病的最初階段,在此階段對患者實施積極治療能有效促進頸椎生理結構及功能恢復,對抑制病情進展并改善患者預后均有重要意義[3-4]。在其病情急性發作期,臨床多會通過應用非甾體抗炎藥對患者進行止痛治療,待其疼痛緩解后會輔以多種物理療法。手法推拿為治療頸型頸椎病的重要方法,能有效松弛頸部肌肉并緩解頸背疼痛。鄧文雯等[5]研究表明,單純實施手法推拿的效果或可受多方面主觀因素影響。針刀療法是中國古代九針及現代醫學外科相結合的閉合性松解術,能通過對局部組織進行松解、剝離而產生的止痛效果[6]。本研究分析可視化針刀輔助非甾體抗炎藥治療頸型頸椎病的效果及安全性。
資料與方法
1.一般資料
本研究為隨機對照試驗,選取2022 年1 月至12 月南陽醫學高等專科學校第一附屬醫院收治的106 例頸型頸椎病患者作為研究對象,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常規組(53 例)和針刀組(53 例)。常規組男30 例,女23 例;年齡25~45(35.44±5.17)歲;病程7~14(10.52±3.46)d。針刀組男31 例,女22 例;年 齡27~43(36.15±5.22)歲;病 程9~12(10.61±3.28)d。納入標準:⑴入組患者均診斷為頸椎病,且確認為頸型頸椎病[7];⑵病程≤14 d;⑶有頸部活動受限及局部壓痛;⑷頸部生理結構改變但未伴有間隙狹窄[8];⑸均知情同意且自愿參與研究。排除標準:⑴嚴重頸部外傷史;⑵頸椎結核、腫瘤病灶;⑶有骨質疏松等相關癥狀;⑷其他類型頸椎病;⑸伴有精神、認知障礙性疾病。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經南陽醫學高等專科學校第一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W2281)。
2.方法
2.1.常規組 予以手法推拿輔助非甾體抗炎藥治療。非甾體抗炎藥用藥方案如下:病情急性發作期予以口服塞來昔布膠囊[Pfizer Pharmaceuticals LLC(美國),國藥準字J20140072,規格200 mg],首次用藥劑量為400 mg/次,可按200 mg/次追加劑量;次日服藥劑量為200 mg/次,2次/d,連續用藥4周為1個療程。待疼痛緩解后實施手法推拿治療,具體如下:⑴在患者一側以單手扶住頭部,另一手沿頸部棘突、棘突旁、頸側、頸根用指關節依次滾動,每處滾動3 min左右。⑵在患者身后沿上述部位依次用拇指、食指、中指及環指指腹用力按揉,每處按揉3 min左右。⑶在患者身后用拇指、食指、中指及環指依次對頸部棘突、頸側、肩井等部位進行捏拿,每處捏拿3 min左右。⑷用食指、中指、環指指腹按壓頸部痛點,并對筋結處進行分筋,每處分筋3 min左右。⑸在患者身后以雙手食指、中指、環指分別壓雙側頸椎側方肌肉,以指腹用力進行從上向下滑動,連續滑動3 min左右。⑹以上手法推拿2次/周,4周為1個療程,本組連續治療3個療程后統一評估療效。
2.2.針刀組 采用可視化針刀輔助非甾體抗炎藥治療。非甾體抗炎藥用藥方案同常規組,待疼痛緩解后予以可視化針刀治療,具體如下:⑴囑患者取舒適體位,使頸部寰樞椎旁斜方肌、頸夾肌隆起處的天柱穴,耳后乳突下緣的完骨穴,第2、5、6、7頸椎棘突頂端,雙側背部肩胛內上角的肩井穴,以及肩前部肩鎖關節處的巨骨穴等充分暴露。⑵對上述部位進行常規消毒后,經西門子ACUSON X300PE 型超聲診斷儀(上海三崴醫療設備有限公司,藥械注進20143235112)引導下實施平面內入路穿刺,在9~14 MHz探頭上均勻涂抹耦合劑,選用規格為4號的Ⅰ型針刀(北京華夏針刀醫療器械廠,京械注準20212200660)經穿刺點依次刺入上述部位,刺入時針體應與超聲束保持平行;在超聲引導下將針刀逐步置入滑膜及肌纖維排列紊亂或增生肥厚處,以及骨面毛糙且不連續處分別進行縱向、橫向松解剝離,1次/周,4周為1個療程,本組連續治療3個療程后統一評估療效。
3.觀察指標
⑴于治療開始前24 h內及治療1周、2周、4周后分別采用視覺模擬評分法(VAS)[9]評估兩組患者的疼痛緩解情況,滿分10 分,7~10 分表示劇烈疼痛,4~6 分表示中度疼痛,1~3 分表示輕微疼痛或無痛。⑵于治療開始前24 h 內、治療結束后經西門子Multix Select 型數字化醫用X 射線攝影系統(德國SIEMENS AG,滬械注準20142300005)測量并對比兩組患者的頸椎前屈、后伸及左右旋轉活動度。⑶于治療開始前24 h 內、治療結束后分別測量并對比兩組患者的頸椎Cobb 角和頸椎曲度,并采用日本骨科協會評估治療分數(JOA)[10]評估兩組患者的頸椎功能恢復情況,滿分29分,分值越高提示頸椎功能越好。⑷于治療結束后統計并對比兩組患者治療相關并發癥發生情況。
4.統計學方法
數據均采用軟件SPSS 22.0 處理,計數資料以例(%)表示,用χ2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組內采用配對t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1.兩組患者VAS評分比較(表1)
表1 兩組頸型頸椎病患者治療前后VAS評分比較(分,± s)

表1 兩組頸型頸椎病患者治療前后VAS評分比較(分,± s)
注:常規組予以手法推拿輔助非甾體抗炎藥治療,針刀組采用可視化針刀輔助非甾體抗炎藥治療;VAS為視覺模擬評分法;與治療前比較,aP<0.05
治療4周后2.56±0.21a 3.07±0.46a 7.343<0.001組別針刀組常規組t值P值例數53 53治療前6.64±0.25 6.55±0.37 1.467 0.145治療1周后4.55±1.27a 5.65±2.08a 3.286<0.001治療2周后3.24±0.38a 4.41±1.09a 7.379<0.001
治療前,兩組患者VAS 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1周、2周、4周后,針刀組的VAS評分均低于常規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
2.兩組患者頸椎活動度比較(表2)
表2 兩組頸型頸椎病患者治療前后頸椎活動度比較(°,± s)

表2 兩組頸型頸椎病患者治療前后頸椎活動度比較(°,± s)
注:常規組予以手法推拿輔助非甾體抗炎藥治療,針刀組采用可視化針刀輔助非甾體抗炎藥治療;與治療前比較,aP<0.05
組別針刀組常規組t值P值例數53 53前屈后伸治療后45.22±10.36a 39.16±10.21a 3.046 0.003治療前50.45±5.17 50.32±5.22 0.129 0.898治療后62.41±10.27a 55.46±10.27a 3.484<0.001治療前48.44±5.27 48.36±5.31 0.078 0.938治療后60.45±10.24a 54.33±10.25a 3.075 0.003左右旋轉治療前33.49±5.25 33.25±5.37 0.233 0.817
治療前,兩組患者頸椎活動度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治療后,針刀組頸椎前屈、后伸、左右旋轉活動度均高于常規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
3.兩組患者頸椎生理結構及功能比較(表3)
表3 兩組頸型頸椎病患者治療前后頸椎生理結構及功能比較(± s)

表3 兩組頸型頸椎病患者治療前后頸椎生理結構及功能比較(± s)
注:常規組予以手法推拿輔助非甾體抗炎藥治療,針刀組采用可視化針刀輔助非甾體抗炎藥治療;JOA 為日本骨科協會評估治療分數;與治療前比較,aP<0.05
組別針刀組常規組t值P值例數53 53 Cobb角(°)治療前12.25±3.32 12.41±3.15 0.255 0.800治療后18.24±4.41a 15.45±4.36a 3.275<0.001頸椎曲度(°)治療前4.12±1.15 4.08±1.24 0.172 0.864治療后7.63±2.25a 6.42±2.07a 2.881 0.005 JOA評分(分)治療前15.44±3.28 15.35±3.16 0.144 0.886治療后23.36±5.41a 20.18±5.22a 3.080 0.003
治療前,兩組患者頸椎生理結構及功能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治療后,針刀組的頸椎Cobb角、頸椎曲度及JOA評分均高于常規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
4.兩組患者并發癥發生率比較(表4)

表4 兩組頸型頸椎病患者治療相關并發癥發生率比較
針刀組治療相關并發癥發生率與常規組比較[11.32%(6/53)比7.55%(4/53)],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832,P=0.362)。
討 論
頸椎病一般是因頸椎結構及機能衰退、肩頸慢性勞損、頸部肌肉突然遭受撞擊或頸椎受寒等原因導致,頸型頸椎病為其常見分型,也是其他分型頸椎病的初期階段[11]。頸型頸椎病患者臨床多伴有肩背部疼痛、頭暈頭痛及肢體麻木癥狀,其肩頸局部有明顯壓痛點,但部分患者經影像學檢查提示無明顯椎間隙狹窄或退行性病變。因此,暫時無需接受特殊治療[12]。任海濤等[13]研究表明,頸椎病的發生及病情進展與頸部周圍肌肉結構、功能異常密切相關,頸椎周圍肌肉條分布密集,若長期以不良姿勢工作、學習會導致肌肉出現慢性勞損。與其他分型頸椎病患者相比,頸型頸椎病病情相對較輕,但隨病情進展,患者亦可逐步出現頸椎生理結構改變及功能退化[14]。
中醫認為,此病屬“項痹”范疇,其發病機制考慮與經筋氣血失和及其所致頸部生物力學失衡等密切相關。在患者病情急性發作期,臨床常會應用塞來昔布等非甾體抗炎藥改善頸背疼痛癥狀,待其癥狀緩解后予以相應手法推拿能有效改善病變頸椎的血液循環并促進生理結構、功能恢復。但手法推拿的治療效果或可受施術者專業度及主觀性因素影響[15-16]。針刀療法是中國古代針灸及現代醫學外科的閉合性松解術,可通過將金屬制成的小針刀刺入病變深部進行松解后剝離粘連、增生肥厚或毛糙的病變組織,進而起到祛病止痛效果[17]。本研究結果顯示,針刀組治療1周、2周、4 周后的VAS 評分均低于常規組(均P<0.05),這提示針刀療法在緩解患者頸背疼痛方面更具臨床優勢。黃博威等[18]研究指出,針刀療法是古代九針及現代軟組織松解術有機結合的產物,在頸椎多處筋膜施針并切開多個小孔以緩解筋膜張力,緩解筋膜皮神經壓力后即可有效改善患者頸部疼痛癥狀。楊欽等[19]研究表示,頸內部力平衡失調為引發頸椎病的重要原因,針刀可通過松解、剝離變性軟組織而促進力平衡系統恢復,經分離骨肉粘連并松解肌肉后即可促使頸部血流動力學恢復,并改善局部微循環。當頸椎病患者相關癥狀消失后,其頸椎活動度及生理結構、功能均可得到相應改善。本研究中,針刀組治療后的頸椎活動度、Cobb角及頸椎曲度均高于常規組(均P<0.05)。徐科偉[20]研究指出,針刀療法能緩解頸椎病患者疼痛并促進頸椎肌力恢復,經小針刀治療頸型頸椎病后,觀察組的頸肌最大前屈、后伸、側屈等活動度較對照組更高,與本研究結果相似。傳統針刀療法是在非直視條件下對患者病變位置進行剝離、松解,這要求醫師需具備豐富的解剖知識和精湛的操作技術,而本研究采用超聲引導下的可視化針刀療法,與傳統針刀相比,此療法能實現對頸椎病患者的精準治療,對增強治療效果并降低因操作不當引發相關并發癥的風險均有重要意義[21]。手法推拿無需借助任何器械或藥物,即可實現對頸椎病患者的止痛治療,與針刀療法相比安全性更高。兩組治療后的相關并發癥發生率并無明顯差異,這提示可視化針刀療法亦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患者治療風險。
綜上所述,可視化針刀輔助非甾體抗炎藥治療頸型頸椎病能有效緩解患者頸部疼痛,對促進頸部活動度、生理結構及功能恢復均有積極意義,此療法安全性較高,值得進一步推廣。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仵萌:醞釀和設計試驗,采集、分析解釋數據,起草文章,統計分析;劉春巖:指導,支持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