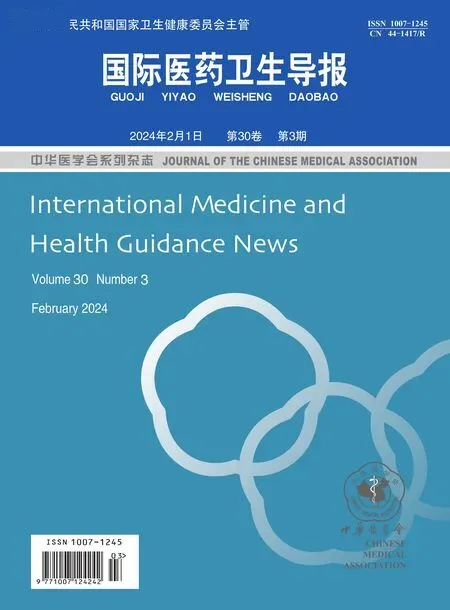初始樣本轉移技術在老年骨折患者血培養采血中的應用效果分析
劉允 邵長生 宋遠征 劉志 楊錫明
滕州市中心人民醫院創傷一科,滕州 277500
血液培養是用于檢測血流感染以指導后續抗菌治療的最可靠、最靈敏的工具之一。盡管血液培養技術取得了巨大進步,但血培養物的污染仍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在一些實驗室中至少有50%的陽性血培養物存在,血培養污染率通常在0.6%~6.0%之間[1]。由于老年患者經常訪問醫療機構,更多地暴露于某些生物膜形成菌株,并可能攜帶具有抗菌素耐藥基因的皮膚共生體,所以更容易發生血液污染。另外,在這些人群中,由于難以評估靜脈、抽血困難,可能會導致血培養污染。因此,來自60~80 歲年齡組老年患者的血培養物更容易受到污染[2]。除了人為錯誤之外,血培養污染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初始血樣中可能含有來自針頭的受污染的皮膚碎片[3]。雖然含乙醇的氯己定等可有效降低皮膚上生物膜生物的生存能力,但它并不能完全消除這些生物[4]。血培養污染會導致老年骨折患者使用不必要的抗生素或抗生素選擇不當,引起抗生素應用時間過長,不僅容易增加老年人臟器功能損害的風險、延誤患者的治療、延長住院時間,而且容易導致多重耐藥菌的感染,給基礎疾病多、機體免疫力差的老年骨折患者的康復帶來了負面影響,增加了治療費用。為降低老年骨折患者血培養的污染率,本研究采用初始樣本轉移技術采血管理方案,取得了良好的臨床效果。
資料與方法
1.研究對象
選擇2019年1月至2023年3月在滕州市中心人民醫院骨科住院的因疑似或確診血流感染而需要采集血培養標本的老年骨折患者400 例進行隨機對照試驗。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將患者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對照組204 例,其中男86 例,女118 例,年齡61~99(81.74±7.96)歲;骨折部位:上肢骨折72 例,下肢骨折90 例,脊柱骨折30 例,骨盆髖臼骨折12 例。觀察組196 例,其中男90 例,女106 例,年齡為60~94(80.36±8.23)歲;骨折部位:上肢骨折64 例,下肢骨折88例,脊柱骨折34例,骨盆髖臼骨折10例。
所有參與患者及其家屬對本研究均知情同意并簽署了知情同意書。本研究經滕州市中心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2019-倫理審查-01)。
2.方法
2.1.對照組 按照醫院抽血的標準流程執行。靜脈穿刺(僅外周靜脈部位)由采血團隊或訓練有素的護士進行,在操作過程中戴無菌手套。靜脈穿刺前,以穿刺點為中心,以向外的同心螺旋狀施加2%葡萄糖酸氯己定醇(主要成分:2%葡萄糖酸氯己定+70%乙醇)30 s并使其干燥30 s,消毒范圍直徑大于5 cm。在靜脈穿刺之前不重新觸診。除了系統的皮膚準備,還包括培養瓶頂部的消毒。
2.2.觀察組 在對照組標準操作流程的基礎上,采用初始樣本轉移技術(initial specimen diversion technique,ISDT)[5]。ISDT實施的步驟包括使用無菌手套、在靜脈穿刺前使用2%葡萄糖酸氯己定醇對血培養瓶的頂部、采血部位進行消毒以及使用蝶形針進行采血。采血管的頂部消毒后收集通過蝶形針抽取的初始少量血液(1.5~2.0 ml),然后丟棄該管。之后,使用同一根針頭采集血培養物。
2.3.血培養方法 從表現出敗血癥臨床癥狀或體征的患者中獲得兩組系列血培養物。使用的血培養瓶是厭氧血培養瓶和需氧血培養瓶(珠海迪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所需的最小血液量為3 ml,需氧和厭氧血培養的最佳體積均為8~10 ml。一旦血培養物被收集,使用密封的標本盒由運送中心人員在2 h內運送到實驗室,并放置在血培養儀器(Bactec 9240)上孵育最多5 d。
2.4.血培養污染的定義 血培養污染是指血培養陽性瓶中的分離菌為在血培養采集時進入瓶子中的外來菌而非患者血液中的病原菌。如果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之一,則血培養分離物被歸類為污染物:⑴常見的皮膚菌群,包括凝固酶陰性葡萄球菌(coagulase negative staphylococcus,CoNS)、棒狀桿菌屬、微球菌屬、芽孢桿菌屬或丙酸桿菌屬,從兩個或多個血培養樣本中的一個樣本中分離出來,而沒有從另一個可能感染的部位分離出相同的生物體;⑵在具有不相符的臨床特征、沒有歸因風險并且在沒有針對該生物體的特定治療的情況下改善的患者中分離出常見的皮膚菌群。如果同一天連續兩套血培養為CoNS,則在臨床微生物學實驗室做進一步種屬鑒定。考慮到在同一血培養中同時分離出真正的病原體和污染物的可能性,并為簡化分析,具有多種微生物血培養結果的患者被排除在該分析之外。如果這種生物體是從不同靜脈穿刺獲得的多種血培養物中分離出來的,那么培養物可以被重新歸類為真正的感染[6]。
3.主要觀察指標
比較兩組患者性別、年齡、骨折部位等一般資料。比較兩組患者血培養結果的真陽性例數(率)、血培養污染例數(率)。真陽性率=產生真正病原體的標本數/同期血培養總標本數×100%,血培養污染率=污染的血培養標本數/同期血培養總標本數×100%。對兩組患者血培養物的微生物學特征進行分析,觀察各菌株的占比情況。分析患者血培養污染的相關成本(靜脈注射萬古霉素的比率、3 d 內額外抽取一組血培養、平均住院時間)。
4.統計學指標
數據使用IBM SPSS Statistics 20.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1.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兩組性別、年齡、骨折部位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1。

表1 兩組因疑似或確診血流感染而需要采集血培養標本的老年骨折患者采血前一般資料比較
2.兩組血培養的真陽性率和污染率比較
觀察組和對照組血培養的真陽性例數(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249,P>0.05),提示采用初始樣本轉移技術前后,真正菌血癥的生物體數量沒有發現統計學上的顯著變化。觀察組污染例數(率)明顯少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7.209,P<0.05)。見表2。

表2 兩組因疑似或確診血流感染而需要采集血培養標本的老年骨折患者的血培養的真陽性率和污染率比較[例(%)]
3.兩組患者血培養物陽性的微生物學特征及各菌株的占比情況
兩組老年骨折患者污染血培養物中所分離的菌株中大部分為CoNS(8/11,72.73%):表皮葡萄球菌4 例、人葡萄球菌2 例、溶血葡萄球菌1 例、頭葡萄球菌1 例;其次為需氧革蘭陽性桿菌2 例(2/11,18.18%)和鏈球菌屬1 例(1/11,9.09%)。兩組老年骨折患者真正菌血癥最常見的原因是腸桿菌科種屬(30/44,68.18%),其次是金黃色葡萄球菌(7/44,15.91%)。
4.血培養陰性、血培養污染、真性菌血癥患者血培養污染相關成本
血培養污染患者比血培養陰性患者靜脈注射萬古霉素的比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接到第1次血培養結果后3 d 內兩組老年骨折患者額外抽取血培養物的總體比率為28.75%(115/400)。血培養物污染患者比血培養陰性患者額外抽取血培養物比率高39.87%,差異統計學意義(P<0.05)。血培養受污染患者的平均住院時間比血培養陰性患者長2.97 d(95%CI1.5~3.0 d)。見表3。

表3 血培養陰性、血培養污染、真性菌血癥患者血培養污染相關成本比較
討 論
血培養污染一直是令臨床醫生和微生物學家感到沮喪的根源。模棱兩可的培養結果會導致臨床診斷的不確定性,并且會因不必要的治療和檢測而增加醫療成本。本研究發現,血培養受污染患者的平均住院時間比血培養陰性患者長2.97 d;接到第1 次血培養結果后的3 d 內,血培養物污染患者比血培養陰性患者額外抽取血培養物比率高39.87%;血培養物污染患者靜脈注射萬古霉素的比率高于血培養陰性患者。根據在世界各地不同機構進行的獨立的第三方同行評審成本分析,受污染血培養的成本為每位患者3 000~4 000 美元,甚至更高[7]。Gander 等[8]觀察到,每次污染事件的額外費用甚至達到8 720 美元。增加的費用主要由于延長的住院時間、使用不必要的抗生素以及額外的血培養檢查等所致。Alahmadi 等[9]在一項隨機對照試驗中發現,血培養污染與5.4 個額外住院日相關,費用約為7 500 美元。Geisler BP 等[10]研究發現,與其匹配的真陰性患者相比,血培養假陽性患者平均住院時間延長2.35 d,最常見的醫院相關不良事件是譫妄(占所有不良事件的82%)。假陽性血培養會立即損害患者的生活質量,住院時間每延長1 d,感染相關疾病的概率就會增加1.4%[11]。在30%~40%的患者中,血培養污染與不必要的抗生素治療有關,抗生素費用增加近40%,患者最多有一半的時間接受抗生素治療,并且受到與抗生素使用相關的危害,例如毒性、不良反應、相互作用和耐藥性的出現[12];萬古霉素、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致急性腎損傷的發生率高達20%[13-14]。艱難梭菌感染通常與抗生素給藥有關(由于抗生素改變了腸道菌群),并且可能是致命的。接觸不必要的抗生素也與患者出院后90 d 內患敗血癥的風險增加有關[15]。因此,受污染的血培養造成的成本和患者傷害是巨大的,無論是對醫院還是對整個社會都是如此。為解決上述血培養污染成本問題,美國臨床微生物學會和臨床與實驗室標準研究所此前采用了3%的血培養污染目標,最近降至<1%[16]。
血培養污染被認為是由于皮膚上攜帶的細菌引起的。皮膚消毒不能完全防止皮膚菌群對血液培養物的污染;通過無菌手術技術采集的皮膚樣本發現多達20%的皮膚相關細菌在消毒后存活下來,這些皮膚細菌可能位于皮膚深層或消毒劑無法穿透的其他結構中[17]。皮膚微生物群落CoNS(例如表皮葡萄球菌和頭皮葡萄球菌)的生物膜形成能力可能有助于抵抗消毒劑的殺菌特性[18]。很多文獻報道了各種降低血培養污染率的策略,這些干預措施包括優化皮膚消毒、教育干預、培養瓶準備、單針與雙針使用、使用專門的采血團隊、靜脈切開術和使用無菌商業血培養采集套件等[19-20]。核酸擴增試驗理論上可以促進污染物識別并減輕血培養污染的負面影響[21]。但是,這些測試無法確定血培養中檢測到CoNS 是否代表真正的感染或污染。與其使用技術來評估血培養分離株的重要性,不如采用更合理的方法來預防血培養污染的發生。到目前為止,沒有一種干預措施被證明優于其他干預措施。ISDT是將含有未完全消毒皮膚碎片的前1.5~2.0 ml 血液去除,通過使用這種簡單的轉移方法,能夠降低血培養污染率,同時不會增加程序成本,是迄今為止降低與假陽性血培養相關的成本最有效的單一干預措施。盡管ISDT 并未廣泛用于預防血培養物污染,但它是血庫中的標準技術,使全血捐贈中的細菌污染減少了47%,并已在世界范圍內成功采用,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血液成分微生物污染的風險[22]。與標準方法相比,使用ISDT 不僅可以降低血培養污染事件發生概率,還可以減少萬古霉素的總體使用量[23]。Rupp 等[24]在急診室通過一組抽血師收集的血培養物證實,未使用ISDT 的血培養污染率為1.78%,使用ISDT后降至0.22%,降低了87.60%。Lalezari等[25]發現,與傳統的程序相比,ISDT 不會影響對真正血流感染的檢測,并且無需額外費用,可使患者住院天數減少1.1%。Wiener-Well 等[26]認為,ISDT 是一種易于實施的干預措施,并且有著成本低、培訓需求少等優點。本研究采用ISDT 采血方法預防血培養污染,使老年骨折患者的血培養污染率由4.90%減少到0.51%,而血培養的靈敏度沒有受到影響。采用ISDT 前后,真陽性培養率沒有顯著差異,這一結果與既往的研究相似。筆者沒有觀察到任何因使用ISDT而導致的不良后果,也沒有發現與血培養相關的針刺傷或潛在的血源性病原體暴露。
某些皮膚常駐微生物,如CoNS、微球菌、α-溶血性草綠色鏈球菌、痤瘡丙酸桿菌、棒狀桿菌屬和芽孢桿菌屬在早期研究中已被報道為可能的血培養污染物[27]。本研究通過分析老年骨折患者血培養物中菌株比例發現,CoNS 是最常見的血培養污染物,而真正菌血癥最常見的原因是腸桿菌科種屬。過去,從血培養物中分離出CoNS 通常被認為代表污染,占所有受污染血培養物的70%~80%[28],這與本研究結果相似。因為血流感染通常只包括一種生物體,所以醫生可能會錯誤地認為含有多種生物體的血培養已被污染。這些微生物如果由于誤認為污染物而未經治療,也會延誤患者的治療。有研究發現,當從血培養物中分離出CoNS 時,真正菌血癥的發生率在10.0%~26.4%之間[29],多種微生物菌血癥占所有真正菌血癥的6.0%~21.0%[30]。因此,血培養瓶中簡單存在幾種生物體并不一定意味著血培養污染。由于這些原因,建議進行多組血培養來檢查可能的血流感染。
總之,在不影響血培養真陽性的情況下,使用ISDT 可以顯著減少血培養污染,而且沒有相關成本。這種新穎的方法作為一種簡單、有效的措施,實用、安全,并且不會損害血培養的靈敏度,無需使用昂貴的設備。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劉允:撰寫論文、研究設計;邵長生、劉志、楊錫明:研究設計;宋遠征:研究設計、數據收集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