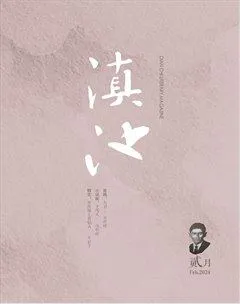永遠在醉中
當“我”對妻子插滿各式各樣的玻璃花瓶里的花開始感到厭倦,當一個永遠正確的人看起來像個傻子,當一個人從選擇喜歡做什么到選擇適合做什么,當這個世界不再需要畫家,當“他”發現自己并不是天才,當女歌手意識到自己只是“他”的模特,當“她終于明白,我不是她想象中的那個人,我是個怯懦的酒鬼”……當這一切開始的時候,當事物找不到它位置的時候,故事便發生了。那一刻就如同啤酒經過喉嚨,瀑布般跌落,落差在此時出現,微小而隱秘的景觀開始在體內形成,亦如那懸掛在高處的大衛走下神壇,“我”所期盼的神像終于沒有出現。故事里的人沒有出口也沒有退路,與理想和生活都愈加遙遠,前者無法抵達,后者無法安頓,這一個個無力對世界和他人做出回應的人,只有在醉中才能按住疼痛,而要想讓疼痛長久地消失,就只有永遠在醉中。
《大衛》:“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她”
“我”和同學畫家、“我”與妻子、畫家和女歌手是經由酒吧里“我”與畫家的對話延伸出的三對關系,彼此間對照、勾連起一幅現實圖景。畫家,一個在藝術世界里失意的人,一個既無法進入真正的藝術殿堂又不愿茍同偽藝術群體的充滿沮喪和怨念的人。與其說擊敗他的是這個盛產垃圾的世界,不如說是意識到自己同樣是個廢材的崩頹。曾經以為的成功,現在看來是如此失敗,失衡的自我認知使他迷失在人欲與天命之間,窘迫如同疾病一樣將生命推向死亡。他因此而自嘲、譏諷、陰陽怪氣,也因此而堅持、對抗、閉眼看世界。他醉著,也清醒著,矛盾又掙扎;而“我”,似乎早早就看透了真相,一個選擇了婚姻與現實的人,卻在日日忍受著生活的無聊,對全然世俗化的妻子的輕蔑與厭倦無從訴說。“我”無法回應畫家對藝術的追問,亦倔強地抗拒著與妻子的溝通,這種無望或許來自于曾經無數次的溝通失效,或者來自于無數遍的自話自說。“我”所有的回應都只是為了不把事情變得更加復雜,為了盡早結束掉對話。在某些時刻,不得不扔掉一些不該扔掉的重負,才能透出一口氣,就如同扔掉妻子叮囑“我”買的夜宵。這種故意的沖動是一種瞬間的、不顧后果的輕松,一種破罐子破摔的消解,然而它只能新一輪矛盾的開始,周而復始的爭吵省略在了不愿再給出篇幅的文字里。這里的“我”早早離開了藝術,同樣早早厭倦了生活。相比于畫家,“我”似乎是個更愿意進入生活的人,而面對妻子,“我”又是那個被生活推出的人,同樣進退皆無路,同樣是被卡住的人生。
女歌手,她沒有被提起,卻存在于今晚的對話里。因為只要擁有過,就會在身體的某一部分一直存在下去,就像那些看似已經關上的門,其實都是虛掩著,過往從門縫里游來蕩去。她曾經同樣是一個充滿怨念的人,她心動于畫家的獨具慧眼,失落于那份不得不承認的被情欲涌動的利用和情欲的消失殆盡;她痛恨他奪走了她的獨處,卻并未給與本應填補的陪伴。對于她清醒的困惑,“我”無言以對,只能說人如畫,畫如人,一個又一個,一張接一張,誰能夠畫出驚世之作,誰又能為一人永遠駐足,總有接續,總會被替代。
有人苦于找不到鑰匙而無家可歸,有人苦于鑰匙就在那里所以必須得打開那扇煩膩透頂的門;曾紋在身上的藝術之花被一場盛大的婚禮洗掉,而那些插在花瓶里的將永無休止地折磨生活里的人。
《另一個酒吧故事》:“我們的生活不是被彼此毀掉的,盡管我們正在努力摧毀對方”
起初以為是一篇由對話結構起的小說,實則是一個長篇獨白。“我”是一個無可救藥的酒鬼,“你”是沒有姓名的接替“我”的下一個;同時,“我”也是一個觀察者,觀察著“我”如何沉淪于酒精,觀察著“我”和“她”的關系如何走向崩壞,觀察著“她”如何瘋掉、如何走向“你”。而“你”同時也是看著“我”的滔滔獨白和以上所有一切的讀者,文字前的你以及你們。
我們常常困惑于人和人的關系是怎樣惡化的,困惑于到底是誰摧毀了我們的生活,困惑于神明是否真的存在,困惑于我們能得到救贖嗎,對于這一系列問題,作品呈現出一種觸目驚心的無力感。為了撫慰生活帶來的失望,為了寬恕內心的失落,“我”和“她”走到了一起,但就像布洛芬一樣,藥效很快就過了,意料之中的互相傷害接踵而至。“我”無法對抗那個虛空的、卻無處不在的敵人,看不見卻時時被壓制著,無法形容,無法命名,悲傷顯得矯情,痛苦又太過愚蠢。而對于“她”,終于在一次次的失望之后,袒露出了所有不幸,前生的、現世的,不可遏制的憤怒和詛咒傾盆而下,在砸碎了“我”用來對抗酒精的“琴”后,“我”終于把“琴”換成了“槍”。“她”那雙宛如“失火的冰窖”的眼睛和一邊抽搐一邊微笑的臉讓她明白那只癱瘓在沙發上的公羊,有著與野獸更為相近的牙齒。
諷刺的是“我”,那個作為觀察者的“我”,并不認為“我們”的生活是被彼此毀掉的,盡管“我們”正在努力摧毀對方。那么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將人變得如此不幸、如此不堪,我想,這是作品真正延伸出去的、真正觸碰到的一種冷酷的、無法推脫的真相:即摧毀我們的不是“彼此”,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我們自己選擇的人生。恰如“我”和“她”因動物本能而選擇的結合,反而“我”的失能、“她”的暴怒恰恰都源于起,源于“我們”曾經以為的救贖,但那只不過是陣痛藥,因為能夠救贖的是“超我”,而不是“本我”。又如“我”選擇的是酒吧,而不是廟堂,所以神像注定不會出現,“我”必然不會朝他走去;重要的不是這個世界上是否有神明,而是“我”是否愿意選擇相信它有。
“那雙眼睛里的東西更豐富了,比起憤怒和恐懼,它似乎顯得更深刻了。那里面充滿想象,充滿回憶,甚至包含著一切可以開向永恒的事物。”那永恒的事物是否只能是死亡?是否只有死亡才能接近永恒?這通體的絕望,透明、美麗,也無比殘酷。
這是令人驚喜的兩篇作品,具備了切近真相的努力和能力。它們表現的是人的無奈,更是人的選擇,無論主動的或被動的,無論深思熟慮的或未加審視的,在人算與天算之間,人做出的權衡與抵近的極限。
李彬彬 文學碩士,現為《廣西文學》編輯部編輯。
責任編輯???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