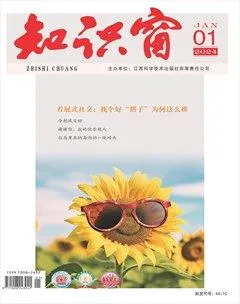每一粒米都有自己的靈魂
丁東
甲骨文中,“米”字是典型的象形字。《說文解字》曰:“米,果實也。象禾實之形。”意思是,米是谷物去殼后的籽實。《黃帝內(nèi)經(jīng)》有“稻米者完”之說。中國人見面,開口便是“吃了嗎”。可見,吃飯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在“民以食為天”的年代,米被人們賦予了神奇的力量。我們很難用一個詞、一句話來形容米在人類的演變史上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它一粒一粒地繁衍,一季一季地生長,一餐一餐地喂養(yǎng),書寫了人類歷史。歷史上,有很多次農(nóng)民起義都是為了奪取大米。
也正因為此,人們對稻米的描述是那樣唯美,對稻米的感情是那么深沉。《詩經(jīng)·七月》云:“八月剝棗,十月獲稻。”《詩經(jīng)·生民》又云:“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詩經(jīng)·白華》曰:“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左傳·哀公十三年》又曰:“食以稻粱為貴。”唐代詩人李紳行走鄉(xiāng)野,見農(nóng)民彎腰弓背,汗流浹背,辛勤勞作,寫下了膾炙人口的《憫農(nóng)》:“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南宋愛國詞人辛棄疾騎著高頭大馬,夜行在江西上饒縣的黃沙道上。當他越過溪橋,看見茅店村像鷓鴣鳥一樣安臥在稻花環(huán)抱的田野中央,脫口而出“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國外一個著名的哲學家認為,在所有的糧食中,大米是有靈魂的,其他都只能算是雜糧。確實,一粒大米,從種子出發(fā)到顆粒歸倉,經(jīng)歷了秧苗分蘗、幼穗發(fā)育、拔節(jié)孕穗、抽穗開花、灌漿結實等不同時期;經(jīng)歷了雨水、驚蟄、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等十三個節(jié)氣;經(jīng)歷了風、雨、雷、電,集天地之精氣,聚日月之精華,終于成為人們舌尖上的美食。誰說它沒有靈魂呢?
我對大米的深情,始于記事之日。我雖生在江南水鄉(xiāng),但因地少人多,收成不豐,在兒時的記憶中,很少能敞開肚子吃米飯。一家六口人每年四百斤不到的大米,母親精打細算著食用,平時以麥粞、大米混雜的麥粞米飯為主食。母親時不時地把沉積在麥粞下面的米飯挖出來,給生病的孩子或奶奶吃。僅在逢年過節(jié)、親戚登門時,我們才能吃上純米飯。那米飯不軟不硬、噴香爽口,溢著晶瑩的油光,裹著淡淡的甜味。不用配菜,我也可以吃上三大碗,可惜家里的糧食不夠我這樣吃,只能輔以土豆、山芋、南瓜等雜糧充饑。兒時,我最大的夢想就是家里能有一個大大的谷倉,里面堆滿稻谷,怎么吃也吃不完。
年歲漸長,我干過拔秧、插秧、除草、割稻、脫粒等農(nóng)活。在稻田的田埂上,在母親“回家吃飯”的吆喝聲中,我看見自己——一個少年的單薄身影,漸漸被夕陽的余暉吞沒。因而,知道每一粒大米背后的辛苦,尊重每一粒米,是人應有的態(tài)度。但凡見人糟踐糧食,我便感到心絞般疼痛。在我的影響下,全家老少都養(yǎng)成了良好的用餐習慣。
多少年來,米飯讓我歷盡生活艱辛,覽盡世事滄桑。每次見到米飯,我便會浮想聯(lián)翩,眼前呈現(xiàn)一片風吹稻浪的景象,繼而我悄然化身為一株站立的稻子,滿心歡喜,隨風搖曳。在我心底,米飯的香,是大地散發(fā)的恒久之香,是萬千生靈綻放的馥郁芬芳。
“水源流入土壤,沃野鋪滿金黃。”米呈現(xiàn)給我的,是珍珠般的皎潔、天使般的柔情、綺夢般的詩意,讓我忍不住伸出雙手捧著它,深情凝視,久久不放。很多時候,我是這樣理解的,一個熱愛大米的人,必然是一個感恩生活的人。換言之,一個沒有看見米生長的人,是沒有家園意識的。一個有家園意識的人,當再也看不見米的生長,他的內(nèi)心是恐慌的。
米是民生之本。人生在世,沒有比吃飯更幸福的事,也沒有比吃不下飯更痛苦的事。一個人對米飯的態(tài)度,就是對生活的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