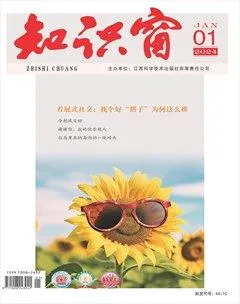“雨”水澆綠小鎮
仇士鵬
“雨”,是師姐的名,也是師姐的影。
師姐給我的印象,能和爽朗的晨光、清亮的鳥鳴相提并論。她很少生氣,像是一襲晚風,不會驚動殘照,又像是一枝柳葉,只會撩動細雨。她說話時,聲音輕柔,但又能從七嘴八舌間探出聲來,清晰可聞。她做事細致入微,總能從我的報告里發現紕漏,它們在我眼中偽裝得極好,卻在師姐一眼掃去時原形畢露。
那時,我還在新手期,粗心大意之下,常給師姐甩去一堆“黑鍋”。但即使報告被導師退回來大修大改,并附帶一通劈頭蓋臉的電話,師姐也只是給我發來消息:“師弟,快回辦公室。”不讓憤怒的情緒傳遞下去。
我常說:“師姐這場‘雨,真像《春夜喜雨》中的‘雨。”
她“隨風潛入夜”——只要遇到問題,隨時聯系她,總能得到回應。有時發完消息不到半分鐘,就會響起敲門聲,是師姐親自上門答疑來了。
她“潤物細無聲”——她會講很多遍項目該怎么做,從師兄去吃晚飯了講到師兄吃完回來,從肚子咕咕直叫講到肚子都餓得沒力氣叫了,直到我們聽懂。
后來,我們也成了干項目的老手,擁有一眼看出報告里比變色龍還能偽裝的紕漏的能力。“這都是我一手帶出來的。”聚會時,師姐臉上的光芒比燈還要明亮。
不過,或許是為我們兜底太多,她要參加每個項目,使得她分身乏術,自顧不暇。聽說師姐曾哭過一次,但我想象不出她落淚的樣子,是梨花帶雨,話不成句,還是匍匐桌前,無聲哽咽?那段時間,我不敢和她對視,畢竟若不是我們扛不起事,又怎么會讓師姐在國考前幾天,還在項目中帶頭沖鋒,而一考完筆試,就馬不停蹄地趕回來加班。
慶幸的是,師姐成功“上岸”。
畢業后,師姐回到故鄉,扎根在鄉鎮基層。她說,她要去澆綠那片土地,用她“知時節”的青春,用她“貴如油”的信念,讓堤上的柳樹成煙。
師姐曾談過她的志向:在故鄉的發展史上,她一定要寫下自己的名字,并且要寫得很重,很深。在那個小鎮,她找到了真正能實施抱負的地方。她參加關愛留守兒童閱讀志愿服務,用她的輕聲細語,把新征程的偉大成果一一講解給那些睜大了眼睛的孩子;她參與舉辦文藝惠民演出活動,一方簡陋的舞臺,上演著內容豐盛的文藝作品,把鄉村振興的精氣神凝聚在“花棉襖”與“大棉帽”的心中;她參與開展健康咨詢和義診志愿服務,講解甲流等季節傳染病的防治知識……
某張照片里,師姐穿著紅馬褂,拿著資料紙,站在一個老奶奶的身邊。老奶奶臉朝向她,微微低頭。我猜,奶奶的臉上一定露出慈祥的笑容。
我也曾看過那個小鎮的照片,低矮的小平房,泥黃色外墻的衛生院,草木叢生的野地,橫拉在半空的高壓線……它不就像是曾經處于新手期的我們嗎?它在等待發展,在等待人才,在等待幫助。它需要一場場大雨去澆灌赤裸的黃土地;它需要一枚枚腳印去喚醒沉睡的種子;它需要一場場清新的風吹走田間地頭積聚的悶空氣,把晨光和雞啼化作源源不絕的力量,灌輸進人的四肢百骸,讓凝而不散的炊煙把鄉村振興的理想送進每一個香甜的夢里。
這個小鎮必然能欣欣向榮!這是師姐曾經給我的信心,現在我把這份信心傳遞給這座小鎮。她曾怎樣澆綠我們,就將怎樣澆綠這個小鎮。
我期待著,小鎮逐步實現繁榮乃至繁華的那天——更多面朝黃土背朝天的人能坐在桌前享受日麗風和,更多在田野間撒丫子跑的孩子能一路跑進盛名在外的高等學府,更多學有所成的人們能帶著“寸草心”回到小鎮,去報得“三春暉”。由此,形成一個蒸蒸日上的良性循環。而在小鎮的發展史中,師姐的名字必然會出現在扉頁、版權頁及全文的字里行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