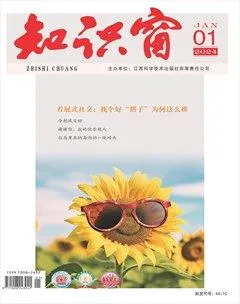總有些人不能忘
馬德
大學畢業十多年后,我重回母校。在學校的甬道上,一個女老師看到我,輕喚我的名字。對她的面孔,我感到有些陌生,但她淺淺笑著的樣子恍若在哪里見過。我猛地想起來,她是學校負責收發郵件的老師。我上大學時發表了一些文章,好多樣刊都是經她的手轉給我的。
女老師對我說:“我這里有你的稿費,苦于聯系不到你,一直給你保存著呢,今天可算看到你了。”隨后,她便把我領到學校操場旁邊的一間宿舍,從靠墻的柜子里取出一個布包,又在布包里翻出一個薄薄的紙包,鄭重地交給我,說:“你畢業后的稿費都在這里啦。”然后,她又看著我,臉上還是淺淺的笑容。
我連聲道謝。從學校回來,我打開紙包,紙包里是有零有整的幾十元錢。就在那張紙上,她還詳細地標注著哪筆錢是哪家報刊的,一清二楚。及至現在,我也不敢忘記這個女老師。不是因為她交給了我幾十元錢,而是她讓我相信,這個世界上真有這么一種人,像一輪明月,不論有沒有其他人在意,始終皎潔地照耀著塵世。
兒子小的時候,鬧肚子鬧了很長一段時間。一天黃昏,他哭得撕心裂肺,妻子急了,說:“咱們還是到市里的醫院看看吧。”可這么晚了,到哪里去找車呢。畢竟,那還是一個車輛比較稀缺的年代。
“沒事,我給你去找。”說話的是鄰居霍大哥。
當時,我剛搬到那里,所謂鄰居,也不過剛剛認識。隨后,霍大哥就找了一輛面包車。到了市里,已是晚上九點多,醫院里只剩下幾個值班的人。在簡單問過情況后,醫生就說:“住院吧。”隨后,醫生要我交住院押金。那時,我才第一次知道,住院需要交押金。到了交款的地方,收費人員說:“交2 000元。”啊!居然要交這么多,當時我只有200元,我說:“我沒帶那么多錢。”這時,一直跟在我身邊的霍大哥掏出1 000多元,說:“我這里有,先給你墊上。”后來,我還錢的時候才知道,那些錢是他給作坊工人發的工資,結果給我先行墊付了。那晚,霍大哥一直幫我辦完住院手續后才走。
若干年后,霍大哥的女兒在我任教的學校讀書,我竭盡所能地幫助她。霍大哥總覺得過意不去,我給他講過去的事,他總說:“那點兒事算什么。”他哪里知道,他的幫助在我心里足夠稱得上義薄云天。
在最后的日子里,父親已經病得形銷骨立。本家的幾個叔伯已經很長時間沒來家里看一眼,一來怕我們跟他們借錢,二來怕有什么事纏住他們。四姨對我母親說:“二姐,你照顧病人,我幫你干點家務活。”于是,她便從幾公里外的村莊來到我家,四姨成了那段艱難日子里唯一的“外人”,白天幫母親做飯,侍弄家畜,干地里的農活,晚上陪在母親身邊,成了母親深夜里最后的膽量。
很快,姨父便托人捎話過來,說家里養的幾十只羊管不過來。母親催促四姨回去,可是無論母親怎么勸,四姨就是不走,一直陪伴我家走過那段最難的、最苦的日子。
母親現在已經七十多歲了,依然不停地念叨四姨的恩情。母親說:“不要因為是親戚,這些事就可以忘了,有的親戚不如外人,而有的親戚,咱一輩子不能忘!”
其實,不用母親說,這些年人世的冷暖一直駐留在我心里,讓我對這個世界有著足夠清醒的認識。是的,在人生最艱難時候,還能守在你身邊的人,無論是誰,一定值得你終生托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