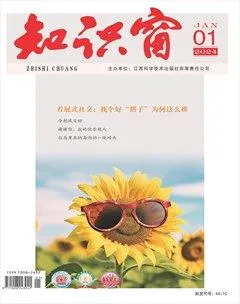文以載道,賀蘭當先
桂人慶
一
十二月忽而寒起,在沿海的江滬小城刮起真正意義上的西風。一夜側枕書卷,卻聽到來自賀蘭山的雪聲。
對賀蘭山的情緣,一時溯不清源頭,道不清來意。只記得萬千中國山水,或伶仃,或蒼勁,或雋秀,或綺麗,是美,美得大氣,卻還是少了點耐人尋味的韻致——張弛,卻又內柔外剛;極簡,卻又格調高雅。
直到我看到賀蘭山峰,那種韻致才找到最佳的載體。在寧夏的山峁,平坦的公路修得很寬,但在廣袤的天地間,它還不及一條細細的發帶。
四周空曠,除了天,便是地,除了風聲,依舊是風聲。這里沒有多余的色彩,筆筆皆是天意。我張開雙臂,仿佛在那一刻,擁抱了萬千山河、星宿滄海。
賀蘭山,美在山。它不是水墨畫里的寒山瘦水、巍峨青翠,而是覆著雪氣,點著藍彩,一點點由汪洋生長成陸地,由陸地挺拔成山石,最后連連綿綿長成的一群山。
正如一切偉大而美好的事物衍生時,時光都仿佛為之失語,唯有予之鐫刻下亙古永存的符號。
我一直篤信,中華的每一座山,都有一個年齡:青綠雋秀的江南山色如年方十八的少年,霧鎖巍峨的齊魯江山如三十而立的青年,橫貫蒼茫的喜馬拉雅山如古稀之年的老者,而遙遠西北帶著幼態之藍的賀蘭山脈則如初生的嬰孩,即山巒生命的起點。
把最純粹的藍毫無保留地潑灑,涂抹,再灑上糖霜般的雪粒,極致的美學往往不在于高貴疏離,而在于接近自然本源的天真親切。
純粹而干凈,幼態而滿腹天真,這也是中華文化誕生的最初姿態。誕生于齊魯的《詩經》的淳樸風貌里,冥冥之中竟隱著賀蘭山峰的影子,就如同中國文脈,一脈相承。
二
而賀蘭山山峰交匯處碰撞出的最絢爛的火花,當屬賀蘭山巖畫。
我第一次站立在這片神異的地方時,眼前是巨大的黃石塊挺立在天藍的背景下,而剎那間撲入眼簾的,是上萬年前留下的獨具特色的巖畫。
巖石飽經風霜,經過萬年的光陰,被尖銳的風劃開棱角,被歲月的雪水浸透出石礪,粗糙的臉上,每一道皺紋都揭示著過往。
在這般凹凸起伏的巖面上,有一道道非自然力量造成的溝壑——被尖銳的山石劃開的印跡。一條條線串聯成一個個圖形,一個個圖形又并聯成一幅幅龐大詭譎的畫面。嶙峋山間中,有約 6 000 幅巖畫,反映著先人狩獵、放牧、祭祀、征戰、娛舞的場景。
無論是神圣威嚴的太陽神巖畫,還是反映當時女性地位的女人花巖畫,當我佇立在它們面前,凝視著那些奇異的線條時,仿佛用萬年的時光匆匆走完那五尺的距離,用億萬星宿的輪轉穿梭進了古人類的內心,領略游牧民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況味。
其中,馬是巖畫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元素。據唐人記載,突厥語中的“馬”漢語音譯為“賀蘭”,突厥人將這座山命名為“馬”。頃刻間,眼前的巖畫便輪轉著千年前那個汗血寶馬奔騰在賀蘭山腳,豪放的先人飛馳著穿過蒼郁的樹木,挽弓射大雕的情景。
“歲月失語,惟石能言。”馮驥才先生為這些古老的符號題下這八個字。歲月流淌,卻緘口不言,唯獨那同樣寡言的石,用神秘的東方語言文化展示中華民族偉大的先祖的高深智慧,更浸透著那未知而又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中華文化的瑰麗一角。
巖石間,忽而蹦出三兩只可愛的生靈,是巖羊!這些可愛的小生命仿佛與生俱來的,與巖石峭壁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其毛色仿佛也在進化和演變中帶上了同巖畫一般神秘的色彩。
當地人把巖羊喚作賀蘭山的精靈。它們奔跑、跳躍,恍惚間,也成了巖畫的一部分,將生氣與靈氣注入巖畫,使巖畫煥發充滿生命力量的光彩。
賀蘭山的文化,還體現在那曲折滄桑的藝術長廊里展現的中華風貌與民族之氣,直至后來西夏王朝建都于這片土地的山腳,這種充滿智慧的文化也根植于土壤中。
三
走出賀蘭山,我行走在公路上,耳畔依舊是呼嘯的風,道路兩旁依舊是看不到邊際的原野。一股無名的力量用力將我推向這廣袤的賀蘭山群,推向自然的臂彎。
賀蘭山的山峰沐浴在暖陽下,那抹泛著藍意的雪色與陽光交相輝映,遠遠看去,正如一匹駿馬在偌大的天地間馳騁。
從那一刻起,我將身心投入一個更廣袤的天地,不再需要在現代文明的喧鬧燈火里修籬種菊,不強求“大隱隱于市”,而是以一種松弛感,吐納著純凈的空氣,讓心暢意地棲居,真正融入自然。
融入自然,是賀蘭山最后一味文化。不是單純的踏入,而是要在與天地、與萬物的交流中,汲取、吸收、回味和忘我,體會自然的廣博、無垠、茂盛和韌性。
于是乎,我情不自禁地邁開腳步,奔跑。真正意義上純粹的奔跑,狂奔,飛奔,義無反顧地往前沖,像匹脫韁的馬。
眼前的賀蘭山越來越高大,那條曲折的公路也望不盡、看不清。一種大汗淋漓而無拘無束的快感充盈著我的身心,賀蘭山混著雪水、巖畫、駿馬的空氣集滿我的胸腔,自然的純性、野性、真性注滿我的心靈。此刻,我的胸懷間仿佛擁有了整個宇宙。
自然,是賀蘭山最厚重的文化。身在其中,令我無拘無束地釋放真我,最大限度地擁抱自然,感受自然,最終融入自然。
賀蘭山的文化源遠流長,是發源之始的幼態純真,是發展壯大的民族之氣,更是由繁華轉入自然本源的返璞歸真。
在歲月的洪流中,我權且做一塊賀蘭山的巖石,向世人道一道賀蘭山這部無字史書里深沉而博大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