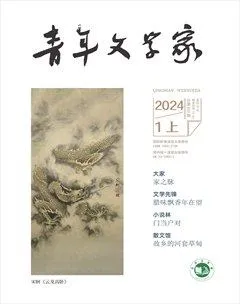炊煙
范智榮
“渡頭余落日,墟里上孤煙。”吟詠唐代詩人王維的佳句,眼前就會(huì)浮現(xiàn)出我少小時(shí)黃昏的炊煙在老家十字街上空彌漫回旋的鏡頭。那炊煙起處總有一縷是慈母的款款深情,分明是她輕輕揮臂在向我招著手……
古城西南,長者山似眉峰豎,玉帶溪如眼波橫,青山秀水,交相輝映,如詩如畫,給十字街平添了一種雄渾和瀟灑。每當(dāng)夕陽西下,放學(xué)后的我顧不上摘下書包就與小伙伴們在老街巷嬉戲打鬧,而面黃肌瘦的母親拖著疲憊的身軀從田間地頭回家,系上一塊綴滿補(bǔ)丁的圍裙,便開始了灶前的忙碌。她用一雙粗糙干癟的小手點(diǎn)燃灶火,再叉些柴草進(jìn)灶膛,隨著火苗噼噼啪啪歡快作響,她那張?jiān)镜狞S臉會(huì)被火光映得紅潤好看。那煙火在熏得她連聲咳嗽的同時(shí)翻卷著躥上高矗的煙囪,從房頂囪管口冒出一縷縷淡白的煙兒,隨風(fēng)升上空中,又追著落日飄散過去。
為節(jié)省大米,母親做晚餐老是用少量的米加大量青菜、蘿卜、土豆等煮成。我一放下碗筷,就得抓緊做作業(yè),一做完就去睡覺,以免饑腸轆轆了睡不著。次日早晨,有線廣播一響起,母親便輕手輕腳下床,生火做早餐。不久,那晨炊的香味兒就會(huì)撲鼻而來……
炊煙裊裊,炊煙起處有我家,只要母親還能讓自家的炊煙升起,我就不會(huì)餓著。年復(fù)一年,我沒有離開過十字街那個(gè)炊煙升起的地方,平日上學(xué)校,過年走親戚,都是在望得見炊煙的范圍內(nèi);日復(fù)一日,我在每日至少有三次升起炊煙的家里漸漸長大。十八歲那年秋天我去杭州上大學(xué),第一次遠(yuǎn)離了老家的炊煙……
如今,身居市區(qū)忙于俗務(wù),我已經(jīng)多年沒能在晨昏相伴炊煙,然而那失去了的炊煙卻時(shí)常飄于思緒之中;炊煙升起的美麗與溫馨在逝去了多少年之后,不僅沒有在心頭消退,反倒像陳年老酒的醇香飄溢在記憶的深處……
故鄉(xiāng)春夏的早晨總是霧氣蒙蒙,家家戶戶早上升起的炊煙與晨霧攪在一起,迷離難分地向著古城的四野飄去。待到秋高氣爽的時(shí)日,晨煙在澄凈的空中化作一種婀娜的身姿,遠(yuǎn)遠(yuǎn)望去,好像身披輕紗的玉女在晨風(fēng)中曼妙起舞……
十字街的夕煙又是另一種秀逸風(fēng)姿。黃昏時(shí)分,陽光即將告別輝煌而隱入夜幕,這意味著高潮就要結(jié)束,留戀與惆悵為那種熱烈注入了更多的情韻。在我看來,夕陽比朝陽似乎更絢麗多彩,它總是散發(fā)著金色的光芒,成熟中逸出華美,淺笑中充滿欣慰,它最終裸露著火紅赤誠的身心,意猶未盡地從西山輕緩滑落下去,那不是一天的結(jié)束,而是它一番激情燃燒、傾情奉獻(xiàn)后的暫時(shí)謝幕。有了夕陽的相襯,黃昏的炊煙那真是底氣十足、風(fēng)情萬種。特別是在稻、麥成熟的時(shí)節(jié),當(dāng)金色的夕陽涂抹著金波滾滾的麥浪、稻浪時(shí),從那翠竹綠樹掩映的粉墻黛瓦間升起一股股炊煙來,經(jīng)涼爽的微風(fēng)輕輕吹散,便裊裊地飄灑于滿目金色的氤氳中。夕陽下,踏上歸途的老牛因告別了勞作而心情變得輕松,它那難得的一聲歡叫,也宣告了故鄉(xiāng)農(nóng)人們一天辛勞的結(jié)束。于是,農(nóng)婦們趕快撥旺灶膛中的火苗,隨著鍋碗瓢盆的叮當(dāng)歌唱,農(nóng)家飯菜的清香猶如炊煙一樣飄散開來,催叫孩童歸家的聲聲呼喊也此起彼伏。漸漸地最后一抹陽光淡去了,炊煙也悄無聲息地融入了暮色中。夕陽與夕煙構(gòu)成的一幅金色雅圖,就這樣不著痕跡地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對于炊煙,我在過去晨昏相伴的那段時(shí)間其實(shí)沒有多少感覺,而在自己遠(yuǎn)離它之后倒有了新的感悟。人在喧囂中待得久了,難免思念田園的靜謐。煩躁之際,自然渴望輕靈的心境。這時(shí),讓那與晨昏同在的炊煙悄然飄升,無疑是最好的安慰。如果說當(dāng)年我對晨煙的欣賞僅止于曼妙和嬌美,那么長久以后的回味,更能感受它蕩滌心靈的那種安寧、祥和;如果說當(dāng)年我對夕煙的贊賞僅止于它的性感和綺麗,那么年近六旬的回眸,那夕煙分明是故鄉(xiāng)的標(biāo)志,是老家的呼喚!
多少年來我只要一吟詠《歸家》,腦海中就會(huì)飄升起老家的炊煙。我總在想,那炊煙就是無字的“家書”和無聲的“歸家”。
老家的炊煙默默無言地飄逝而去,卻有千言萬語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