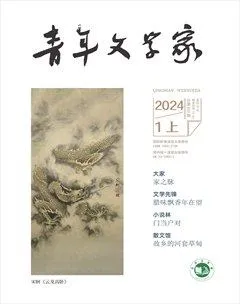單叔
王亞杰
小時候,單叔是我家的常客。
父親年輕時有幾個要好的朋友—李叔、單叔、劉叔。李叔是奶奶的親侄兒,在我家隨意來去;劉叔來到我家大多是向父親請教他在教學中遇到的問題,或者借書看;單叔來我家是和父親交流的,他們一起談天說地、喝酒忘憂,也一起讀書、回憶、下棋,度過農閑時光。
塞北農家的生活是單調的。尤其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漫長的嚴冬,屋外是一望無際的松嫩大平原,上面鋪滿了厚厚的白雪,村莊也掩藏在了大雪里面,想找一個參照物都很難。室內一燈如豆,昏黃的光暈下,幾個暗淡的人影坐在炕沿上、坐在凳子上,說著他們常說常新的話題。甚至單叔在我家坐的位置都是比較固定的,晚飯后別人先到的話也不搶他的位置坐。他常常坐在南炕炕梢兒,對著地上的一張桌子,桌子上放著一盞油燈,后來換成了蠟燭,再后來就安裝了電燈。一個暖水瓶,幾只水杯,有時候還有幾本書。父親坐在地上的板凳上,若再來其他的客人都會坐在北炕的炕沿兒上和大家說著話,聽父親講書,聽單叔講古,聽李叔說一些村子里當天發生的事情。后來有了收音機,他們就圍在一起聽評書《楊家將》《岳飛傳》等等。
單叔個子很矮,人又瘦,但是有著超于常人的精神頭兒和意志力。什么農活兒他都會做,上工的時候從不會落后,掙的工分總是最多的。而且他們家也是最會過日子的,用我祖母的話說就是又勤勞又節儉。在那個超過半數人家都有借債的村子里,單叔家是有余錢的。誰家要是有個急事兒,都會去找他借,多半也都會借到。秋收后還上,來年春天還會借。
單叔進門還沒坐穩就會掏出他的煙荷包開始卷煙,不一會兒,熟悉的煙圈裊裊升起,當他把卷煙從嘴上拿下來,掐在手里時就開始他的第一句話:“老哥,你說《七俠五義》里到底是南俠的武功高,還是北俠的武功高?”“要論武功,歐陽春(北俠)第一,展昭(南俠)第二。”父親喝了一口茉莉花茶,肯定地說。“鉆天鼠肯定排在徹地鼠之前。”單叔又說。父親點頭表示同意。《七俠五義》里的人都有武功嗎?那武功到底有多高呢?于是,我也偷偷地讀起來,磕磕絆絆地也沒看出來到底是誰的功夫更高些。而他倆常常談論的《紅樓夢》居然是一本殘了封面的繁體字的書,需要從上往下,從右往左讀,更是讓剛讀小學的我難明所以。
也許八九點鐘,也許十點鐘,燈油盡了,兩根蠟燭也要燃盡了,有時候天上的三星都出齊了,單叔慢慢地站起來,推門走人。父親也不留,也不用送,因為明天相同的時刻還會到。好像他們倆幾個世紀之前就約好了似的,約好了一起在荒涼的鄉村里共度寂寞的時光。
夏日連雨天出不了工,父親坐在窗前讀他從縣城里租來的書,單叔推門進來說:“這雨還沒完了,喝點兒吧。”父親抬起頭就看到單叔手里拎著一瓶酒,于是就囑咐母親去炒菜。小小的炕桌,放著燉豆角、黃瓜拌蔥絲兩個小菜,單叔和父親相對而坐,淺斟慢飲。“今年是一龍之水,看來這莊稼是錯不了的。”單叔說。“今年收麥子,都灌漿了。”父親回。他們的話不多,聲也不高,親切的氣氛溫暖著黃昏。我不明白他們為什么喝得那么慢,而窗前的大黃狗是理解他們的,它在籬笆下默默地注視著他們對飲,一動不動,眼睛里似懷著無限的柔情和感動。
每年過了臘月二十五,父親就開始忙了,他要給村里人寫對聯。而這個時候單叔是一定要過來幫忙的。單叔裁紙研墨,父親酌句揮毫,分工明確,效率極高。紅紅的紙,黑黑的墨,神奇的筆,一撇一捺,一鉤一提組成了多少充滿無限憧憬、無限幸福、無限期盼的句子啊,好像給那些樸素的節日換上了新裝,給未來的生活插上了翅膀,給鄉親們的日子帶來了希望。如今,單叔的小兒子去當兵并且轉了志愿兵,在部隊里總是給他寄錢,單叔說他沒有花錢的地方,就留著給兒子娶媳婦用。我和妹妹們也相繼離開了那個小村莊,只是會常回去看望。
七十一歲的單叔和七十六歲的父親還會時常見面,只是不怎么喝酒了,也很少看書了。他們倆常常坐在一起,有時候說些什么,有時候什么也不說,只是那神情更安詳了,一副世上萬物了然于胸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