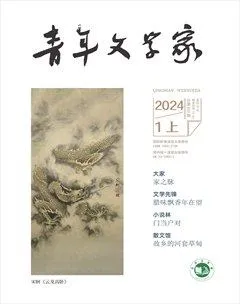訣別終究不舍
王宏興

“不去醫院,不點滴。”老人已然槁形衰損、病骨支離,可是,意念仍舊堅定、明晰。
在家主事一輩子了,老人的話從不曾遭遇忤逆,可這一次,怎么能聽他的?不聽他的,誰又能說服他呢?任憑六個女兒怎么說都不當用。老人枯槁的面容許久不動,一會兒,半睜半閉的眼里投出一絲微弱的光,落在盤坐床角的老伴兒身上,似乎在求取著最后一次支持。
六十七年的相濡以沫,老伴兒最懂他:“老頭兒呀,這次真的不想再拖累兒女了,他想早點兒走啊。”
連醫生都詫異,八十二歲的一把老身子骨兒上發現了肺癌,還能維持四個年頭兒,真是個奇跡。不過,這回恐怕是扛不住了,轉移到了全身多處器官,連氣管里都滿是病瘤。臥床半年多,近些天來已經說不出完整的話,只有老兒子能聽個明白。那哪兒是聽啊,多半是父子眼神互望,一個猜,猜對了,另一個就點頭回應。
在省直機關工作的兒子放下一切事務,專門請假回來陪伴著老父親。“如果你不點藥,那我就先走,我走你前面,到地下等你,你一到就看到我了……”
老人耳力好,心里更是明亮著呢,于是不解:兒子這是怎么了?從來沒有過的說話口吻,又強硬又動怒。
夫婦二人年輕時連要了六個女兒,不甘心,終于盼來了老兒子。人口多,老人想盡一切辦法才能讓孩子們活下命來。二姐還記得,老父親當時步行到幾十里外的安達市集鎮賣掉東西,換回一塊布,要不然自己那么大的姑娘家還沒有一身穿得出門的衣褲呢!
兒女們像小燕子,一個個陸續長成飛離了窩。隨著日子漸漸好起來,老人年歲也大了,身板也弱了,被兒子接進城生活了十五年,老人的心里滿滿的幸福。平時,愛喝一口小酒,聽老伴兒的話只在晚上喝一杯兒子炮制的人參酒,邊喝邊看電視,因為說不定啥時兒子就在新聞聯播里出現了。小區里幾個老人常常聚堆兒閑聊,老人就講兒子的種種好,上學時的、參加工作后的,新鮮的沒有多少,講過的隔三岔五再講。在聽者的嘖嘖稱贊中,一輩子謙虛務實的老人總是心生一份隱隱的驕傲,面露一絲飛著紅暈的自喜,就像一個考試打了滿分而受到表揚的孩童。
不過,當著兒子的面,老人卻少有贊語,常是板起面孔來,一遍遍囑告從縣里到市里、從市里到省里工作的兒子:不能貪,不能占,不能伸手。有著六十四年黨齡、當過二十三年村黨支部書記的老人,在兒孫面前儼然一位嚴厲的領導。成長的歲月,一路吹在耳邊的風,早已絲絲縷縷、悄無聲息地浸入了孩子們的心間。從過去的一個大家到現在的若干個小家,從兒女到孫輩,皆能自食其力、本分做事,皆平平安安,還有什么比這更讓老人欣慰的呢?
老人的心里沒有遺憾和牽掛。
老人一輩子剛毅,連死也不怕。他覺察出自己的身體不好,趁著還能言語,即向兒女作了交代—堅決不要躺在醫院,滿身插著管子呼嗒著一口氣。人啊,早晚得走,誰沒有這么一天呢?
生命之火將熄了,老人的心里明鏡似的。能在自己的家里閉眼,有老伴兒陪在身旁,有兒女們圍攏著,這是老人最大的心愿。
這會兒工夫,聽到兒子的厲聲嗔責,老人手指冰箱要來一小塊冰含在口里,潤了喉,攢了攢力氣。老人努力地抬動手臂,嘴巴一翕一合說著什么。說什么,只有兒子聽得懂。兒子俯下身來,老人枯瘦的、涼涼的手緊攥著兒子的手:“給你—當爹—沒當夠,下輩子—你還做—我的兒子啊!”一滴淚珠從老人的眼角滑過。
那一滴溫熱的淚,源從老父親干涸的眼窩,更流自兒子的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