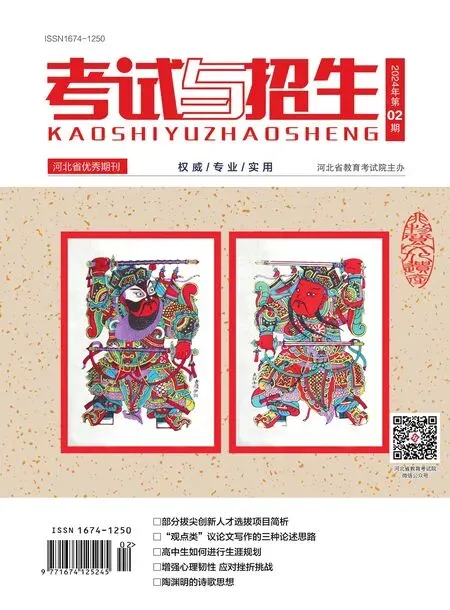魂牽夢繞高粱地
劉明禮
兒時的印記,在時光的長河中大多慢慢消逝;腦海中剩下的唯有那些最為深刻的回憶,猶如一塊塊烙痕深深地刻在心房。在不經意間,它們就會從塵封的記憶寶盒中浮現出來,悄然撥動心弦。家鄉的高粱地不知多少次出現在我的夢里。
我的家鄉地處遼闊的冀中平原,小白河曾從那里流過。我們村子的地勢普遍低洼,多是一些黏土地。雨水大的年份,地里的積水滲不下去,有些作物不太適宜生長。高粱這種莊稼,秸稈高大,且耐澇,所以種植高粱就成為首選。在我小的時候,家鄉人基本上是“靠天吃飯”。谷雨前后,隨著大地滾過第一聲春雷,天公祭下一場久違的春雨。趁著墑情,生產隊派社員給地施上底肥,細細犁過,耙蓋平整,耩下高粱種子。一周左右,地里開始冒出一株株幼苗,也生長出人們對生活的熱望。
春風吹拂,春雨滋潤,在人們翹首期待中,禾苗一天天長起。待高粱苗長到一拃來高,按照一尺左右一棵間好苗,再鋤地保墑。麥收過后,田野里便是一片青翠。寬大的高粱葉隨風揮舞,像輕揚著一條條翠綠的綢緞,泛起層層綠波。眼瞅著高粱長到齊腰,又竄過頭頂,孩子們的玩心也隨之蕩漾。及至炎夏,高粱地成為一片茂密的青紗帳!一望無際的綠淹沒了村莊,遠遠望去,只能看到一片突起的樹梢,像一艘墨綠色的艦艇,半沉半浮地游弋在碧海之中。

北方此時進入多雨的季節。一場又一場的雨使高粱地里的積水沒過了腳面。青蛙日夜不停地鼓噪起歌喉,產下的卵乳化成一群群蝌蚪,接著變為只有后肢的幼蛙。不知從哪冒出來的小魚、小蝦、小泥鰍、血簸箕、水蝎子,在高粱棵下浮游,蜻蜓、彩蝶、麻螂狗在高粱葉間翔飛駐足,你追我逐。驟雨初歇,孩子們從各自家中跑出來,相約奔向高粱地,支楞著耳朵靜聽高粱拔節,那“咔吧、咔吧……”的聲音,細微而清脆。在農家孩子的耳朵里,這聲音,傳遞的是豐收的希望,引起他們無盡的遐想。就在這拔節聲中,高粱悄悄地吐出了穗兒。
生長在平原的農村孩子,沒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可去,高粱地便成了最好的選擇。頂著炙人的太陽,三五個小伙伴相約來到青紗帳里。找一片水深的地方,用泥巴圍起一個堰子,用雙手淘干堰里的水,一條條小魚、小蝦、小泥鰍、小蝸牛之類的,便乖乖做了俘虜。裝進罐頭瓶里,帶回家找一個破盆破缸養起來,有的能活到過秋。有時候只顧了玩水,不小心就被螞蟥叮了。小伙伴們不慌不亂,用手在螞蟥身上輕輕拍打,不一會兒螞蟥就縮成一團,乖乖地從肉里退了出來。那會兒,貪玩的男孩有幾個沒被螞蟥蜇過?沒人把這當成多大的事。苦樂的年華,倒也帶給孩子們堅強、勇敢和別樣的智慧。
在高粱地里,我們學著電影里的樣子玩八路軍捉日本兵的游戲。當然都愿當八路軍,沒人想扮日本兵,于是便用猜“錘子、剪刀、布”的辦法,輸了的來扮演日本兵。“八路軍”用高粱葉編一個帽圈戴在頭上,“日本兵”則在臉上抹上爛泥,每人擗一根樹枝當槍。“八路軍”埋伏在青紗帳里,等“日本兵”打地頭經過,大喊一聲:“不許動,舉起手來!”“日本兵”撒腿要跑,“八路軍”舉著槍,嘴里發出“啪、啪、吧夠兒——”的槍聲,“日本兵”便一頭栽倒在高粱地旁……伴隨著高粱咔咔的拔節聲,孩子也一天一天快樂地成長。
高粱地不光是歡樂的舞臺,也是生活的希望所在。農諺云,“立秋三天遍地紅”。果不其然,秋風乍起,高粱便擎起了紅紅的火炬。立秋三日,寸草結穗。到了為豬羊準備過冬食物的時候,孩子們背起筐拿著刀到地里去割草。在苦澀的日子里,柴米油鹽的壓力,讓農家子弟更懂得承擔。其實,割草未必非要到高粱地,只是貪吃貪玩的孩子,更愿意選擇這里。因為高粱地里不光更容易逮到螞蚱、螳螂和蛐蛐,而且還有“烏膽”和“甜棒”。烏膽,就是高粱頭受了病菌的感染,穗子發育成了黑黑的東西;而甜棒,就是不結穗的“槍桿”。烏膽,有的長成煙圈型,有的如天女散花。這東西相當于高粱穗上長出的食用菌,可以吃,雖沒什么味道,卻能夠打打牙祭;而甜棒更不在話下,因它不結穗,營養全集中在了秸稈上,在家鄉人眼中無異于甘蔗。在那個饑饉的年代,這些東西對孩子的誘惑力可想而知。至于能割多少草,那就別提了,往往是最后擗一些高粱葉爛“葉”充數。
家鄉的高粱地,以她獨特的方式,塑造著農家子弟的童年。她為農家孩子清寂的童年,賦予多少色彩,書寫多少詩情,孕育多少夢想,留下多少眷戀!告別歡樂的童年,揮別成長的故土,也遠離了承載著歡樂童年的高粱地。然而故鄉那泥土的芬芳,那熟悉的高粱花子味道,連同那曾經的過去,卻時常縈繞在我的夢里。不論何時,不論何地,怎能忘記啊,我來自于那片火紅的高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