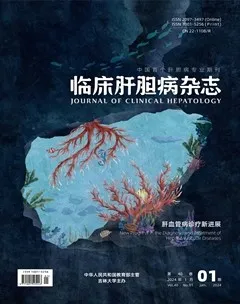肝竇阻塞綜合征的研究進展
張 明
南京大學醫學院附屬鼓樓醫院消化內科,南京 210008
肝竇阻塞綜合征(hepatic sinusoidal obstruction syndrome,HSOS),又稱肝小靜脈閉塞病(hepatic venular occlusive disease,HVOD),是由各種原因導致的肝血竇、肝小靜脈和小葉間靜脈內皮細胞水腫、壞死、脫落進而形成微血栓,引起肝內淤血、肝損傷和門靜脈高壓的一種肝臟血管性疾病[1-4]。HSOS 病因較多,但國內外明顯不同。歐美地區報道的HSOS 主要發生于骨髓造血干細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HSCT)清髓處理后和化療或免疫治療后的患者。國內報道的HSOS主要發生于服用含吡咯生物堿(pyrrolidine alkaloid,PA)植物,特別是土三七(或稱菊三七)的患者。不同病因導致的HSOS,臨床表現存在較大差異。常見的臨床表現為腹脹、肝區脹痛、腹水、黃疸、肝大等[2-4]。
1 HSOS的認識過程及命名演變
關于HSOS 的病例記錄最早見于1920 年,為1 例狗舌草中毒的南非患者。隨后在20 世紀50 年代,牙買加和印度報道多例類似患者,病因分析提示可能與食用狗舌草和灌木茶相關,病理研究發現患者存在肝內毛細血管阻塞,隨著疾病的進展最終發展為肝淤血、肝纖維化,當時該病被稱為“漿液性肝病”。1954 年,Bras 等[5]報道了5例因食用狗舌草而導致急性門靜脈高壓表現的類似病例,病理改變均為肝內小靜脈阻塞,遂將該病命名為“HVOD”,此后HVOD 的命名被學界廣泛接受。20 世紀50年代,多有報道接受肺部腫瘤放療和肝轉移性腫瘤放療的患者出現HVOD。1989—1990 年,多個研究團隊發現接受造血干細胞移植的患者術后出現致命性黃疸、腹水、肝損傷等并發癥,經病理研究證實為HVOD。此后的動物實驗和臨床病理研究發現,在肝靜脈閉塞性病變發生之前,即可出現肝血竇和中央靜脈的內皮損傷,表現為靜脈內皮下區域和Disse 間隙附近靜脈內皮剝落、紅細胞和非細胞碎片積聚,肝細胞的凝固性壞死也出現在肝血管內皮損傷之后。于是,有學者在2002年提出以“HSOS”代替原“HVOD”這一名稱,以便更好地解釋和強調肝竇內皮損害為該病始發因素,該命名目前已獲得廣泛認可[2-3]。
2004 年,針對結腸癌肝轉移手術標本的研究[6]發現,奧沙利鉑化療后的肝組織存在較為明顯的肝血竇阻塞。此后,這一現象被證實在奧沙利鉑化療后的患者中廣泛存在[7]。除前文所述發病因素,ABO 錯配血小板輸注、淀粉樣變性等疾病及嬰幼兒免疫缺陷也可導致HSOS 的發生;與HSCT 化療相關的HSOS 被稱為HSCTHSOS,與PA 相關的HSOS 被稱為PA-HSOS,與奧沙利鉑等化療相關的HSOS目前尚未被專門命名。
2 HSOS的病因和發病機制
導致HSOS的病因不同,則發病機制也不同,具體機制也未完全闡明。總體而言,HSOS 的發病機制可概括為:肝血竇和中央靜脈內皮細胞的中毒性損傷,以及肝血竇和中央靜脈內皮細胞的修復過程受阻[1-4,8-9]。具體過程可能是損傷因素引起肝竇上皮細胞水腫,細胞間隙擴張,細胞間緊密連接喪失,通透性增加,紅細胞和脫落的肝竇壁內皮細胞滲入Disse 間隙,使肝竇擴張、破裂。同時,受損的內皮細胞釋放血管性血友病因子和纖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劑-1,前者可促進血栓細胞聚集和凝塊形成,而后者可抑制纖維蛋白裂解。這些高凝狀態共同導致肝竇和小靜脈形成微血栓,并導致竇后梗阻。同時,肝竇周圍間隙和門靜脈區炎癥細胞浸潤增加,進而加重肝臟充血和炎癥損傷,導致肝竇周圍間隙的肝星狀細胞活化。活化后的肝星狀細胞合成大量膠原纖維,導致竇狀纖維化加重和小葉中央靜脈血栓形成,反之又導致肝竇流出道阻塞和肝內竇性門靜脈高壓。如果未能及時干預,最終可能發展為肝纖維化和肝硬化。
PA 作為一大類毒性生物堿,是自然界存在最廣泛的植物防御性毒素。目前已知自然界中含PA 的植物超過6 000 種,廣泛分布于世界各地。PA 對肝、肺、腎等均有毒性,但不同分子結構的PA 具有一定的器官特異性,此外還具有遺傳毒性和致癌作用。既往有報道孕期女性服用含PA的中草藥導致新生兒早產并患PA-HSOS的病例。《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收錄的多種中草藥中均含有PA 成分,如茵陳、佩蘭、野馬追、一點紅、返魂草、款冬花、紫草、番瀉葉、飛揚草、地錦草、苦玄參、半枝蓮等。藥典未收錄但民間使用的品種,如菊三七(五加科三七即參三七中不含PA)、白頭婆、洋甘菊、牛至等也含有PA。部分已上市的成方制劑中也含有PA,如乙肝寧顆粒、小兒肝炎顆粒、紅花片、小兒肺咳顆粒、清肺化痰丸、止咳寶片、外傷如意膏、腸炎寧片、萬通炎康片等[10]。PA的毒性主要來自其在肝臟中形成的脫氫代謝產物——脫氫吡咯,該物質是一種具有活性的烷基化試劑,具有很強的親電性,與組織中親核性的蛋白質、核酸或酶結合可導致肝竇內皮細胞谷胱甘肽耗竭,引起內皮細胞死亡。此外,基質金屬蛋白酶、NO、凝血途徑多種酶異常等也參與PA-HSOS的發生、發展[3-4,10]。
在HSCT過程中往往同時應用多種可能損傷肝臟的藥物,因此,很難確定具體哪一種藥物導致了HSOS。目前已見報道可導致HSOS 的藥物包括:6-巰基嘌呤、6-硫鳥嘌呤、放線菌素D、硫唑嘌呤、白消安、阿糖胞苷、環磷酰胺、達卡巴、卡莫司汀、達卡巴嗪、絲裂霉素、氨基甲酸乙酯、特比萘芬、吉姆圖珠單抗、美法侖、烏拉坦等[9-10]。HSCT-HSOS 的發病率為10%~60%,對該病的認識及診斷標準不一致導致發病率數據的巨大差異。總體而言,最近20年HSCT-HSOS 的發病率逐漸下降。兒童發病率是成人的2 倍。20 世紀80 年代,HSCT-HSOS 在同種異體移植中的發病率為21%~24%,在自體移植中的發病率約為5%。隨著新型誘導化療藥物的出現以及用藥劑量的降低,目前HSCT-HSOS 發病率已顯著降低,但并未消除[11-12]。我國很少有關于HSCT-HSOS 的報道,其原因可能并非實際發病率低,而是臨床對該病的認識不足。HSCT-HSOS 相關的危險因素包括:基礎肝病病史、HSOS 病史、腹部照射史、巨細胞病毒感染、吉姆圖珠單抗治療、2 歲前嬰兒第2 次移植、家族淋巴組織細胞增多癥、巨噬細胞激活綜合征、骨硬化病、白質營養不良、高齡、代謝綜合征、地中海貧血、一些基因(GSTM1多態性、C282Y 等位基因、MTHFR 677CC/1298CC 單倍型)突變、肝硬化、病毒性肝炎、鐵過載等[9-13]。
奧沙利鉑導致的HSOS 相關門靜脈高壓,可出現在化療結束后多年,也可在短期內出現。肝切除的手術標本或肝穿刺活檢標本顯示,這類患者的HSOS 發病率高達79%,不接受奧沙利鉑化療,而接受其他類型化療藥物的同種類型腫瘤患者,HSOS 的發病率僅為23%[6]。這類患者出現食管靜脈曲張的比例僅為5.7%,而血小板降低、脾增大的比例遠遠高于靜脈曲張,表明雖然肝血竇阻塞普遍存在,但引起嚴重有臨床意義門靜脈高壓的比例并不高[6-7,14-15]。鉑類化療藥導致的HSOS 通常呈現特異的“藍肝”,可能與肝臟膠原纖維沉積有關,也可能與肝臟淤血有關[6-7,16]。奧沙利鉑相關HSOS 的危險因素包括:GGT 升高、高齡、女性、肝儲備功能減弱、化療周期數、化療結束與消化系統手術間時間間隔過短。AST/PLT 比值指數、PLT、透明質酸水平以及脾容積大小對預測鉑類化療藥誘導的HSOS是否發生及嚴重程度具有一定價值。編碼跨膜藥物轉運體的ATP7B 基因的多態性與奧沙利鉑化療誘導患者HSOS的易感性有關。
3 HSOS的臨床表現
PA-HSOS 和HSCT-HSOS 患者的臨床表現相差不大,主要包括黃疸、肝大或者肝區脹痛、腹水、體質量增加、納差等。二者均為在暴露HSCT 或PA 后的一定時間內(多數為30 天)發病。體格檢查可見不同程度的皮膚鞏膜黃染、肝區叩擊痛、移動性濁音陽性,部分患者可合并胸水和下肢水腫。少部分重癥患者或并發門靜脈血栓時,可導致肝功能惡化,血清膽紅素在短時間內迅速升高[3-4]。慢性PA-HSOS 患者缺少典型表現,或僅表現為頑固性腹水和門靜脈高壓相關并發癥。腹水性質符合典型的門靜脈高壓性腹水表現,血清腹水白蛋白梯度>11 g/L。HSCT-HSOS 患者若出現以下情況通常提示病情較重:移植后快速進展為HSOS;肝功能迅速惡化,膽紅素水平24 h 內翻倍;多器官功能衰竭[9]。黃疸指數升高至15 mg/dL 或者體質量增加超過10 kg 的患者病死率高達90%以上,其死亡原因不一定為肝功能衰竭,可能為膿毒血癥、肺部感染、消化道出血及多臟器功能衰竭[8-9,11]。
化療藥物或免疫抑制劑所致的慢性HSOS可無典型臨床表現。奧沙利鉑化療相關的HSOS是一個相對慢性的過程,從肝竇擴張、出血到門靜脈高壓形成,通常持續數月,顯著升高的肝酶不明顯,伴隨肝結節再生性增生,逐漸出現脾大和血小板減少,可不伴有腹水、黃疸和肝大。因其臨床表現相對隱蔽,往往被漏診。脾體積增大可作為一個相對簡單判斷奧沙利鉑化療后出現HSOS的臨床指標[6-7,15]。
4 HSOS的診斷與鑒別診斷
不同病因導致的HSOS 診斷標準并不一致,最早被提出的是HSCT-HSOS 診斷標準。該診斷標準依次有1984 年西雅圖標準、1993 年改良西雅圖標準、2009 年巴爾的摩標準以及2016 年歐洲骨髓移植協作組標準。前3 個診斷標準均要求在HSCT 后的一定時間內(通常<30天),出現黃疸、肝大或者肝區脹痛、腹水、體質量增加等數個指標中的2個或多個[9,11-12,17]。然而,部分患者的HSOS 可發生在移植的30 天之后。因此,2016 年歐洲骨髓移植協作組診斷標準將HSCT-HSOS 進一步分為早發HSOS 和遲發HSOS。早發HSCT-HSOS 的診斷標準:在HSCT 的21天內,出現膽紅素升高>2 mg/dL(34 μmol/L),且同時具備以下3項中的2項:痛性肝腫大、腹水、體質量增加>5%;遲發HSCT-HSOS 的診斷標準:在HSCT 的21 天后,出現經典的HSCT-HSOS 相關臨床表現,或有HSOS的組織病理學,且同時具有以下5項中至少2項:膽紅素升高>2 mg/dL(34 μmol/L)、痛性肝腫大、腹水、體質量增加>5%、血流動力學和/或超聲的HSOS 證據。上述診斷標準均未包含影像學資料,也不強調病理學檢查[12,19]。歐洲開展的多中心調查將HSCT-HSOS 分為輕度(自限性,無需治療)、中度(需治療,可完全緩解)和重度(導致死亡或在100 天內未緩解),其發生率分別為8%、64%和28%,病死率分別為1%、18%和67%。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多個診斷標準中明確提出HSOS 的診斷需要可見黃疸不同程度地升高,但有報道30%的兒童HSCT-HSOS 患者無黃疸,15%的成年HSCT-HSOS 患者無黃疸。因此,根據巴爾的摩和成人EBMT 標準,部分患者將可能被漏診[12,19-20]。
肝靜脈壓力梯度(hepatic venous pressure gradient,HVPG)測定和經頸靜脈肝活檢是HSCT-HSOS 特異性診斷工具,這類患者HVPG 通常升高,活檢可明確HSOS,還可鑒別移植物抗宿主病。但由于HSCT-HSOS 患者基礎狀態通常不佳,上述檢查手段較難實施。瞬時彈性成像對早期發現HSCT-HSOS可能有益[20]。肝臟超聲多普勒可發現肝脾腫大、腹水、附臍靜脈開放、膽囊壁增厚、肝動脈阻力指數改變、肝靜脈血流頻譜、門靜脈血流減慢或反向等提示門靜脈高壓癥的信息,上述信息無法用于診斷HSOS,但可協助鑒別診斷,如發現右心衰導致的肝靜脈增粗。需要注意的是,肝臟超聲正常并不能排除HSCT-HSOS。HSCT-HSOS 患者受累于基礎疾病,腎功能往往較差,不建議常規行增強CT檢查。需要與HSCTHSOS 鑒別的疾病包括:移植物抗宿主病、靜脈流出道梗阻(如Budd-Chiari 綜合征和充血性心力衰竭)、藥物反應、病毒性肝炎、真菌感染和敗血癥等。有學者提出將內皮損傷的生物標志物用于預測HSCT-HSOS,包括移植前和移植后循環血管性血液病因子、血栓調節素、e-選擇素和可溶性細胞間黏附分子-1、移植后血清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升高也與HSOS 的發生有關。對于HSCT-HSOS患者,一般不要求病理診斷[19-21]。
PA-HSOS 主要見于有服用中草藥習慣的國家和地區。2017 年,我國學者制定的PA-HSOS 診斷標準(南京標準)[3],要求有明確的服用含PA 植物史,且符合以下3 項:(1)腹脹和/或肝區疼痛、肝大和腹水;(2)TBil 升高或其他肝功能異常;(3)典型的增強CT 或MRI 表現,同時排除其他已知病因所致的肝損傷。不符合上述3項臨床表現但病理診斷支持也可確診PA-HSOS。PA-HSOS的典型超聲及CT 表現主要為肝臟彌漫性腫大、肝實質密度及回聲不均勻、腹腔積液、門靜脈脾靜脈內徑正常血流速度緩慢、下腔靜脈受壓變細、門靜脈周圍存在水腫帶等[3-4]。PA-HSOS 主要與急性肝靜脈型布加綜合征相鑒別,后者在超聲檢查時可見下腔靜脈近心端和/或肝靜脈有狹窄或閉塞,伴有尾狀葉腫大、肝靜脈間交通支形成、第三肝門開放等特征性表現。二者難以鑒別時,可通過下腔靜脈/肝靜脈造影和HVPG 測定進一步明確診斷[3-4,23]。
奧沙利鉑化療導致的HSOS,臨床表現無特異性且輕微,甚至無臨床癥狀,可僅表現為實驗室檢查指標輕微改變。目前,關于奧沙利鉑化療導致的HSOS 大多通過病理檢查確診,尚無臨床診斷標準。因此,這類HSOS的診斷標準不能參照HSCT-HSOS 和PA-HSOS。對于既往接受過鉑類化療藥,且臨床出現脾大、PLT 水平下降、腹水、肝損傷的患者,需高度警惕發生HSOS的可能。奧沙利鉑還可誘導肝臟出現局灶性HSOS,表現為乏血管腫瘤的表現,同時局灶性結節性增生的比例顯著增加,需要與肝臟轉移瘤相鑒別。2021年,我國對奧沙利鉑說明書作出修改,明確提出要重視奧沙利鉑導致HSOS 的監測。PLT 減少和脾體積增大被認為與HSOS 的發生呈正相關[7]。貝伐單抗及其他血管內皮生長因子抑制劑被認為可減少奧沙利鉑導致的HSOS的發生風險。一旦發生HSOS,患者接受肝切除的手術風險、術中輸血量、術后并發癥的風險均顯著增加。Rubbia-Brandt 等[6]提出的奧沙利鉑導致的HSOS 的分級方法目前被廣泛應用,即根據肝竇擴張累及小葉的范圍:不存在肝竇擴張視為0 級;肝竇擴張累及肝小葉區域>1/3 視為1 級,輕度;肝竇擴張累及肝小葉范圍擴展至2/3為2級,中度;肝竇擴張累及整個肝小葉為3 級,重度。該分級僅為病理分級,目前尚無奧沙利鉑化療導致的HSOS的臨床分級。
5 HSOS的預防和治療
PA-HSOS 的治療手段包括基礎治療、支持治療、抗凝治療和手術治療。基礎治療包括保肝、利尿、放腹水改善癥狀、營養支持等。支持治療包括肝腎替代治療,用于肝腎功能惡化的患者。抗凝治療是最根本的治療,可改善患者的預后。我國專家共識推薦的抗凝藥物為低分子肝素和華法林,二者可單用或合用,常規劑量是低分子肝素2 次/d,華法林劑量根據INR 調整,控制INR在2~3[3-4,25-27]。新型口服抗凝藥是否可用于治療PAHSOS 仍有待研究。我國專家共識對糖皮質激素治療PA-HSOS持謹慎態度。根據筆者中心經驗,PA-HSOS應用糖皮質激素治療極易引發肺部真菌感染,感染早期可無任何臨床癥狀,一旦出現發熱等癥狀提示肺部感染嚴重,大部分患者最終死于肺部感染[3-4,25-27]。
內科治療效果不佳轉經頸靜脈肝內門體分流術(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TIPS)治療的時機可參照DTSS 系統(Drum Tower Severity Scoring System,即鼓樓嚴重度分級系統)。該系統收集患者AST、TBil、纖維蛋白原和門靜脈血流速度4 個參數并分別賦分:評分4~6 分的患者建議接受門診抗凝并2 周門診隨診;評分7~10分的患者建議住院接受抗凝監測;評分≥11 分的患者抗凝無效的風險極大,建議盡快行TIPS治療。此外,若患者就診時出現門靜脈血栓/閉塞、治療過程中門靜脈血流速度<10 cm/s、病程中黃疸>5 mg/dL者,也應考慮行TIPS 治療。如果嚴格按照抗凝-TIPS 階梯治療策略,PA-HSOS 的治愈率可達90%,病死率<10%[25-27]。對于合并肝衰竭內科治療不佳的患者,可考慮行肝移植。但PA 的次級代謝物半衰期較長,且對肝臟也有一定毒性作用,PA-HSOS 行肝移植的病例極少,肝移植能否改善預后仍有待研究。
去纖苷是一種從豬腸黏膜中提取的具有多種抗血栓、纖溶和血管生成活性的低聚脫氧核糖核苷酸,是目前預防和治療HSCT-HSOS 的孤兒藥,但尚未在我國上市。去纖苷在歐美各國中被用于HSCT-HSOS 的適應證并不完全一致,多數情況下被用于重度HSOS 的治療。去纖苷被用于HSCT-HSOS預防的情況包括:存在較為明顯的肝臟基礎疾病、二次HSCT、清髓治療方案中包含白消安、移植前使用吉姆圖珠單抗等。去纖苷的常規用量為25 mg·kg-1·d-2,共4次。在使用去纖苷的過程中,出血風險約為15%。在使用去纖苷后,盡管患者的HSOS 臨床嚴重程度無變化,但總體病死率可顯著降低[8,11,18-20]。移植前2周開始應用熊去氧膽酸在部分國家被作為常規方案,但能否降低HSCT-HSOS的發生率尚不明確。在骨髓細胞移植后的前90 天內應用熊去氧膽酸作為HSCTHSOS的一級預防,并不降低HSCT 相關的HSOS發生率,但可降低已發生HSOS患者的黃疸水平,同時可降低無復發相關死亡率,并提高總體生存率[28]。低分子肝素用于治療HSCT-HSOS 被認為無效。TIPS 和肝移植在HSCTHSOS患者中未見對提高生存率有益[8,11,19,20]。
針對奧沙利鉑相關的HSOS,目前無特異的預防和治療藥物。降低化療藥物的劑量是目前唯一被證實的有效預防和/或降低HSOS 嚴重程度的手段。終止化療和支持治療可降低急性期肝衰竭的發生率。去纖苷在奧沙利鉑相關的HSOS中未被證實有效。補充外源性谷胱甘肽可減輕氧化應激和炎癥反應,但對于改善肝纖維化并無作用。貝伐單抗是一種抗血管生成藥物,在一些研究中被證實,可減少奧沙利鉑導致的HSOS 的發生率和嚴重程度。不僅如此,貝伐單抗聯合治療還可延緩脾腫大的發病時間,降低血小板減少的發生率[7,15]。
6 小結
HSOS 是一類有相似病理改變的疾病的統稱,病因不同則臨床表現有較大差異,治療方案也各不相同。部分患者在及時祛除病因后可無需治療,但部分患者需要行肝移植。加大對HSOS 的宣傳力度,避免民眾未經處方服用含PA 藥物,提高臨床醫生對該病的認識,積極預防、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是減少HSOS危害的重要措施。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不存在任何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