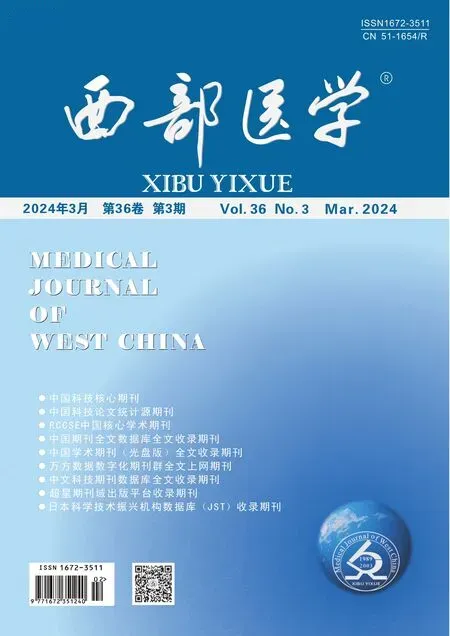美托洛爾聯合氯吡格雷對心肌缺血再灌注損傷小鼠的作用機制*
門汝梅 王艷林 張琳娜 門麗麗 蘭文達 孟慶蘭 于建才
(1.滄州市人民醫院心內三科,河北 滄州 061099;2.滄州市中西醫結合醫院手顯微外二科,河北 滄州 061013;3.滄州市中心醫院心內二科,河北 滄州 061017)
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是冠心病中最嚴重、危害最大的病癥之一,具有發病急驟、進展迅速、復雜多變、并發癥多、死亡率高等特點[1]。AMI治療方法通常為溶栓療法、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冠脈搭橋術)[2]。多數情況下,缺血后再灌注可使組織器官功能得到恢復,損傷的結構得到修復,患者病情好轉康復;但有時缺血后再灌注,不僅不能使組織、器官功能恢復,反而加重組織、器官的功能障礙和結構損傷[3]。這種在缺血基礎上恢復血流后組織損傷反而加重,甚至使心肌發生不可逆性損傷的現象稱為心肌缺血再灌注(Myocardial ischemia reperfusion,MI/R)損傷。MI/R損傷是一個重要的臨床問題,尚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案。研究表明β受體阻滯藥降低AMI病死率與減慢心率有關,β受體阻滯藥美托洛爾能夠選擇作用于心臟,不增加周圍血管阻力和影響后負荷,且不增加支氣管阻力,故臨床上較常選用[4]。研究發現美托洛爾治療具有降低MI/R損傷引發的心肌梗死[5]。此外,AMI患者再灌注期間要常給予抗血小板藥物治療,避免血栓形成[6]。研究表明在MI/R損傷過程,血小板激活通過分泌血清素等促進循環系統中性粒細胞激活,激活的中性粒細胞會浸潤至缺血再灌注區域心肌組織中,然后發生脫顆粒,引發心肌組織損傷[7]。因此,抗血小板藥物在抗凝的同時可能具有改善MI/R損傷的功能。本研究探討美托洛爾聯合抗血小板藥物氯吡格雷對MI/R損傷小鼠的作用,為臨床MI/R損傷藥物治療提供理論基礎。
1 材料與方法
1.1 實驗動物 75只10周齡SPF級雄性C57BL/6小鼠購于北京維通利華實驗動物技術有限公司[許可證號:SCXK(京)2022-0009]。飼養條件:飼養盒內飼養,溫度20~26 ℃,濕度40%~60%。本研究獲滄州市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審批號:K2022-批件-065(11.1)]。
1.2 動物分組及MI/R損傷模型復制 小鼠隨機化分為假手術組、模型組、美托洛爾組、氯吡格雷組及聯合組,每組15只。術前分別給予假手術組和模型組生理鹽水灌胃、美托洛爾組美托洛爾(阿斯利康制藥有限公司,10 mg/kg/d)灌胃、氯吡格雷組氯吡格雷(賽諾菲安萬特杭州制藥有限公司,20 mg/kg/d)灌胃、聯合組美托洛爾(10 mg/kg/d)和氯吡格雷(20 mg/kg/d)灌胃。各組小鼠吸入3%異氟烷麻醉誘導,1.5%~2%異氟烷麻醉維持。方法:將小鼠以仰臥位放置,剪開左胸皮膚,鈍性分離胸肌,然后經第4肋間隙開胸迅速暴露心腔,心包打開后,小鼠心臟暴露,用左手手指調整心臟位置使心尖朝向胸廓開口處,在心臟跳動的帶動下輕輕將心臟擠出至胸外,假手術組小鼠使用7-0絲線在距心底3 mm處左前降支冠狀動脈下穿線,不結扎。其余組小鼠使用7-0絲線在距心底3 mm處左前降支冠狀動脈下穿線結扎,形成活結,然后將心臟迅速放回胸腔,手動排空氣,胸腔皮膚用4-0絲線縫合。缺血30 min時,將心臟上7-0結扎絲線解開并移除。
1.3 心臟超聲檢查 采用VeVo 2100小動物超聲儀(VisualSonics公司)檢測再灌注24 h后小鼠心功能。將小鼠用3%異氟烷誘導麻醉,然后用1.5%~2%異氟烷維持麻醉狀態。將小鼠以仰臥位放置,在其胸部涂上超聲耦合劑,通過超聲儀檢測心臟功能和心室結構,評估左心室射血分數(Ejection fraction,EF)和左心室縮短分數(Fraction shortening,FS)。
1.4 心臟伊文思藍及2,3,5-氯化三苯基四氮唑(TTC)染色 MI/R 24 h后,用1%戊巴比妥鈉(80 mg/kg)麻醉小鼠,按缺血時的位置、寬度和深度結扎左前降支冠狀動脈,通過升主動脈將2%的伊文思藍染料200 μL注入心臟。取下其心臟并用PBS漂洗,吸水紙吸干心臟表面的水分。將心臟在-80 ℃冷凍30 min以上,然后將結扎線以下的心臟組織橫向平均切成五片。切片置于1% 2,3,5-氯化三苯基四氮唑(索萊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37 ℃避光孵育10 min,然后用10%福爾馬林固定2~4 h。對染色后的心臟組織進行拍照記錄。
1.5 流式細胞儀檢測 MI/R 24 h后,取50 μL各組小鼠外周血,分別加入0.5 μL FITC標記的抗小鼠CD41a抗體、PE標記的抗小鼠CD62p抗體,冰上孵育30 min,然后4 ℃ 400 g離心5 min,將沉淀細胞用FACS緩沖液重懸,流式上機檢測。所有抗體均購于Biolegend公司。
1.6 免疫熒光及TUNEL染色 MI/R 24 h后,取小鼠心臟,采用10%福爾馬林溶液固定組織24 h,然后將固定的組織脫水,石蠟包埋,制備石蠟切片。免疫熒光染色:取石蠟切片,脫蠟、固定,山羊血清(中杉金橋)進行封閉,然后分別使用兔抗小鼠Ly6G抗體(Abcam公司)、大鼠抗小鼠CD41抗體對組織中性粒細胞和血小板進行染色,4 ℃孵育16 h,洗片后再使用Alex Flour488標記的抗兔IgG抗體(中杉金橋)及Alex Flour594標記的抗大鼠IgG抗體(中杉金橋)室溫孵育1 h,洗片后用DAPI封片,熒光顯微鏡下觀察拍照。TUNEL染色:石蠟切片經二甲苯透明和梯度乙醇脫蠟水化處理后,使用TUNEL細胞凋亡檢測試劑盒(綠色FITC標記熒光檢測法,凱基生物)對小鼠心肌細胞凋亡情況進行分析,具體方法參照試劑盒說明書,通過光學顯微鏡觀察細胞凋亡狀況。
1.7 Western blot檢測 MI/R 24 h后,取小鼠心臟,然后加入1 mL RIPA裂解液,使用組織勻漿機對組織進行勻漿,勻漿后的組織放于冰上裂解10 min,之后4 ℃,12 000 g離心5 min,取上清液;然后往上清液中加入上樣緩沖液;SDS-PAGE跑膠、轉膜,轉印蛋白的膜用5%脫脂奶粉37 ℃封閉2 h,之后抗小鼠Caspase 3抗體(1∶1 000)、PARP-1抗體(1∶1 000)、GAPDH(1∶1 000)抗體4 ℃孵育12 h(GAPDH、Caspase 3和PARP-1抗體均購于Abcam公司),然后使用HRP標記的二抗37 ℃孵育1 h,最后加入ECL發光液曝光檢測。

2 結果
2.1 各組小鼠心功能變化 MI/R損傷手術前各組小鼠左心室EF值和FS值無顯著性差異(P>0.05)。手術后(再灌注24 h后),模型組、美托洛爾組、氯吡格雷組及聯合組小鼠左心室EF值、FS值相比于手術前顯著降低(P<0.05);美托洛爾組、氯吡格雷組及聯合組小鼠左心室EF值、FS值顯著高于模型組(P<0.05);聯合組小鼠左心室EF值、FS值分別顯著高于美托洛爾組、氯吡格雷組(P<0.05),見表1。

表1 各組小鼠左心室EF和FS比較
2.2 各組小鼠缺血再灌注區心肌梗死面積比較 伊文思藍-TTC染色結果顯示,再灌注24 h后,假手術組、模型組、美托洛爾組、氯吡格雷組及聯合組小鼠缺血危險區面積/心臟總面積無顯著性差異(P>0.05);模型組、美托洛爾組、氯吡格雷組及聯合組小鼠缺血區心肌梗死面積顯著高于假手術組(P<0.05);美托洛爾組、氯吡格雷組及聯合組小鼠缺血區心肌梗死面積顯著低于模型組(P<0.05);聯合組小鼠缺血區心肌梗死面積分別顯著低于美托里爾組和氯吡格雷組(P<0.05),見圖1。

圖1 各組小鼠缺血再灌注區心肌梗死面積比較
2.3 各組小鼠外周血血小板活化水平比較 流式細胞術檢測分析結果顯示,再灌注24 h后,模型組、美托洛爾組、氯吡格雷組外周血血小板活化水平顯著高于假手術組(P<0.05),氯吡格雷組和聯合組外周血血小板活化水平顯著低于模型組(P<0.05),聯合組外周血血小板活化水平分別顯著低于美托洛爾組和氯吡格雷組(P<0.05),與假手術組水平接近(P>0.05),見圖2。

圖2 各組小鼠外周血血小板活化水平比較
2.4 各組小鼠缺血再灌注區血小板、中性粒細胞沉積水平比較 免疫熒光染色結果顯示,再灌注24 h后,模型組、美托洛爾組、氯吡格雷組及聯合組缺血再灌注區心肌組織血小板、中性粒細胞沉積顯著高于假手術組(P<0.05),美托洛爾組、氯吡格雷組、聯合組缺血再灌注區心肌組織血小板、中性粒細胞沉積顯著低于模型組(P<0.05),氯吡格雷組比美托洛爾組下降更明顯,聯合組缺血再灌注區心肌組織血小板、中性粒細胞沉積分別顯著低于美托洛爾組和氯吡格雷組(P<0.05),見圖3。

圖3 各組小鼠缺血再灌注區血小板、中性粒細胞沉積水平比較
2.5 各組小鼠缺血再灌注區心肌細胞凋亡水平比較 TUNEL染色結果顯示,再灌注24 h后,模型組、美托洛爾組、氯吡格雷組及聯合組缺血再灌注區心肌組織凋亡心肌細胞顯著高于假手術組(P<0.05),美托洛爾組、氯吡格雷組及聯合組缺血再灌注區心肌組織凋亡心肌細胞顯著少于模型組(P<0.05),美托洛爾組比氯吡格雷組下降更明顯;聯合組缺血再灌注區心肌組織凋亡心肌細胞分別顯著低于美托洛爾組、氯吡格雷組(P<0.05),見圖4。

圖4 各組小鼠缺血再灌注區心肌組織TUNEL染色比較
2.6 各組小鼠缺血再灌注區凋亡調控蛋白水平比較 Western blot檢測結果顯示,再灌注24 h后,模型組、美托洛爾組、氯吡格雷組及聯合組缺血再灌注區心肌組織剪切的Caspase 3和PARP1水平顯著高于假手術組(P<0.05),美托洛爾組、氯吡格雷組及聯合組缺血再灌注區心肌組織剪切的Caspase 3和PARP1水平顯著少于模型組(P<0.05),美托洛爾組比氯吡格雷組減少更明顯;聯合組缺血再灌注區心肌組織剪切的Caspase 3和PARP1水平分別顯著低于美托洛爾組、氯吡格雷組(P<0.05),見圖5。
3 討論
冠心病是臨床常見的缺血性心臟病,是指冠狀動脈發生粥樣硬化引起管腔狹窄或閉塞,導致心肌缺血缺氧或壞死而引起的心臟病。各種血運重建手段通過及時有效地恢復心肌血液灌注,可以減輕缺血導致的心肌損傷及壞死,然而心肌缺血后恢復血液再灌注本身也可進一步導致MI/R損傷。病理性缺血與心肌梗死治療后再損傷的耦合性疾病,尤其難以治療。盡管心臟保護作用在動物實驗中取得了成功,但事實證明將其轉化為臨床實踐很困難[8]。目前為解決臨床MI/R損傷藥物治療問題,對現有心血管疾病藥物用于MI/R損傷治療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
美托洛爾是一種高選擇性β受體阻滯藥,它廣泛使用于心力衰竭和AMI的臨床治療,且有研究顯示美托洛爾治療能夠顯著減少AMI患者治療后的死亡率,且動物實驗研究表明美托洛爾能夠減少MI/R損傷后心肌梗死面積,其機制與抑制心肌細胞凋亡有關[9-10]。本研究同時發現美托洛爾干預能夠顯著改善小鼠MI/R損傷后心功能,減少心肌梗死面積。另外,AMI患者經治療后心肌恢復血流后都會給予抗凝藥治療,避免術后血栓形成,引發二次堵塞,其中抗血小板抗凝劑氯吡格雷是常用的抗凝劑。氯吡格雷是通過抑制血小板表面的ADP受體(P2Y12),起到抑制血小板的作用以預防血栓形成。與其他抗血小板抗凝劑如阿司匹林相比,氯吡格雷具有抗血小板作用強、起效快等特點,且長期使用氯吡格雷的安全性比阿司匹林更高[11]。研究表明血小板通過其受體P2Y12激活后,能夠調控機體中性粒細胞、單核巨噬細胞激活[12]。此外,在MI/R損傷過程中血小板介導的炎癥反應扮演至關重要角色。研究表明,當缺血心臟恢復血流發生再灌注時,小鼠循環系統中血小板被激活,激活的血小板釋放血清素,繼而激活循環系統中性粒細胞,使中性粒細胞浸入至缺血再灌注損傷區域,導致心肌梗死加重[13-14]。此外,在MI/R損傷過程激活的血小板會沉積在心臟微血管上,導致微血管堵塞,引發心臟微循環障礙,導致心肌梗死加重[15-16]。因此,抗血小板P2Y12受體的氯吡格雷可能具有改善MI/R損傷的作用。本研究發現單獨給予氯吡格雷治療改善小鼠MI/R損傷后心功能,減少缺血再灌注區心肌梗死面積,其效果與單獨使用美托洛爾效果相當。進一步發現美托洛爾聯合氯吡格雷改善MI/R損傷后心功能及減少心肌更面積的能力顯著優于單獨使用美托洛爾或氯吡格雷。
MI/R損傷機制涉及炎癥反應、心肌細胞凋亡等[17-18]。本研究發現,MI/R損傷小鼠外周血血小板激活水平及缺血再灌注區小鼠心肌血小板沉積顯著高于假手術組,美托洛爾或氯吡格雷單獨治療及氯吡格雷聯合美托洛爾治療小鼠外周血血小板活化水平、缺血再灌注區小鼠心肌血小板沉積顯著下降,但氯吡格雷單獨治療血小板活化程度弱于美托洛爾,提示氯吡格雷主要通過抑制血小板激活改善MI/R損傷。對缺血再灌注區心肌組織凋亡分析發現,MI/R損傷小鼠缺血再灌注區心肌細胞凋亡數量及心肌組織剪切的Caspase 3、PARP1蛋白水平顯著高于假手術組,美托洛爾或氯吡格雷單獨及聯合治療小鼠缺血再灌注區小鼠心肌細胞凋亡數量及心肌組織剪切的Caspase 3、PARP1蛋白水平顯著下降,但美托洛爾單獨治療小鼠心肌細胞凋亡數量及心肌組織剪切的Caspase 3、PARP1蛋白水平少于氯吡格雷,提示美托洛爾主要是通過抑制心肌細胞凋亡改善MI/R損傷。有研究發現[19-20],MI/R損傷與Toll樣受體4/核轉錄因子κB(TLR4/NF-κB)、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PI3K/Akt)、Janus蛋白酪氨酸激酶/信號轉導子與轉錄激活因子3(JAK/STAT-3)等信號通路有關,其中心肌缺血后PARP蛋白上調,并通過增強NF-κB活性和增加基質金屬蛋白酶9的mRNA和蛋白表達造成再灌注損傷;MI/R后大鼠心肌組織NF-κB和Caspase-3活性明顯升高,而抑制JAK/STAT信號通路后心肌組織NF-κB和Caspase-3表達下調,但目前有關美托洛爾聯合氯吡格雷通過調控上述信號通路來影響Caspase 3、PARP1蛋白表達的詳細機制仍有待完善。由于MI/R損傷具有復雜的分子機制,美托洛爾及氯吡格雷均展現了抑制心肌細胞凋亡及血小板活化,但是二者也都基于其藥物特點,展現出相應側重的分子機制。
4 結論
美托洛爾聯合氯吡格雷治療心肌缺血再灌注損傷效果優于美托洛爾或氯吡格雷單獨治療,其機制與抑制心肌細胞凋亡及血小板激活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