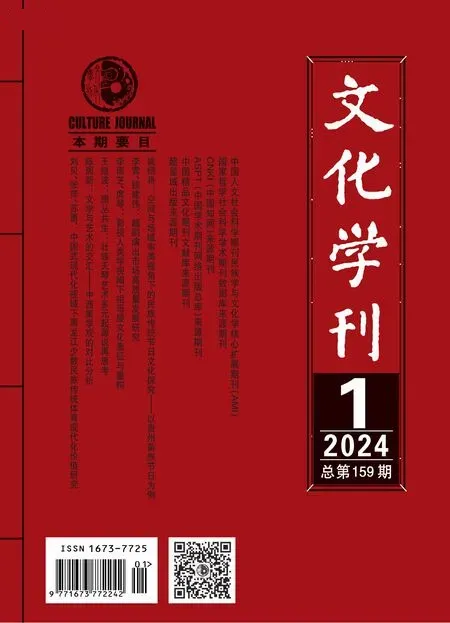空間視域下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劇成因初探
王倩倩
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在安娜這條線索中講述了一個因愛情出軌的貴族婦女在同命運斗爭無望后臥軌自殺的故事。小說于1956年出版后便成為各類文學家研究的重點對象,很多學者從文本出發對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宗教、悲劇成因、女性意識進行了分析。在對安娜悲劇成因的分析中,韓家勝、康佳瓊分別從社會和個人因素出發將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劇歸咎于制度的禁錮,張璐從“自由的悖論”角度指出安娜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她的死亡悲劇,等等。這些研究較為全面地揭示了安娜死亡悲劇的成因,但卻沒有從空間理論視角對造成安娜死亡的原因進行分析,忽略了在上流社會權力規訓下形成的狹窄女性空間對安娜生存空間和精神空間的剝奪。“空間并不是某種與意識形態和政治保持著遙遠距離的科學對象。相反,它永遠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1]小說揭示了空間生產其實是一種空間規訓,安娜對“自由愛情”的追求是對自身生存空間及精神空間的擴張奢望。本文以列斐伏爾的空間三元辯證法理論和福柯的權力空間理論為出發點,從空間侵占和權力規訓方面論述造成安娜死亡悲劇的原因。
一、空間的轄制
(一)社會空間規范下的社交寵兒
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中提出了空間三元辯證法,即構建了空間實踐、空間表象、表征性空間的三位一體,將空間劃分為物質空間、社會空間和精神空間。“列斐伏爾的社會空間強調了統治、服從和反抗的關系,它具有潛意識的神秘性和有限的可知性,作為一種開放性的親歷性空間,它是一種實際的空間。”[2]空間表象“與生產關系以及這些關系所強加的‘秩序’捆綁在一起,從而也與知識,與符號、代碼,以及種種‘臺前的’關系捆綁在一起”[3]。由此可見,《安娜·卡列尼娜》中上流社會等級森嚴、階層明顯的社交界體現和承接的正是統治階級的意志,是統治階級對空間秩序設定的具象化呈現。
上流社會從貴族個體到社交界都是權力規訓下的產物,安娜的社交活動主要由家庭生活和社交生活組成,這是封建貴族地主中女性成員的生活常態。家庭生活中,安娜最初安分地扮演著賢妻良母角色。比安娜大20歲的卡列寧是由安娜姑媽介紹而來,雖然他冷漠呆板,但安娜仍然對其及家庭充滿熱情。此階段的安娜正是被沙俄上流社會馴化出的一個美麗貴婦人,她發不出“從來如此,便對么?”[4]的質問,因為她的家庭生活正是上流社會推崇的“家庭范本”。在社交生活中,安娜經常涉及彼得堡上流社會的三個小圈子,一個是她丈夫政府官員的圈子,關系錯綜復雜;一個是卡列寧借之發跡的圈子,以李雅迪伯爵夫人為中心;后一個則是十分輕視半上流社會的社交界,奢侈華麗。在上流社會空間轄制下長大的安娜顯然對各類社交得心應手,安娜在社交場的八面玲瓏正體現出了社會空間對個體的規訓,她無意識地服從著空間規訓,扮演著飽受贊譽的女性角色。
社會空間中等級森嚴的各類社交場所其實正是階級、權力、社會意識形態的表征,無形中影響著個體的身份認同。此時的安娜連自己都尚未意識到自身生存空間是怎樣瑟縮于社會空間的緊緊轄制下。
(二)安娜自我空間意識的萌發
“我們所關切的社會階層和各種群體界限,以及滲透其中的社會權力關系,均鑲嵌在一定的空間里。”[5]女性作為社會空間網羅下的個體,經營自我空間的同時也經受著權力規訓。克瑞西達·海斯(Cressida J.Heyes)對空間規訓頗有想法,她認為規訓塑造出了服從的個體,“個體是一個循規蹈矩、溫順、自我監督的人,他被期望以特定的方式發展,并受制于更嚴密但看似更良性的管理形式”[6]。彼時俄國古老的封建地主受到西歐資本主義浪潮的猛烈沖擊,新思想一定程度上對上流社會空間有所滲透,安娜的女性意識因愛情得以滋生,其自身的空間意識也因此萌發。與伏倫斯基的偶遇扭轉了她的人生走向,“她故意收起眼睛里的光輝,但它違反她的意志,又在她那隱隱約約的笑意中閃爍著”[7]55。兩個富有生氣的人開始互相吸引,但已有家室的她本能地隱藏著這份欣賞。回家的列車上,安娜因沉浸式讀書神往和男主人公同至新封領地,此時的她感到害臊,于是反問自己“但他究竟有什么害臊的?我又有什么可害臊的?”這個質問影射了安娜對自身與伏倫斯基關系的看法,是安娜對自我生存空間的第一次質問與反思。舞會之后,伏倫斯基設法與安娜在列車廂偶遇,安娜深受觸動,在與丈夫碰頭后,安娜萌生“他的耳朵怎么變成這個樣子了?”[7]91的想法,“這是一種由來已久的熟悉的感覺,也就是在對待丈夫關系上的虛情假意。她以前沒有注意到這種感情,現在卻十分明白而痛苦地意識到了”[7]91。伴隨著愛情滋長,安娜的女性意識由此覺醒,同時意識到自身精神空間在社會空間規訓下的狹隘。安娜自我空間的意識萌發得益于列車媒介,在魚龍混雜的車廂或車站,安娜仿佛暫時脫離了等級森嚴的上流社會空間的規約,抓住了審視自己心意的瞬間。
二、試圖沖破空間束縛的女“斗士”
(一)安娜對生存空間遭受擠壓的反抗
權力無處不在,“但列斐伏爾并沒有像福柯那樣,面對無孔不入的權力控制而悲觀地認定現代人已經‘無可反抗’ 或 ‘無家可依’,而是認為,空間既是壓迫的重災區也是反抗的間隙處”[8]。
安娜因為伏倫斯基體會到了愛情在生命中的重要分量,深覺自身生存空間正遭受著社會空間的無情傾軋。于是她開始追隨自身心意行事,一系列行為正是其對生存空間遭受擠壓的本能反抗。夜談失敗后,安娜和卡列寧之間生出隔膜,其實這種隔膜一直存在,只是伴隨安娜女性意識的覺醒得以顯現。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安娜表面上熱衷社交,實際上到處都同伏倫斯基見面,安娜最終懷孕了,這是她無意識中擴張自我生存空間的第一步。
女嬰順利降生,安娜與伏倫斯基雙雙度過生命危機且更加確信雙方的重要性。安娜未與卡列寧離婚且選擇和伏倫斯基一起出國,此時場所發生轉移,與情人出國是安娜自我生存空間擴張的第二步表現。
旅行結束后回國,即使社交界大門已對安娜關閉,可她還是不顧伏倫斯基的勸阻去觀看了眾多名流在場的歌劇,這種在外人看來是公開挑釁的做法,是安娜為拓展自身空間樹立起的一面旗幟,是安娜為擴張自我生存空間所邁出的第三步。
這一系列行為實際上正是安娜為擴展自身生存空間所進行的反空間實踐,是一場抓住一切間隙擴展自身生存空間的權力博弈。
(二)安娜對自身精神空間的擴張欲求
精神空間是“人物對客觀世界的反映,是人物意識在空間實踐中的表現”[9]。安娜多年來深受上流社會的空間轄制,謹守自己的一隅空間。可當愛意洶涌而來,安娜的自我空間意識迅速生長,精神空間的擴張欲求愈發強烈。
與伏倫斯基的熱戀是引發安娜擴張自身精神空間的第一個動力來源。在上流社會,人們普遍對有婦之夫或有夫之婦與情人、情婦的曖昧持容忍態度,但絕不允許私情公開。安娜接受不了如同做賊般把愛情的火焰壓在暗處,于是便仇恨上這虛偽的社會空間,拼命想實現自身精神空間的擴張,在與伏倫斯基痛快的熱戀中踐行自我愛的權利。
卡列寧在發覺妻子出軌后幾次發出談話邀約,可安娜屢次婉拒,因為那些話無非是對妻子因“墮落”而濺到丈夫身上污泥的批判。對卡列寧而言,在妻子出軌所帶來的沖擊里,使自己名譽受損和上升通道受阻占了絕大部分,由此也可看出安娜確實在這無愛的家庭中飽受壓抑。愛情滋長使安娜深刻認識到自身生存空間的逼仄,進一步激起其擴張自身精神空間的欲望。
事態愈演愈烈,安娜終于在賽馬事件后向卡列寧坦白,這種行為表現出安娜在飽受心理折磨后對愛情的坦蕩追求,對自身精神空間獨立性急需確立的渴望,對脫離上流社會空間規訓和男權空間束縛的精神追求。面對安娜的坦白,卡列寧書信一封要求安娜留在家中以保持體面,安娜發出“我要沖破他這張想束縛我手腳的謊言的羅網”[7]251的吶喊。擴展自身精神空間的欲望和深陷泥潭難以抽身的現實共同威逼著安娜,她因深感無力沖破任何羅網而處于無盡痛苦之中。
三、掙扎不出的空間圍困
(一)社會空間對女性生存空間的擠占
如福柯所說,空間中的群體必然會受到“空間規訓”。“所謂‘空間規訓’,意指通過對空間的刻意為之的籌劃、設置與構造,對個體的心理狀態和人格結構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使之心悅誠服地屈從于既有的社會——文化秩序,并逐漸蛻變為馴順而高效的‘被規訓的物種’。”[10]
兩人的桃色新聞流傳時,伏倫斯基在生活表面上還可以繼續按照舊有生活軌道進行,安娜卻遭受著社會輿論的重壓。可見社會空間對女性進行著更為嚴苛的束縛,這是社會空間規訓女性的印證,更是男權社會下女性生存空間搖搖欲墜的表現。安娜同卡列寧徹底攤牌,繼而又在誕下女嬰后同伏倫斯基出國旅行,此時俄國上流社會對安娜的排斥表現出社會空間對女性生存空間的嚴格束縛,如果女性想要逃離空間規約,就會受到社會空間的進一步施壓。而后,安娜與卡列寧共赴鄉下莊園,希望從上流社會空間的約束中掙扎出來,此時安娜已把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于伏倫斯基。寄居莊園的安娜幾乎沒有了社交活動,表面上看似脫離了上流社會的空間束縛,實際上其生存空間已被擠壓到極點。上流社會通過對安娜的排斥實踐著權力規訓,同時也以安娜的“悲哀”下場對上流社會其他成員進行警示,借此維持城市空間的話語權,保持社會空間的穩定性。
生存在社會空間中的安娜不可能完全與世隔絕,身在其中卻不被接受的境遇展現出安娜自我生存空間屢遭擠占的現實,空間施壓是導致安娜死亡的重要推手。
(二)安娜自身精神空間的數遭圍堵
作為被上流社會權力空間網羅下的女性,安娜無法斬釘截鐵地做出離婚決定,只能在慌亂中說出“‘一切都完了,’她說,‘我除了你,什么也沒有了。你要記住!’”[7]132安娜也清楚,一旦對上流社會發起挑戰,被排斥是必然結局。但上流社會對女性生存空間的擠壓讓安娜無法自處,她只好在迷茫中將未來寄托于伏倫斯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是安娜精神空間的自為性擴張。在彼時俄國上流社會的空間規訓下,依附男性生活也是女性生存空間逼仄的原因之一。可安娜別無他法,因為社會沒有為她提供獨立機會。因此出國旅行時,只要伏倫斯基回家稍晚,安娜便疑竇叢生,這樣的生活狀態已顯病態,也為安娜的死亡埋下隱患。回到彼得堡后,安娜深覺社交界對她的排斥,因此情緒起伏極大,這說明安娜在拓展精神空間的過程中屢遭輕蔑,精神世界非常脆弱。安娜不僅失去了整個社交界,還失去了看望兒子的機會,在參加巴蒂歌劇時更是受到名流們明里暗里的輕蔑,安娜在精神空間擴張的路上再遭圍堵。
在鄉下莊園,安娜的精神空間已因社會空間排斥而萎靡,在她看來伏倫斯基是唯一的希望。可伏倫斯基只把愛情看作人生中求索的一部分。“總之,我什么都可以為她犧牲,就是不能犧牲我男子漢的獨立性。”[7]543伏倫斯基的想法是壓倒安娜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與外界的交往是如此讓安娜恐懼。歸根結底,安娜因生存空間逼仄而對伏倫斯基有著極強的依賴性,因此,當安娜誤解伏倫斯基對她的忠誠和深愛時,她的精神空間幾近消亡,生活對她來說毫無可留戀之處,于是安娜選擇了自殺。
安娜最終選擇了在火車站赴死,火車站其實正是社會空間相互滲透的一個交界點,是空間劃分不明晰的一個交界處。安娜的自我空間意識由火車站始,由火車站終,在空間的縫隙里覺醒,又在空間的縫隙里湮滅,她的精神因為沒有掙扎出權力空間的圍困而漂泊無依。
四、結語
從空間視域下對安娜的死亡悲劇進行分析,可以看到內化在空間中的權力意志對安娜的全方位束縛。安娜因為女性意識覺醒而本能地探求著自身生存空間與精神空間的擴張,卻因空間的裹挾只能苦苦掙扎。這場必然會輸的空間博弈實際是女性群體為突破自身生存空間與精神空間飽受壓榨所做的努力,展現了陷于空間囹圄的女性的本能性抗爭。安娜自身空間的擴張行動雖最終以死亡告終,但卻發人深省,“血和淚往往能給我們比歡笑更甜美的滋味”[11]。托爾斯泰在書寫安娜命運時持有同情之心,隱晦地批判了當時俄國的男權社會對女性的盤剝,其對受壓迫女性的人文關懷由此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