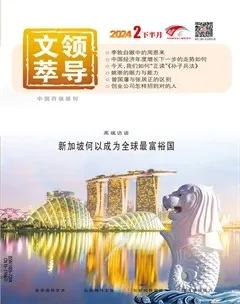鄉(xiāng)村振興需要人、業(yè)、地、村都發(fā)生變化
劉守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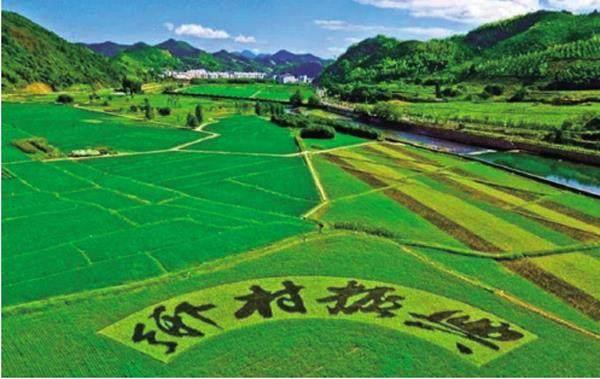
我們討論中國鄉(xiāng)村振興的問題,一定要在一個整體面上討論中國鄉(xiāng)村的未來。鄉(xiāng)村是一個系統(tǒng),人、業(yè)、地、村四者之間形成的有機系統(tǒng)是我們鄉(xiāng)村的魂。單要素改變鄉(xiāng)村就會導(dǎo)致鄉(xiāng)村系統(tǒng)的失衡,必然帶來整個鄉(xiāng)村的衰敗。重構(gòu)中國的鄉(xiāng)村系統(tǒng),就是要認清中國城鄉(xiāng)融合的形態(tài)和推進城鄉(xiāng)融合的路徑,重構(gòu)城鄉(xiāng)轉(zhuǎn)型的方式。最終的結(jié)果是城市更好,鄉(xiāng)村同樣更好。
破解鄉(xiāng)村問題的核心就是破解鄉(xiāng)村的“業(yè)”。中國首先面臨的問題是要把搞農(nóng)業(yè)的人口降下來,這樣農(nóng)業(yè)才能強。日本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驗是農(nóng)業(yè)工業(yè)化,將農(nóng)業(yè)要素重組。比如貴州遵義湄潭原來是非常貧困的地方,但這個地方的農(nóng)業(yè)形態(tài)和其他地方不同,人、地、業(yè)、村的系統(tǒng)已經(jīng)發(fā)生了重構(gòu),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農(nóng)業(yè)融合。湄潭最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推進農(nóng)業(yè)工業(yè)化的道路。
如何提高中國農(nóng)業(yè)的競爭力,最重要的秘訣是提高單位土地回報。哪個地方找到了提高單位土地報酬的辦法,哪個地方的農(nóng)業(yè)就有希望。山東濰坊的壽光建有基本上是全世界最大規(guī)模的設(shè)施農(nóng)業(yè)和大棚,大棚農(nóng)業(yè)的核心是提高單位土地的報酬。整個壽光的農(nóng)業(yè)就是在一個大棚里發(fā)生的農(nóng)業(yè)要素組合:通過農(nóng)業(yè)技術(shù)物聯(lián)網(wǎng)對農(nóng)業(yè)各種參數(shù)進行監(jiān)測,同時農(nóng)民成為新農(nóng)民,接受再教育培訓(xùn),對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認可,最終實現(xiàn)了單位土地報酬的提高。
實現(xiàn)鄉(xiāng)村經(jīng)濟的活化。現(xiàn)在鄉(xiāng)村經(jīng)濟的最大問題是單一,關(guān)鍵是要恢復(fù)鄉(xiāng)村經(jīng)濟的多樣化。要提高農(nóng)產(chǎn)品的復(fù)雜度。我們看日本和中國臺灣地區(qū),農(nóng)業(yè)的復(fù)雜度非常高,背后是知識含量,農(nóng)產(chǎn)品提高知識含量以后復(fù)雜度就提高了,價值也就提升了。
城市能留人,鄉(xiāng)村能換人。人的城市化關(guān)鍵是讓那幾億人在城市落下,而不是回村里。搞農(nóng)業(yè)的人少了,農(nóng)業(yè)和鄉(xiāng)村才有希望。所以農(nóng)村還有20%的人要想辦法在城市落下,關(guān)鍵點就是“農(nóng)二代”必須落城。人在城市落下來以后,鄉(xiāng)村也要換人。人口城市化以后鄉(xiāng)村是要換人的,一是讓部分出村的人回流,但一定是愿意到鄉(xiāng)村做事的人回到鄉(xiāng)村。二是一些搞農(nóng)業(yè)的企業(yè)要進來,未來的農(nóng)業(yè)要由企業(yè)家來組合農(nóng)業(yè)的要素,否則就沒有主體。三是讓一部分喜歡鄉(xiāng)村生活方式的人到鄉(xiāng)村。
鄉(xiāng)村的業(yè)、人改變的過程中,一定有地的改變。第一是人地關(guān)系的重構(gòu)。未來必須實現(xiàn)人地關(guān)系的重新匹配。第二是鄉(xiāng)村土地的重劃,用以解決鄉(xiāng)村土地的破碎狀態(tài)。土地碎化的結(jié)果是什么?就是搞農(nóng)業(yè)不積極,搞工業(yè)也不積極。城、鎮(zhèn)、村高度分割,農(nóng)業(yè)用地不規(guī)模、工業(yè)用地不規(guī)模、城市用地也不規(guī)模。中國鄉(xiāng)村需要按照土地的功能進行用地重劃。第三是在制度上要解決集體所有權(quán)下的承包權(quán)和經(jīng)營權(quán)的分置問題,核心就是解決新的主體進入鄉(xiāng)村以后,農(nóng)業(yè)企業(yè)家和規(guī)模化經(jīng)營主體的權(quán)利保障問題。第四是宅基地的改革。在保證農(nóng)民宅基地財產(chǎn)權(quán)利的同時,讓新的主體也能在村里落下來。第五是鄉(xiāng)村產(chǎn)業(yè)發(fā)展,需要集體建設(shè)用地與國有建設(shè)用地同地同權(quán)。
在業(yè)、人、地改變以后,一定要有村莊形態(tài)和功能的變化。第一,村莊變化要圍繞農(nóng)業(yè)發(fā)展方式,重新思考村落的半徑問題。農(nóng)業(yè)發(fā)展方式變化以后,村落的半徑可以適當(dāng)擴大。第二,村莊聚落要跟著功能來變。傳統(tǒng)村莊具有保護功能,現(xiàn)在的村莊很大程度是文化功能,強調(diào)聚落的功能、記憶的功能、歷史的功能和寄托鄉(xiāng)愁的功能。第三,未來的鄉(xiāng)村要解決基本公共服務(wù)的到位與體面問題。第四,村落要解決老人的精神和文化寄托問題。第五,村莊要成為鄉(xiāng)愁寄托的地方,讓農(nóng)一代在鄉(xiāng)村體面地老去,讓農(nóng)二代把鄉(xiāng)村變成詩和遠方。第六,鄉(xiāng)村要開放,成為一個驛站,各種對鄉(xiāng)村有想法、愿意到鄉(xiāng)村生活的人可以到鄉(xiāng)村去。
(摘自《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