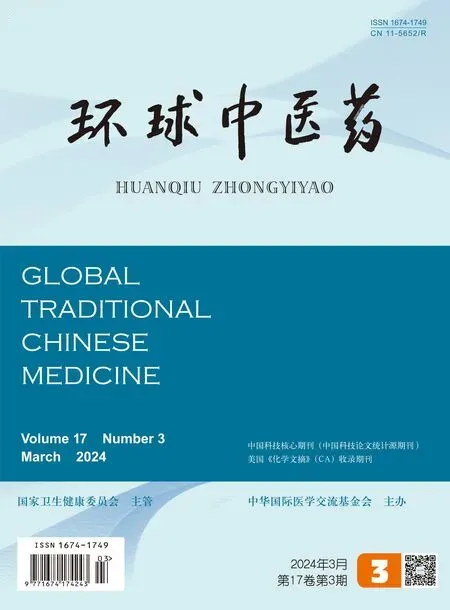《千金要方》宋校本與新雕本針灸文獻異文探析
王林云 潘鋒 李寶金 曾鳳
孫思邈《千金要方》集唐初及唐以前醫(yī)學之大成,保存了大量針灸醫(yī)學成果,具有極高的理論研究與臨床實用價值。值得注意的是,現今通行本宋校《備急千金要方》(以下簡稱“宋校本”)與早期傳本《新雕孫真人千金方》(未經后人校改,基本保存原著舊貌[1]。以下簡稱“新雕本”)針灸文獻存在大量異文[2]。筆者通過對兩版本針灸文獻的逐字對勘,發(fā)現二者在篇次篇題、條文編次、病種、主治病癥、腧穴順序、穴名及定位等方面多有異同,如新雕本在外陰、膽竅陰兩穴,宋校本并作竅陰;新雕本陽關,宋校本作關陽。本文以學科性差異為重點,對這些版本異文進行分析考察,探討宋人整理《千金要方》針灸文獻的原則、方法及內容,以期為當今針灸文獻理論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
1 《千金要方》宋校本與新雕本針灸文獻異文概述
《千金要方》針灸文獻主要源自《黃帝內經》《黃帝明堂經》《針灸甲乙經》《明堂圖》《明堂人形圖》等[3],針灸專篇卷29主要敘述腧穴理論與刺法灸法等,卷30記載了大量孔穴主對病癥。對比發(fā)現,宋校本與新雕本此兩卷的相異之處主要包括篇次篇題異文52處,腧穴定位異文96處,穴名異文22處,以及大量病種及主治病癥異文。此外,宋校本增補諸多針灸文獻。分述如下。
1.1 篇次篇題異文
《千金要方》卷29的具體內容包括明堂三人圖、經脈流注、針灸禁忌以及針例和灸例等,卷30以孔穴主對法為主。宋校本與新雕本此兩卷的篇次篇題異文計52處,其中以卷30居多,詳見表1。從表中可見:(1)從篇題來看,新雕本以疾病分篇,包括頭病、舌病、膝病、風病、癲病、雜病6篇,顯示出孫思邈原書按照“病”編排疾病主治。宋校本則有兩種分篇標準,一是按照身體部位,分為頭面、心腹、四肢3篇。二是按照病因病機分為風痹、熱病、癭瘤、雜病4篇。此外,宋校本將婦人病獨立成篇,并將小兒病附列其中,顯示出分科細化的趨勢;(2)從篇內內容編排來看,新雕本將頭病與舌病并列立篇,將手、臂、胸、腰等病列于《舌病第二》;將腸脹鳴不食、嘔吐、吐血、咳逆等病列入《膝病第三》,疾病歸類混雜。宋校本則根據類別的相似性,分為身體部位、病因病機分別歸類孔穴主對,分類清晰,便于臨床查找使用。
1.2 條文編次異文
宋校本與新雕本針灸文獻的條文編次異文,大致可分為三類:(1)條文所在卷次不同。如“左手關前寸口陰絕者,無心脈也,苦心下毒痛……刺足少陽”條,新雕本位于卷14《小腸腑·虛實第二》,宋校本位于卷13《心臟·脈論第一》。又如“兩乳間名身堂,主上氣厥逆”條,新雕本位于卷15《脾臟·虛實第二》,宋校本位于卷17《肺臟·積氣第五》;(2)條文所在篇次不同。以卷30為例,如“凡實則肩背熱,皆汗出,四肢暴腫……”條,新雕本歸于《舌病第二》“手病”,宋校本歸于《四肢第三》“肩背病”;又如“嘔吐病”諸方, 新雕本歸于《膝病第三》,宋校本歸于《心腹第二》;(3)同一篇中,條文所在位置不同。如卷29《明堂三人圖第一》側人耳頸二十穴,新雕本歸于“仰人明堂”條目,宋校本歸于“側人明堂”條目。

1.3 腧穴順序、穴名及定位異文
孫思邈自述《千金要方》“針灸孔穴一依甄公《明堂圖》為定”。黃龍祥認為甄權《明堂圖》是《黃帝明堂經》的腧穴圖譜及文字說明[6]。原書已佚,現有《黃帝明堂經》輯校本(以下簡稱“《明堂》輯校本”)。除了《千金要方》,宋以前針灸文獻主要保存于《千金翼方》《針灸甲乙經》《外臺秘要》《靈樞》《醫(yī)心方》等書[3],其中前三書亦經過宋人整理(以下簡稱“宋校《甲乙經》三書”)[7]14。現有研究發(fā)現,宋人根據《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以下簡稱“銅人”)校改《千金要方》“針灸篇”原文[7]189。以下本文依據此三方面的材料,對宋校本與新雕本腧穴部分異文進行考察。
1.3.1 腧穴順序異文 宋校本與新雕本腧穴順序基本一致,按照四肢部腧穴分經(從下到上)、頭面軀干部腧穴分行(從上到下)進行排列。詳考發(fā)現兩版本腧穴順序有兩處不同,一處見于《胸部第三行六穴遠近第五》,新雕本作膺窗→屋翳,宋校本作屋翳→膺窗。此兩穴位于軀干部,排序為從上到下,屋翳在庫房下一寸六分陷中,膺窗在屋翳下一寸六分,可見新雕本屋翳、膺窗上下順序顛倒。另一處腧穴順序差異見于《足少陽膽經十四穴遠近法第三》,新雕本作光明→陽輔,宋校本作陽輔→光明。此兩穴位于小腿部,排序為從末端到軀干,陽輔在懸鐘上,去外踝四寸,光明定位于外踝上五寸,亦可見新雕本上下順序顛倒。宋校本屋翳→膺窗、陽輔→光明的排序,與《銅人》和宋校《甲乙經》三書相同。
1.3.2 穴名異文 宋校本與新雕本穴名異文數量眾多,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用字不同,學術內涵相同,即“同穴異名”。如新雕本上管,或作上脘、或作上腕;亶中,或作膻中等,顯示出唐代一穴多名的現象非常普遍。宋校本前者均作上脘,后者均作膻中,表明該版本對穴名進行了統一。另一類穴名異文是用字不同,學術內涵亦不相同,詳見表2。從表中可見:(1)新雕本在外陰、膽竅陰分別表示兩個定位。宋校本將兩個穴位統稱竅陰,但未對二者的定位進行區(qū)分說明。與《明堂》輯校本、《銅人》和宋校《甲乙經》三書一致;(2)新雕本陽關定位于陽陵泉上三寸、犢鼻外,與《明堂》輯校本、《銅人》和宋校《甲乙經》三書一致。宋校本相同定位作關陽;(3)新雕本以會陰代指兩個穴位,宋校本區(qū)分為會陽、會陰,與宋校《甲乙經》三書一致;(4)新雕本兩處和髎,宋校本并作禾髎;《明堂》輯校本、《銅人》和宋校《甲乙經》三書分為禾髎、和髎兩穴。

表2 新雕本與宋校本、《明堂》輯校本、《銅人》、宋校《甲乙經》三書穴名對比
由此可以看出:(1)宋人對《千金要方》和宋校《甲乙經》三書的穴名進行統一改動,但宋校本存在疏漏,如關陽;(2)宋校本注重統一穴名用字,但對同一穴名代指兩個定位的情況未加以區(qū)別說明,如禾髎,有異于宋校《甲乙經》三書,表明宋人對穴名的統改存在疏漏。
1.3.3 腧穴定位異文 宋校本與新雕本穴名相同而定位有異主要有4處,詳見表3。由表中可知:(1)新雕本肺俞、心俞均定位于第五椎,其中必有一穴定位有誤。宋校本及《明堂》輯校本、《銅人》和宋校《甲乙經》三書分別定位于“第三椎”“第五椎”;(2)新雕本迎香定位于禾髎上、陽交定位于踝上七寸;宋校本分別作“禾髎上一寸”“外踝上七寸,斜屬三陽分肉間”,與《明堂》輯校本、《銅人》和宋校《甲乙經》三書相合;(3)新雕本和宋校本頭面正中線從發(fā)際線至頭頂的腧穴順序,發(fā)際處的起點神庭穴定位均為入發(fā)際五分,直鼻,其順序為神庭→上星→囟會→前頂→百會。二者的區(qū)別在于,新雕本百會穴定位于前頂后一寸,宋校本則為一寸半。結合《外臺秘要》《銅人》神庭定位從發(fā)際處后移五分的記載,以及宋人參考二者校改《千金要方》的史實,推測新雕本和宋校本百會穴定位相差5分的差異緣自宋校本的疏漏。

表3 新雕本與宋校本、《明堂》輯校本、《銅人》、宋校《甲乙經》三書腧穴定位對比
1.4 病癥異文
《千金要方》卷30“婦人病”直接輯錄《黃帝明堂經》主治婦人病條文,體例與諸篇不同[7]192。逐條對比發(fā)現,此一部分宋校本和新雕本具有醫(yī)學內涵差異的異文計有34處,其中病癥異文16條。舉例對比如表4(以□標識異文)。從表中可見,新雕本“衃血在內不下……”“小腹腫,溏泄……”兩條均是敘述病癥;宋校本作“絕子,衃血在內不下……”“女子疝及小腹腫,溏泄,癃,遺尿,陰痛,面塵黑,目下眥痛,漏血……”,增加病名“絕子”“女子疝”以及“目下眥痛,漏血”等癥狀,內容更為豐富。此外,新雕本“傷食脅滿,刺期門”,宋校本作“傷食腹?jié)M,刺期門”。有學者指出,該條文出自《黃帝明堂經》:“主婦人產余疾,食飲不下……傷食,脅下滿……”[7]192在現存文獻中,“肝募在期門”見于《脈經·肝膽部第一》,作“期門定位于兩脅部,主痙……脅下滿……以治療胸脅部疾病為主”。由上可知,新雕本以期門治傷食脅滿,與《黃帝明堂經》《脈經》相合;宋人將其改為“傷食腹?jié)M”,偏離了其腧穴主治,顯示出他們對文獻來源以及期門穴主治適應癥不甚了解。

表4 新雕本與宋校本病癥對比
1.5 宋校本增補大量針灸文獻
宋校本在針灸專篇增補大量針灸文獻,如在卷29增加《太醫(yī)針灸宜忌第七》,添補了推天醫(yī)血忌等月忌及日忌旁通法,推行年醫(yī)法、求歲天醫(yī)法、求月天醫(yī)法、推避病法、推治病法、喚師法、推十二部人神所在法、 日辰忌等大量內容, 指出“欲行針灸,先知行年宜忌,及人神所在”“凡醫(yī)者不知此法,下手即困;若遇年命厄會深者,下手即死”,體現出對針灸禁忌的高度重視以及追求內容豐富完整的校書理念。此外,宋校本增加阿是穴、“小兒病”部分,以及“三里,主乳癰有熱”等諸多治療婦人的針灸方。
2 異文比對結果分析
2.1 宋校本為精校本和臨床實用本
從以上異文比對結果可知,宋校本注重根據事類相從的原則分篇,篇題準確清晰;各篇收錄內容與篇題關聯緊密,條文順序編排合理,顯示出內在的邏輯性;疾病分科細化;穴位定位更準確,穴名、病名更規(guī)范;增補了針灸禁忌、小兒病、阿是穴及大量針灸主治病癥等,在豐富完善《千金要方》針灸文獻內容的基礎上,增強了該書針灸學術框架的系統性與完整性。結合宋人依據《銅人》[3]302校改《千金要方》針灸文獻的史實[7]189,可以說宋校本針灸文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宋代針灸學術的水平,為當時的臨床使用提供了參考,體現了宋人以實用性為目的,以簡便易用為校改理念的特點[8]。
2.2 宋校本存在若干訛誤
由上述可知,宋人對所校醫(yī)書的針灸文獻進行了統一改動,如上文提到的宋校《甲乙經》三書,但是其統改存在疏漏訛誤之處。一是在穴名方面,如陽關穴名稱,宋校《千金要方》與宋校《甲乙經》三書不同,當是前者有誤。二是宋校本存在“同名異穴”現象,如禾髎、竅陰二穴,均以一個穴名代指兩個不同定位,未加以區(qū)別說明。三是腧穴定位,如百會和神庭定位,宋人在統一校改時出現疏漏之處。四是主治病癥方面,宋校本“婦人病”“產余疾……傷食腹?jié)M,刺期門”,對“腹?jié)M”和“脅滿”的定義未進行嚴格區(qū)分,偏離了期門的主治適應癥。
今人對宋人整理《千金要方》針灸文獻的失誤多有考證。如黃龍祥指出孫思邈“孔穴主對法”所列主治病癥,一般為第一穴的主治原文,如“中沖、勞宮、大陵、間使、關沖、少沖、陽溪、天髎,主熱病煩心,心悶而汗不出,掌中熱,心痛,身熱如火,浸淫,煩滿,舌本痛”,其中“主熱病煩心……”等癥狀,為第一穴“中沖”的主治。但由于宋人對這種體例不了解,在宋校《甲乙經·卷七》中將中沖的主治病癥列于天髎之下,給后人考察原書原貌造成較大的困難[2]。
2.3 宋校本增補文獻所據不明,以往基于該版本提出的某些醫(yī)學史觀點有待重考
宋校本以直接填充的方式增補大量原書未有的醫(yī)學資料[9],其中包括大量針灸文獻,且未注明出處,不僅有違古籍整理的基本原則[10],也給今人溯源其文獻依據、厘清學術內涵,正確認識其文本內容帶來極大困擾。在醫(yī)學史方面,以往基于宋校本提出的某些學術觀點需要重新考證[8]。例如“阿是穴”,學界歷來公認其由孫思邈創(chuàng)立并給予極高評價,普通高等教育中醫(yī)藥類“十三五”規(guī)劃教材《中國醫(yī)學史》[11]《經絡腧穴學》[12]等也認為是孫思邈重要學術貢獻之一。本文通過考察版本異文發(fā)現“阿是穴”由宋人補入《千金要方》,此一問題有待結合相關文獻進一步深入考察。
3 討論
北宋校正醫(yī)書局作為歷史上首個官方醫(yī)書整理出版機構工作成就卓著,宋校醫(yī)書以質量精良及官方權威性成為后世之圭臬[13],是當今傳承發(fā)展中醫(yī)學的基礎性文獻。然而,本文通過版本異文的對勘顯示出宋校本《千金要方》針灸文獻存在若干訛誤及諸多存疑待考之處。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北宋校正醫(yī)書局以儒臣主導校書工作[14],“惟執(zhí)宋儒所說之理以為理,以儒者治經談道之說施之于醫(yī)[15]”;另一方面囿于主校者醫(yī)學專業(yè)知識的局限,在關乎學術內涵的文本上易于出現偏差[16]。因此,宋校本針灸文獻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尤為值得重視。
現代關于《千金要方》針灸文獻的研究,以通行本宋校本為主。針灸文獻研究屬于針灸的基礎研究,其研究對象主要是知識的載體和文字含義,以及這些文本所載述有關針灸的認知與方法,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針灸防治疾病[17]。因此,文本的準確性尤為重要。而宋校本與新雕本在腧穴名稱定位和腧穴主治病癥方面存在諸多異文,這些異文給正確理解與繼承孫思邈的針灸學術思想與臨床經驗帶來了困難。因此,有必要對宋人整理《千金要方》針灸文獻的理念、原則、方法程式及具體內容進行全面系統考察,辨章學術,甄別正誤,以便有效利用其文本意義,并為相關研究提供有益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