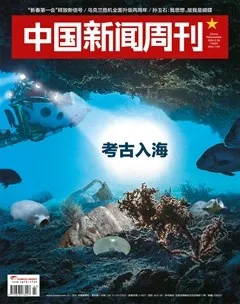尋找北洋沉艦
徐鵬遠(yuǎn)

經(jīng)遠(yuǎn)艦海底保存完好的舷窗。圖/受訪者提供
遼寧東港市西南方19海里,有一個6.6平方公里的島嶼,仿若蒼茫黃海之中一只踡臥的梅花鹿,因此得名“大鹿島”。島嶼東部山巒的北坡上,青松翠柏掩映著一座墓園,紅磚堆砌、水泥抹頂?shù)陌雸A形墳丘前立有一塊2.5米高的石碑,上面鐫刻了金光灼目的四個金色大字“鄧世昌墓”。在大鹿島村民代代相傳的講述中,這是英雄的埋骨之處。
島嶼西南方向大約9海里的地方,便是那具遺骸出水的位置,除了或北或南的風(fēng)浪,這片壯闊的海域如今不再有任何其他的波瀾。然而曾經(jīng),這里卻籠罩在滾滾煙塵之中——那是1894年的9月17日,中國北洋海軍與日本聯(lián)合艦隊在此上演了人類第一場蒸汽鐵甲艦隊的大規(guī)模戰(zhàn)爭,史稱黃海海戰(zhàn)。這是中日甲午戰(zhàn)爭的重要戰(zhàn)役之一,對甲午戰(zhàn)爭后期的戰(zhàn)局具有決定性影響。雙方各自出動了十余艘軍艦,分別以“雁行陣”和“一字陣”對壘,一時間炮聲四起、海水沸騰。
這場海戰(zhàn)從中午12時48分打到了下午5時半,持續(xù)5個小時,以北洋海軍損失5艦退守旅順、威海而告終。其中最為壯烈的一幕出現(xiàn)在下午3時左右,彼時北洋的旗艦定遠(yuǎn)艦中彈燃起大火,日艦趁機迅速靠近,準(zhǔn)備將其一舉擊沉,千鈞一發(fā)之際,致遠(yuǎn)艦沖了出來,開足馬力馳向敵陣。在之前的戰(zhàn)斗中,該艦已多處受創(chuàng),嚴(yán)重向右傾斜,左側(cè)螺旋槳甚至露出了海面,因此這是一次孤注一擲的沖鋒,抱了必死的決心欲與敵人同歸于盡。然而,這艘北洋軍中航速最高的巡洋艦卻在距離日艦尚遠(yuǎn)的地方,響起了一聲劇烈的爆炸,一頭扎進海里。
作為管帶(即艦長),鄧世昌從此成了英雄,光緒皇帝御賜的挽聯(lián)“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傳頌千秋。然而致遠(yuǎn)艦的沉沒卻留下了重重疑團:在李鴻章上呈清廷的報告中,該艦是被日艦以魚雷轟沉的,另一些當(dāng)事人則回憶是一顆320毫米口徑巨炮導(dǎo)致沉沒,但無論魚雷還是火炮,在日軍參戰(zhàn)各艦的戰(zhàn)斗報告里都未曾被提及過。
直到2015年,沉睡海底120年的致遠(yuǎn)艦被重新發(fā)現(xiàn),這道謎題才在一批殘片和遺物提供的線索中變得明晰一些。與此同時,這次發(fā)掘也標(biāo)志著自2013年啟動的“甲午沉艦水下考古”取得了第一個正式收獲。之后十年,該計劃不斷得到推進,至2023年,所有遺址尚存的北洋海軍主力沉艦幾乎都得到了確認(rèn)和調(diào)查。作為該計劃的第一個全面總結(jié),《致遠(yuǎn)艦水下考古調(diào)查報告》也在2023年正式出版。2024年起,研究者將開始集中精力完成定遠(yuǎn)艦的考古報告,經(jīng)遠(yuǎn)艦、來遠(yuǎn)艦的報告也會陸續(xù)提上日程,許多關(guān)于北洋海軍和甲午海戰(zhàn)的信息與細(xì)節(jié)正在或者即將被解讀出來。
致遠(yuǎn)
對北洋沉艦的尋找其實早在1980年代就開始了,如今陳列在甲午戰(zhàn)爭博物館的兩門210毫米火炮,便來自于1986年對濟遠(yuǎn)艦遺物的打撈。致遠(yuǎn)艦同樣經(jīng)歷過先后數(shù)次的打撈計劃,只是一直未能獲得實質(zhì)性的進展。
1988年,遼寧省文化廳率先作出過嘗試,但因為探摸過程中遇到意外情況而擱淺。1996年,時任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企業(yè)文化研究所副所長的柴勇軍又發(fā)起倡議,在得到國家文物局發(fā)文同意后成立了致遠(yuǎn)艦打撈籌備辦公室。次年,“國家打撈致遠(yuǎn)艦辦公室”正式成立,開始組織打撈籌備工作,后續(xù)在莊河黃石礁、黑島附近開展過海上搜尋,明顯偏離了甲午海戰(zhàn)的主戰(zhàn)場。又過了幾年,北京一家電視臺與東港市接觸,希望籌措社會資金打撈致遠(yuǎn)艦,再次不了了之。2012年,一家雜志提出由其版權(quán)合作的美國雜志派潛水員來進行探查,仍舊沒能成功實現(xiàn)。
盡管這些探索的失敗各有原因,但也映照出一個不爭的事實:對包括致遠(yuǎn)艦在內(nèi)的甲午沉艦進行調(diào)查乃至打撈,是一個難度極大的挑戰(zhàn)。周春水時任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chǎn)保護中心(現(xiàn)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的研究館員,常年致力于水下考古和水下文化遺產(chǎn)保護的研究與實踐,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具體操作角度來說,北洋沉艦考古必須面對這樣幾道難題:“首先是怎么找到(沉船)點,相關(guān)的資料非常繁雜,有的并不準(zhǔn)確,甚至互相之間有沖突,(所以)找到位置就要費很大工夫。而北方地區(qū)的海水很冷,一般4月份的水溫才3℃左右,到6月份才十幾度,每年的工作季壓縮到7月份到9月份短短3個月內(nèi),可用搜尋時段很少。第二,怎么把沉艦面目認(rèn)清也是一個大問題。傳統(tǒng)的沉船考古都是木質(zhì)帆船,大小也就二十多米長,沉艦動輒七八十米長、十幾米寬,(而且)木質(zhì)帆船的結(jié)構(gòu)相對簡單,沉艦則全是機械,很多東西還破損嚴(yán)重,復(fù)雜性成幾何倍數(shù)地增加。另外,北方海域大部分時間能見度都比較差,沉艦又幾乎完全被板結(jié)的泥沙埋住,要用不同的辦法去克服這些問題。”
因此這是一項牽扯大量人力物力以及科技投入的工作,需要整體規(guī)劃和充分準(zhǔn)備才有可能完成。時機在2013年出現(xiàn),當(dāng)年11月丹東港擬擴建海洋紅港區(qū),為避免基建破壞,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chǎn)保護中心聯(lián)合遼寧省文博單位正式啟動了基建區(qū)水下考古調(diào)查工作。周春水被任命為了該項目的負(fù)責(zé)人,在2014年4月帶領(lǐng)著考古隊開始了全新的物探調(diào)查。經(jīng)過多波束聲吶、旁側(cè)聲吶、淺地層剖面儀、磁力儀等設(shè)備勘探以及潛水探摸、抽沙清理,終于在丹東西南甲午海戰(zhàn)主戰(zhàn)場發(fā)現(xiàn)一艘鋼鐵沉艦遺址。2015年,隨著2件帶有“致遠(yuǎn)”篆書字樣的白瓷餐盤被發(fā)現(xiàn),這艘沉艦確認(rèn)為找尋已久的致遠(yuǎn)艦。
2016年10月,致遠(yuǎn)艦的水下考古宣告結(jié)束,歷時三年的調(diào)查不僅獲得了涵蓋70余個種類共429件/套出水文物,也弄清楚了殘存艦體的基本情況。通過這些成果,以往對于其沉沒是由于魚雷或火炮攻擊所致的說法基本可以排除。對此,周春水作出了詳細(xì)的解釋:“如果是被魚雷擊沉的話,(艦底)肯定有撕裂傷,但通過對水下沉艦的現(xiàn)狀分析,整個艦底是比較完整的。另外,我們在艦內(nèi)還發(fā)現(xiàn)了一些完整的炮彈和魚雷引信,如果被魚雷或炮彈打中,所有這些易爆品肯定是會被引爆的。”

甲午沉艦水下考古調(diào)查場景(遠(yuǎn)處為劉公島)。圖/受訪者提供

修復(fù)“致遠(yuǎn)”篆書餐盤。圖/受訪者提供

甲午沉艦遺址出水的部分小口徑子彈。圖/新華
周春水認(rèn)為,致遠(yuǎn)艦沉沒的真正原因或許還是因為此前受創(chuàng)產(chǎn)生的艦體傾斜導(dǎo)致艙內(nèi)處于進水狀態(tài),到達(dá)某個臨界點后無法再維持漂浮。事實上,鎮(zhèn)遠(yuǎn)艦軍官曹嘉祥、饒鳴衢在戰(zhàn)后的一份呈文中就曾提及過類似的看法:“譬如‘致‘靖兩船,請換截堵水門之橡皮,年久破爛而不能整修,故該船中炮不多時,立即沉沒。”
當(dāng)然,這一觀點并非定論。山東大學(xué)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的教授姜波就有另外的意見,此前作為國家文物局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長,他也參與過致遠(yuǎn)艦的調(diào)查。從發(fā)掘到的穹甲上顯露出的外翻跡象,他推斷是鍋爐爆炸的結(jié)果。在最后的沖鋒途中,致遠(yuǎn)艦的航速超過了動力上限,強排風(fēng)導(dǎo)致鍋爐壓力過大而發(fā)生劇烈爆炸,艦體因而迅速沉沒。“早期船艦因鍋爐爆炸發(fā)生的事故并不罕見。”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經(jīng)遠(yuǎn)
就在2014年致遠(yuǎn)艦被發(fā)現(xiàn)的差不多同時,其西方約三十公里外的海域也收到了磁力儀探測的信號反射,一個1400 余噸的鐵質(zhì)巨物埋藏在海面之下十米水深的地方。
在當(dāng)?shù)貪O民的記憶中,曾有人出海時撈到過銅片、洋錢、彈殼 、煙袋之類的東西,甚至撿到過魚雷。而老輩人則在1894年9月17日的夜里見過一群逃命的散兵,自稱是“林大人部下”——這位林大人,即是經(jīng)遠(yuǎn)艦的管帶林永升,已在當(dāng)天下午的作戰(zhàn)中“突中炮彈,腦裂陣亡”。與此同時,民國時期的《莊河縣志》也記載著,經(jīng)遠(yuǎn)艦沉沒的地方就在離漁村不遠(yuǎn)的“蝦老石東八里”。種種跡象都指向了一種可能,磁力儀收到的信號或許就來自經(jīng)遠(yuǎn)艦遺存。
不過倘若參考另一份資料,這種可能卻又似乎微乎其微。在日本戰(zhàn)后發(fā)布的報告中,經(jīng)遠(yuǎn)艦沉沒點的坐標(biāo)被定位在東經(jīng)123度33分、北緯39度32分,后經(jīng)整理改為東經(jīng)123度40分7秒、北緯38度58分,都與蝦老石海域相距較大。

海底的經(jīng)遠(yuǎn)艦銘牌。圖/受訪者提供
但隨著潛水探摸的展開,一艘出露海床0~2 米高、超過40米長的艦體殘骸出現(xiàn)在了考古隊員眼前。殘艦的船殼鋼板帶有20~40厘米不等的厚重裝甲帶,與經(jīng)遠(yuǎn)艦作為裝甲巡洋艦的特征極為相符,同時采集到的一塊德文銘牌也與經(jīng)遠(yuǎn)艦為德國建造的史實相印證。等到2018年開始正式調(diào)查,通過對艦體中后段右舷外壁的抽沙作業(yè),深埋在海泥以下5.5米的兩個木質(zhì)髹金大字“經(jīng)遠(yuǎn)”終于露出了容貌,遺物中也發(fā)現(xiàn)了一塊戳印著“經(jīng)遠(yuǎn)”字樣的木牌,至此確證了答案:這就是經(jīng)遠(yuǎn)艦無疑。
在那場激烈的戰(zhàn)斗中,經(jīng)遠(yuǎn)艦與致遠(yuǎn)艦同處陣列左翼,各自編為小隊,互相應(yīng)援。致遠(yuǎn)艦沉沒后,附近的濟遠(yuǎn)艦見狀逃離了戰(zhàn)場,與其編為一隊的廣甲艦以為有例可援,亦隨之遁走,于是左翼徹底崩潰,徒剩經(jīng)遠(yuǎn)艦孤軍奮戰(zhàn)。日軍的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艘艦艇遂對其形成圍攻之勢,“先以魚雷,繼以叢彈”,致使經(jīng)遠(yuǎn)艦身中數(shù)彈、火焰沖天、進水不止,于5時29分向左舷傾覆,成為北洋海軍在交戰(zhàn)中損失的最后一艘軍艦。吉野艦上的常備艦隊參謀釜屋忠道后來對此做過十分細(xì)致的記述:“在該艦傾斜時,可以看到露出的艦體鐵梁,實乃奇觀。該艦的艦員或是爭相攀爬到繩梯上,準(zhǔn)備翻沉?xí)r好泅水逃生,或是攀上桅桿,以圖求生……不久,‘經(jīng)遠(yuǎn)到了生命的終點,螺旋槳露出海面在空轉(zhuǎn),紅色的艦底也露出在水面上。”
這些歷史記載在考古中一一得到了印證:遺址左側(cè)外面發(fā)現(xiàn)的桅桿斜桁、天幕桿等甲板上的建筑,皆已折斷,說明艦體確是以翻扣之姿沉沒的;木桿上的火燒痕以及一批因高溫而自爆的彈藥,則側(cè)面證實艉部經(jīng)歷過嚴(yán)重的火燒。
相比致遠(yuǎn)艦,經(jīng)遠(yuǎn)艦的保存狀況要好得多,因為倒扣在海底,大部分生活艙室及甲板上的武器裝備都得以留存。尤其是位于艉部的軍官住艙的一扇銅質(zhì)外框的圓形舷窗,鑲?cè)氲牟A旰脽o損,透過它可以看到細(xì)泥淤滿艙內(nèi),如果沉沒時有人待在里面,那么遺骸有可能還在。姜波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dāng)時考古隊員在水下接觸到這扇舷窗時,仿佛就看到那些英雄犧牲的樣子:“那一刻,真的是在跟歷史對話,跟我們的英烈祖先在對話。歷史是一堆灰燼,但是灰燼的深處尚有余溫。”
最大的破壞來自盜撈,據(jù)周春水估計,艦體埋在泥中2米深的地方應(yīng)該都受到了影響。在漁民的印象里,至少有過三批不法分子在此處活動過,最近的一次是2009年,那些家伙在船上架起了一座鋼架平臺,吊起一個巨大的鐵錘向海里砸,再用大鐵爪往上撈銅鐵,一次就有幾噸重。考古隊進行清理時確認(rèn)了這些暴力盜撈留下的諸多痕跡:艉部外圍的密封艙門、大橫肋、工字梁、鉛質(zhì)水管、通水總管等都呈現(xiàn)出散落狀分布,許多東西發(fā)生了移位,原本應(yīng)該位于舯部(注:指艦艇中部)的一些蒸汽機構(gòu)件和船艏的起錨裝置出現(xiàn)在艉部,艦體外圍還有大量木板與鋼板,斷裂茬口的狀態(tài)可以判斷是打撈時掉落下來的。

燒焦的經(jīng)遠(yuǎn)艦天幕桿。圖/受訪者提供

鏨刻“來遠(yuǎn)”字樣的鍍銀湯勺。圖/新華

來遠(yuǎn)艦水手身份牌。圖/新華
那次盜撈,最后是在媒體的介入下被相關(guān)部門制止了,而之所以此前未能引起足夠重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文物部門尚未對遺址作出相關(guān)認(rèn)定。從這個意義上講,2018年的考古行動即是對這艘英雄沉艦的一次搶救和保護。正如周春水所說:“只有做完基礎(chǔ)的摸底,了解它的位置、水下保存狀況、水下環(huán)境等,才能知道下一步該怎么做,否則即使風(fēng)電、碼頭這樣的基建也可能破壞掉它們。”
定遠(yuǎn)、靖遠(yuǎn)與來遠(yuǎn)
對于黃海海戰(zhàn)的勝負(fù),一直以來存在著不同的觀點。但出戰(zhàn)軍艦的結(jié)局卻是明確的:經(jīng)此一役,北洋海軍損失五艦、其他各艦也均不同程度受創(chuàng),日本艦隊重傷五艦、一艦未沉。
戰(zhàn)后的第二天,即9月18日,幸存的北洋軍艦陸續(xù)回到了旅順。19日,清廷頒布諭旨:“著李鴻章查明傷亡士卒,請旨賞恤,一面飭丁汝昌將各艦趕緊修復(fù),以備再戰(zhàn)。倭船數(shù)多于我,并圖深入內(nèi)犯,此時威、旅門戶及沿邊山海關(guān)各口十分吃緊,應(yīng)飭分防駐守各兵弁晝夜訪察,嚴(yán)密防范,毋令一船近岸。”事實上暫時免除了海軍的巡海重責(zé),將防衛(wèi)任務(wù)交給了陸上海防部隊。
然而旅順的基地在設(shè)計時并未考慮過戰(zhàn)時大規(guī)模修理的需求,僅有1座大型干船塢,因此除了受傷最重的主力艦“定遠(yuǎn)”和“鎮(zhèn)遠(yuǎn)”等,其他軍艦只能排隊空等。反觀日軍方面,除了“松島”、“比睿”、“赤城”、“西京丸”傷勢較重被送回本國,余艦則全部集結(jié)于朝鮮西海岸的小乳纛岬錨地,由工作船“元山丸”利用搭載的技術(shù)工人和裝備、材料進行應(yīng)急維修,并由運輸船“千代丸”“土洋丸”提供彈藥補給,“玄海丸”幫助撤走傷員,至9月22日深夜便基本完工。當(dāng)天下午,聯(lián)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即派出兩艘航速較高的巡洋艦對威海-煙臺-大連灣進行了偵察,次日主力艦隊又前往海洋島以北至大孤山一線的遼東海岸實施偵察行動。
從9月22日到10月22日,日艦一直在渤海灣及西朝鮮灣地區(qū)活動。而北洋的軍艦直到10月18日,才終于駛出旅順,開向威海。11月22日,日本攻陷了旅順。又過了兩個月,1895年1月20日,日本向威海發(fā)起攻擊,短短幾天時間北洋海軍便落入了日本海陸軍的合圍之中。2月17日,北洋海軍全軍覆沒,“鎮(zhèn)遠(yuǎn)”、“濟遠(yuǎn)”、“平遠(yuǎn)”、“廣丙”等10艘軍艦被日本俘獲,“定遠(yuǎn)”、“靖遠(yuǎn)”、“來遠(yuǎn)”則沉入了海底。
2017年,隨著黃海北部區(qū)域的沉艦調(diào)查取得實質(zhì)進展,威海灣的考古也接續(xù)開始展開。相對而言,這一部分的工作的難度略小,三條沉艦離岸更近,留下來的照片也更豐富,通過比對圖片中的陸岸山體形狀便可以圈定出大體位置。但經(jīng)過初步調(diào)查,該區(qū)域并未發(fā)現(xiàn)完整艦體,僅存遺物均呈散落分布狀態(tài),凝結(jié)塊堆積、木板殘斷、鋼板扭曲。這是由于當(dāng)初日本對威海灣沉艦長期打撈所致的破壞,雖然同樣的行為也在黃海北部進行過,但因為離岸更遠(yuǎn)、海況更復(fù)雜,程度不及此處。
威海衛(wèi)戰(zhàn)役中,來遠(yuǎn)艦是最先沉沒的。2023年,在如今已成為旅游渡船錨地的位置,考古隊發(fā)現(xiàn)了這艘沉艦,一把鏨刻著“來遠(yuǎn)”字樣的餐勺和兩塊寫有具體等級、姓名的水手身份牌,確認(rèn)了這就是那艘在日軍凌晨發(fā)動的偷襲中被魚雷擊中,底朝天消失于海平面的裝甲巡洋艦。此外,遺址中還發(fā)掘出了剃須刀、銅鎖、麻將、象棋等大量生活用品,極大豐富當(dāng)年的海軍將士的生活樣貌。
靖遠(yuǎn)艦在守衛(wèi)劉公島的戰(zhàn)斗中,曾在定遠(yuǎn)艦左舷舯部被擊中而產(chǎn)生爆炸后,一度被作為替補旗艦使用,并擊傷了兩艘日艦。日軍隨后調(diào)用了早前占領(lǐng)的皂埠嘴(又稱趙北嘴)炮臺向其開炮,兩發(fā)命中左側(cè),炮彈穿過艦體后從附近的水線下部位穿出,官兵雖奮力搶救,仍無法阻止艙內(nèi)進水,無奈擱淺于威海灣內(nèi)。丁汝昌與靖遠(yuǎn)號管帶葉祖珪欲與艦同沉,被部下誓死救上小船。次日下午,為免于資敵,丁汝昌命令廣丙艦發(fā)射魚雷,擊沉靖遠(yuǎn)艦。2022年夏,這艘沉艦也在威海灣中被找到,一枚重達(dá)150公斤的炮彈成為確認(rèn)其身份的關(guān)鍵證據(jù),其210毫米尺寸與“靖遠(yuǎn)艦”主炮尺寸正好吻合。
敗局已定之際,與靖遠(yuǎn)艦同時被作自毀處理的還有定遠(yuǎn)艦。黃海一戰(zhàn)中,它在中彈起火的情況下仍頂住了五艘日艦的輪番進攻,以致日本水兵三浦虎次郎驚嘆:“定遠(yuǎn)號怎么還不沉?”;威海衛(wèi)一戰(zhàn),它在艦身嚴(yán)重傾斜后搶灘擱淺,繼續(xù)充作炮臺使用。2020年9月17日,經(jīng)過十多個小時的清淤、穿纜、保護、起吊,一塊長283.2毫米、寬260毫米、厚30.5毫米、重18.7噸的定遠(yuǎn)艦鐵甲被打撈出水,足以說明這艘德國伏爾鏗造船廠制造的鐵甲艦,曾經(jīng)為什么會被譽為 “可列于當(dāng)今遍地球第一等之鐵甲艦”。
關(guān)于這塊鐵甲,周春水還向《中國新聞周刊》作出了更為具體的介紹:“它是康邦裝甲,即外面一層硬鋼、里面一層軟鋼的復(fù)合裝甲。這么大的裝甲是一塊一塊安裝的,背面有六個孔,用螺栓擰在軍艦外板上,里面襯一些木頭,只安裝于水線上下的一點位置,全安裝護甲會讓軍艦負(fù)重太大影響航速。我們發(fā)現(xiàn)的這塊裝甲有一點的弧度,應(yīng)該位于主炮的位置,同樣的位置我們也發(fā)現(xiàn)了一塊帶著弧度的木質(zhì)甲板,其弧度與炮座吻合。”
用超過十年的時間去研究
“考古人常說一句話叫‘古不考三代以下(注:指以往考古人認(rèn)為發(fā)掘和研究的重點應(yīng)該在秦漢以前),但實際上時代的遠(yuǎn)近與考古對象的價值沒有關(guān)系,越晚近的東西有可能對我們現(xiàn)在的生活越重要、影響越大。不管從科技史、軍事史還是武器裝備史、艦船史的角度,深入了解甲午海戰(zhàn)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姜波看來,過去十年對于甲午沉艦的所有努力與收獲有著無比重要的意義,不僅事關(guān)考古學(xué)自身的探索,也有利于歷史學(xué)的發(fā)展:“某種程度上,它可以修正我們對歷史的認(rèn)知,也修正我們對歷史的研究方法。”

2020年9月17日,北洋海軍旗艦定遠(yuǎn)艦的一塊鐵甲在劉公島附近海域出水。圖/受訪者提供
而隨著2023年10月19日,國家文物局舉行“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甲午沉艦的實地調(diào)查也暫告了一個段落,所有抽沙清理的區(qū)域已全部進行回填處理,并采用特殊方法在艦體鋼板上加焊了鋅塊,延緩海水的腐蝕。接下來,對出水文物的修復(fù)和保護將成為一項重要工作。在海水里浸泡了百余年的文物,金屬類的必須進行復(fù)雜的脫鹽、除銹處理,木質(zhì)類的必須進行干燥,瓷器類的需要整形,如此才能保證其穩(wěn)定和健康。同時在修復(fù)和研究之后,這些文物才能參與各種形式的展出,實現(xiàn)面向公眾的宣傳、推廣與普及。
對于公眾而言,能否有機會親眼見證沉艦殘骸本身或許是許多人第一反應(yīng)所關(guān)心的。但目前來看,這樣的想法并沒有多少可行性。周春水說:“從技術(shù)角度講,打撈一艘沉船沉艦不是太難的事。主要的難點是,這么大體量的一個東西打撈起來放哪兒?而且很多(沉艦的)保存狀況,實際上不具備打撈的條件了。保護第一,不管是古代沉船還是近現(xiàn)代沉艦,首推的都是原址保護。”
姜波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原址保護是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2001年通過的《水下文化遺產(chǎn)保護公約》的第一原則,是全球范圍內(nèi)的共識。“海底文物在歷史長河里肯定會受到緩慢的腐蝕、氧化,還有生物的破壞。但超過了100年的文物,一般情況下已經(jīng)達(dá)到了一定的穩(wěn)定,特別是那些被淤泥覆蓋的部分,只要海洋環(huán)境、溫度、干濕度不變,應(yīng)該是可以保存下去的。”
除此之外,他認(rèn)為北洋沉艦還有一個獨特的地方:“它是海戰(zhàn)場,北洋海軍官兵的遺骸有它的神圣性,我們應(yīng)該把它作為一種紀(jì)念地來加以尊重,不要去驚擾它。考古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我們的好奇心,考古應(yīng)該是用科學(xué)的態(tài)度對待文物、對待遺產(chǎn)、對待歷史,在沒有能力處理的時候,最好的就是保存下來、傳承下去。”
2023年,作為北洋沉艦系列的第一個全面總結(jié),《致遠(yuǎn)艦水下考古調(diào)查報告》已正式出版。在七年時間里,編寫者以五個章節(jié)的結(jié)構(gòu)對現(xiàn)場調(diào)查及發(fā)現(xiàn)進行了詳細(xì)的梳理和解釋,為北洋海軍和甲午海戰(zhàn)的研究提供了一份寶貴的資料。未來五年,其他沉艦的考古報告將成為相關(guān)項目參與者的精力投放重點,據(jù)周春水介紹:“2024年,主要集中做定遠(yuǎn)艦的報告;然后到2025年或2026年,(爭取)把經(jīng)遠(yuǎn)艦的報告做出來;后面再用一兩年,做來遠(yuǎn)艦的報告。”
當(dāng)然,五年以后當(dāng)所有報告順利完成,也并不意味著圍繞北洋海軍沉艦的工作就畫上了句號。因為——“這十年的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非常豐富了,值得我們用超過十年的時間去研究它們。”周春水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參考資料:陳悅《中日甲午黃海大決戰(zhàn)》《北洋海軍艦船志》,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王家儉《李鴻章與北洋艦隊》

2019年9月2日,威海灣甲午沉艦遺址第一期調(diào)查項目考古隊員入海進行潛水作業(yè)。圖/新華

水下隊員在繪圖工作。圖/受訪者提供

2023年3月14日,山東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文物保護與利用實驗室的工作臺上整齊擺放數(shù)十件靖遠(yuǎn)艦出水文物,工作人員正用刻刀剔除一個船構(gòu)件表面的銹蝕物。圖/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