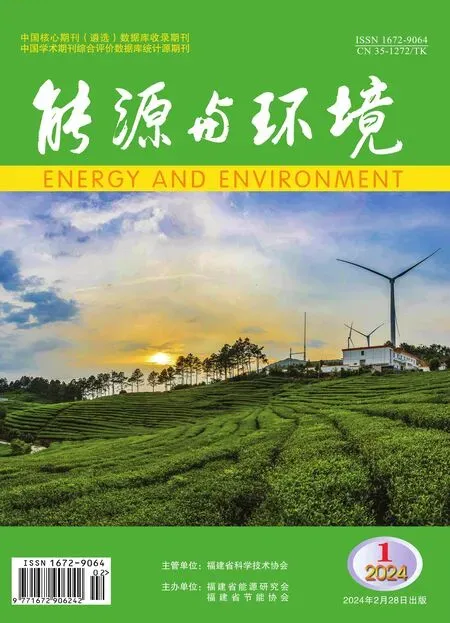某光伏電站發電量波動與偏離特性研究
劉彥鵬 張鵬 詹爽 梁國柱 劉志英 洪春雪
(1 大唐海南能源開發有限公司 海南海口 570100 2 大唐海南文昌新能源有限公司 海南文昌 571353 3 華北電力大學 北京 102206)
0 引言
2022 年全球能源碳排放量再創新高。在“雙碳”目標的引領下,作為清潔能源主力軍的光伏行業在我國獲得了飛速發展。自2005 年第1 座100 kWp 光伏電站成功并網至今,我國光伏累計裝機容量已超392.61 GW。光伏電站的設計和運行優化有利于提高光伏系統效率,保障光伏出力。
光伏發電效率受到多種因素制衡,如傾角、緯度、季節、天氣情況、輻照量、環境溫度、空氣濕度、風速等。宋啟軍等[1]采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篩選光伏發電功率影響因子,最終得出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總輻射量、日照時數、風速以及小時平均溫度。尤海俠[2]提出光伏電站地理位置、太陽輻射、組件間距、陰影遮擋、設備選型5 個因素均對光伏發電系統效率存在影響。魏晨晨等[3]以光伏組件為研究對象,結合光伏實驗臺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光伏組件的發電效率與輻照度成正比,與組件電池板溫度成反比,環境溫度的升高也會使得發電效率下降。其中,組件安裝傾角對光伏出力的影響達到3%~5%,眾多學者就傾角優化做出了研究。陳艷等[4]采用太陽輻射量及天空散射的各向異性模型,針對固定式光伏方陣計算最佳傾角,發現總輻射中水平面散射輻射的占比對最佳傾角存在影響,若采用固定式支架,北方地區最佳傾角較南方地區高。王建民等[5]在傳統計算方法的基礎上,綜合項目占地、基礎和支架的投資等因素,改進了光伏陣列最佳傾角計算方法。以上均為理論研究,實際運行過程中,設計值和實際發電量存在較大偏差。因此本文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探討實際發電量與理論值的偏差,能夠為此后同類地區的光伏電站優化調整提供理論支持。
1 研究方法
1.1 光伏電站簡介
某光伏電站位于北緯19.90°,東經110.82°。光伏規劃容量130 MWp,實際安裝240 772 塊光伏組件,共布置8 576~8 640 路光伏組串。1 路組串由28 塊組件串聯而成,經過電量表后接入1 臺逆變器,每臺逆變器接入17 路組串,組串間距為5 m。光伏組件為隆基LR5-72HBD540Wp 單晶硅雙面光伏組件,光電轉換效率為20.89%,陣列采用固定式支架。逆變器采用華為SUN2000-196KTL-H0 組串式逆變器,9 路MPPT 輸入。三維場景模擬見圖1。
1.2 軟件模擬
本項目模擬采用光伏系統設計輔助軟件PVsyst 進行。該軟件的計算原理是基于太陽輻射的變化規律以及太陽能電池板的物理特性,采用多種數學模型和算法來模擬光伏組件的發電效率和具體發電量。其中,入射采光面總的輻射量計算采用斜面輻射量理論模型(K-T 方法)[6]。該方法具體模型見式(1)~(3)。
式中:ρg為地面反射率;β 為陣列固定傾角為水平面月均散射輻射量為水平面月均總輻射量[6];D 按式(3)計算。
式中:ωss為斜面日落時角;ωsr為斜面日出時角;ωs為水平面日落時角[6]。
除入射采光面總的輻射量計算方法外,該軟件還利用多種太陽能電池板模型、電池板陣列模型、電池板性能模型等計算光伏陣列發電效率和發電量。
在軟件中創建站點并導入軟件內置的氣象數據,而后按照下文2.1 設置系統模擬工程實際。光伏陣列方位角取0°,朝向正南,固定傾角取8 個不同角度進行對照,分別為10°、11°、13°、14°、17°、18°、19°、20°。
1.3 現場記錄實際發電量
記錄1 路光伏組串每日發電量,同時設置日射強度計記錄當地輻照量。得到不同傾角光伏陣列實際運行數據后,將其折算成日利用小時數,與設計值進行對比分析。按照組件參數及陣列布置,折算公式見式(4)。
式中:T 為光伏陣列日利用小時數;W 為陣列日發電量。
為了反映實際值相對設計值的偏離情況,本文將現場數據與模擬數據的差值占模擬數據的比重定義為偏離度。偏離度定義見式(5)。
式中:σ 為偏離度;Wm為模擬數據;Ws為實際數據。
2 結果分析
2.1 發電模擬結果
不同固定傾角下17 路光伏組串的發電年利用小時數模擬值如圖2 所示,隨著傾角增大,發電年利用小時數先增后減。海南文昌固定傾角首年利用小時數參考值為1 255 h,軟件模擬結果與參考值接近。當光伏陣列傾角為10°時,年利用小時數為1 221.76 h;傾角增至14°時,年利用小時數增至1 232.01 h,較傾角10°工況增加0.84%;而傾角為18°時,年利用小時數最大,為1 243.80 h,較傾角10°工況增加1.80%。資料顯示,海南省三亞市最佳傾角參考值為17°,海口市最佳傾角參考值為14°[7]。這是因為根據經驗,最佳傾角受到緯度限制,一般在緯度±10°范圍內。但具體角度受當地具體氣象條件及地面條件影響,即使同一緯度地區,最佳傾角也可能存在差異。

圖2 不同傾角下光伏發電年利用小時數模擬值
18°傾角工況光伏發電逐月月利用小時數如圖3 所示。該工況下全年月利用小時數均值為103.65 h,各月月利用小時數差異較大。其中,1 月月利用小時數波動最大,較均值波動24.16%;3 月利用小時數波動最小,較均值波動4.36%。

圖3 18°傾角工況光伏發電月利用小時數模擬值
18°傾角工況下,光伏陣列總入射采光面輻射量如圖4 所示。該工況下月總入射采光面輻射量均值為436.60 MJ/m2,各月總入射采光面輻射量存在差異。其中,1 月總入射采光面輻射量波動最大,較均值波動25.81%;9 月總入射采光面輻射量波動最小,較均值波動4.97%。

圖4 18°傾角工況光伏月總入射采光面輻射量
對比圖3 和圖4,可見18°傾角工況下,光伏陣列逐月月利用小時數變化趨勢與月總入射采光面輻射量變化趨勢相同,且波動范圍近似。由此可知,光伏陣列逐月月利用小時數的波動主要是由于每日入射采光面輻射量的不同導致的,而二者不完全成正比是因為光伏出力在一定程度還受到組件運行溫度、空氣相對濕度、當日風速等因素影響。
2.2 實測數據分析
不同固定傾角下1 路光伏組串總利用小時數實測值如圖5 所示,當陣列傾角在10°~20°,總利用小時數實測平均值為978.96 h。陣列傾角為10°時,陣列年利用小時數最低,為951.12 h;當陣列傾角增大到18°時,陣列年利用小時數為998.70 h,較10°傾角工況增加4.76%。王輝等[8]認為理論上光伏組件的傾角越大,光伏出力越大,但應根據項目地理位置和現場情況綜合確定。史巨峰等[9]認為光伏陣列傾角變化,太陽入射角也會隨之變化,進而影響組件表面的輻射接收量。不同傾角下,光伏發電系統接收的太陽能輻射量不同,發電量不同。實際數據與以上研究結論吻合。

圖5 不同傾角下光伏發電年利用小時數
18°傾角工況下,每日對應日利用小時數如圖6 所示,日利用小時數波動率如圖7 所示。該工況下,年日利用小時數均值為2.77 h,每日日利用小時數存在不同程度波動,位于0.03%~86.64%之間,均值為20.68%。該工況每日日利用小時數模擬值的波動率介于0.01%~92.23%之間,引起此波動的主要原因是輻照條件的每日變化。

圖6 18°傾角工況光伏發電日利用小時數

圖7 18°傾角工況光伏發電日利用小時數波動率
2.3 偏離度分析
不同傾角月利用小時數模擬值與實際值對比及偏離度見圖8,不同傾角下各月模擬數據均大于實際數據,各傾角工況每月偏離度接近。不同傾角工況下,月利用小時數相差平均值為25.71 h,偏離度均值為23.11%。10°傾角工況下,3 月模擬值與實際值差值最小,相差15.92 h;4 月模擬值與實際值差值最大,相差53.68 h。18°傾角工況下,統計期內月利用小時數偏離度均值為20.56%,其中,除4 月外月利用小時數偏離度介于8.68%~23.83%,均<30%,在正常范圍內;4 月月利用小時數偏離度最大,為41.12%。據查,2023 年4 月,項目所在地多云20 d,降雨9 d,光照條件低于歷年平均水平,這可能是4 月光伏陣列月利用小時數較模擬數據偏差大的主要原因。其次,光伏組件表面積灰、設備運行穩定性、組件功率衰減等情況也可能對光伏出力產生一定程度影響。

圖8 不同傾角下光伏發電月利用小時偏離特性
3 結論
(1)隨著傾角增大,不同傾角發電年利用小時數模擬值先增后減。18°傾角工況下各月月利用小時數模擬值較均值有4.36%~41.34%的波動,主要與日輻照量的分布有關。
(2)當傾角分布在10°~20°,光伏組串實際利用小時數平均值為978.96 h。18°傾角工況下,發電日利用小時數實際值波動率介于0.03%~86.64%,均值為20.68%。
(3)光伏系統實際發電量與模擬發電量存在較大偏差。統計期內平均偏離度為23.11%。18°傾角工況下,除4 月外各月利用小時數偏離度介于8.68%~23.83%;4 月偏離度為41.12%,偏離度大的主要原因是光照條件低于歷年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