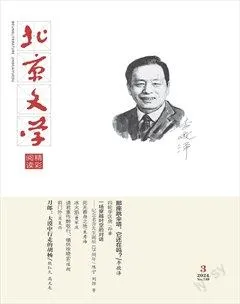賣蜂蜜的女人

一
人與人相遇是人生軌跡的一次交叉。
蕓和她的交叉點在蕓尚美容院。
蕓尚美容院正門是商業街,后窗是小景湖。湖邊有一小片樹林,以桂花樹居多,也有幾棵銀杏樹,緊挨著窗的是一株喜樹。喜樹是中國老百姓的樹,遍地生長,總能給普通人帶來幸運。蕓就是看到窗外的喜樹最終決定租這間店鋪。清晨和黃昏,總會有一些鳥兒在喜樹上鳴唱,讓蕓的心情歸零或者重啟。有時候喜樹上也會出現嘰嘰喳喳的麻雀,那肯定是要變天。蕓尚美容院不大,前半部分是美發,后半部分是美容護理。有六間房,一個單間,五個雙人間。接待客人的地方是小雅座,淡紫色的布藝沙發,茶幾上總會擺放一些水果和甜品,墻壁上是淡紫色的藝術瓷盤拼圖。蕓喜歡紫色,有夢幻般的浪漫。紫色的窗紗,紫色的吊燈,甚至床單也是淡紫色的細花,在舒緩的輕音樂中,恍如進入了一個夢幻的寓言世界,一地雞毛的生活永遠在門窗之外。
在客人不多的時候,蕓也會脫得光溜溜的,享受一下護理時光。當蕓脫得只剩下一個小內內的時候,她進來了。蕓沒說話,她也沒說話。蕓習慣性上床,趴下,大腿藏進被窩,雙肩和臀部就交給小米。小米用熱毛巾給她敷上,擦背,推油,按摩。蕓閉上眼,似睡非睡。
這時,她也上了床,只是,她話很多。“小美女,今天做什么護理呀?”小微答:“卵巢護理。”
小微和小米都是蕓尚美容院的一級美容師,○○后的姑娘。小米高挑秀氣,十指纖纖,輕柔舒展,擅長做臉部護理。小微胖嘟嘟的,手掌也是肉嘟嘟的,力道很到位,擅長身體護理。
卵巢不是在前面嗎?怎么給我搓背?她又問。
溫宮暖腎,先把背部搓熱,再給你腰部按摩,讓腎活起來,再撥經排毒。小微很有耐心。
這個套盒做下來,能治好我的婦科病?她又問。小微答,排除了體內宮寒濕氣,百病全消。
小微擰開精油瓶,滴在她背上說,姐,你皮膚真好,彈性很足,說明膠原蛋白很豐富。顧客都是上帝。蕓尚美容院有條規矩,都得喊姐,縱使女人年紀能當你奶奶,也要喊姐。一來叫姐親,二來叫姐叫得人年輕。凡來做美容的女人都是遇到年齡危機的女人。小微又說,姐,你經常做保養吧?那個女人說,要說保養,那還是喝蜂蜜,上美容院是頭一回。小微加大了手上力度說,蜂蜜,是好東西,美容養顏。
女人笑起來,我就是賣蜂蜜的,喝蜂蜜像吃大白菜。我家的蜂蜜都是原生態,沒添加劑,比市場價便宜。我的蜂蜜是直接銷售,沒有中間環節。女人很會推銷,甚至不放過短暫的護理時光。
別看小微人小,心機卻不少。當女人翻過來做正面時,她也趁機推銷,姐,你的乳房長得真漂亮,飽滿得像二十歲姑娘。呀!好像有點硬塊哦。小微推銷也是行內規矩,小題大做,讓顧客在驚慌失措時自覺掏錢做拓展項目。美容是一個永遠做不完的項目,就說乳房,挺拔的要讓它垂下,垂下的要讓它挺拔,這是一個無休止的循環。
小微用手捏捏她左邊的乳房,捏捏她右邊的乳房。又讓那女人自己捏,果然有硬塊。小微說,姐,硬塊暫時不會有感覺,等到痛起來,可能就是乳腺癌。女人嚇一跳,急忙追問,乳腺癌?又問,得了乳腺癌會怎樣?小微反而不急說,乳腺癌早期切除乳房,能保命,晚期癌細胞擴散,命就沒了。
單是說切掉乳房,就足以讓女人膽戰心驚,更別說丟命。女人怎么能沒有乳房,沒有乳房還是女人嗎?女人與女人不同的就是乳房,沒有乳房那不是要與男人絕緣嗎?女人顯得非常害怕,急切地問,美容院能做不?小微笑著說,姐別緊張,我們就能做。不但能把硬塊做沒了,還能讓姐的乳房更挺拔。姐遇到我很幸運,我心細,發現了硬塊。婦聯正在與我們店搞紅絲帶活動,原本一個套盒2999元,活動價只要1999元。女人急巴巴地說,好,就給我開這個套盒。
蕓聽到小微忽悠,想笑,但當她側過臉看到女人的乳房,卻沒笑出來。女人的乳房真的很美,像剛成熟的大蜜桃,乳暈還仍然是玫瑰紅。女人的身材也是百里挑一,腰纖細光滑,肚臍微微內陷,腹部微微隆起,小內內很低,是鏤空的蕾絲花邊,哪怕是對女人都很有誘惑力。女人欣賞女人,目光都是很毒辣的。面對如此完美的胴體,蕓突然想豪邁一回,忍不住給小微發微信,紅絲帶套盒在活動價基礎上,再打七折。別告訴她,我是老板。為這樣的美女掏腰包,不只男人喜歡,女人也喜歡。但她不想在這個時候,暴露她是老板。蕓也說不清楚這是為什么,也許是突然來的小情緒。蕓總是喜歡把莫名其妙的想法歸結為小情緒。
蕓是安徽姑娘,認識了當兵的宋嘉。宋嘉退伍把她帶回了老家。蕓性格文靜,剛到婆家,人生地不熟,就更加不說話。后來,生下兒女,日子過得捉襟見肘,每次問宋嘉要錢時,宋嘉都是拉長著臉。蕓好傷心,就去美容院打工。做美容師首要技術好,還要口才好,才能賣得出產品。美容院是個大熔爐,沒過多久就把蕓鍛造成了一個優秀產品。蕓變得伶牙俐齒,八面玲瓏。蕓的名聲做起來了,就自己開了這家蕓尚美容院。
蕓第二次見到她,是在鑫冠蛋糕店。
雨,剛起時,如霧絲,吹到臉上,涼絲絲的。在漫不經心時,又突然變成雨珠子,滴答滴答,打下來。緊接著是雨的大部隊,急急如律令,唰唰唰,飛馳而來。經過變奏的雨漸漸變成了長腳雨,一時半會兒還停不下來。蕓叮囑姑娘們關店修整,她拿車鑰匙出了門。
一個男人在吼,滾,瘋婆子!
一個女人也在吼,婊子生的東西,想賴賬?
男人繼續吼,賣假貨還想要錢?我舉報你!
女人手舞足蹈,來呀,有種舉報呀!
男人端起一盆水,直接潑向女人。女人氣瘋了,抓起柜臺上的蛋糕就摔。柜臺后躥出一個姑娘,二話不說,掄起巴掌扇女人。姑娘毫不留情,一巴掌就是一道血紅的手印,邊扇還邊罵,不要臉的安徽婆,看姑奶奶怎么收拾你!
女人就是蕓尚美容院的她,登記的名字叫慧慧。慧慧此時的形象與蕓尚美容院的形象完全不同,一個是淑女,一個是潑婦。安徽婆?她也是安徽來的女人?蕓本來沒打算管,但安徽婆三個字刺痛了她。安徽是緊挨著江南的一塊中原大地,安徽的女人有江南女人的玲瓏秀美,什么時候成了“安徽婆”?蕓猛地推開玻璃門,冷冷地說,陳竹生,學會欺負女人了。陳竹生是鑫冠蛋糕店老板,蕓跟他很熟。
慧慧披頭散發,手上、臉上都是血。蕓把蹲在地上的慧慧扶起來,走,去醫院。
二
慧慧的蜂蜜店是一個沒有招牌的小店。店門口擺了一張小桌子,桌子上有大大小小的玻璃罐,罐子中間插了一個紙牌,歪歪扭扭寫著:正宗蜂蜜。難道這就叫“正宗”?這些年,很多產品賣的就是包裝。突然有一天,人說漂亮的包裝里是假貨或者毒貨,弄得人神經兮兮。倒是粗俗簡陋的包裝讓人放心。這種包裝和擺放也太對不起正宗蜂蜜了。蕓估摸著沒有走錯,站在門口朝里喊,有人嗎?買蜂蜜。話音落了半天,也沒有回音。旁邊小吃店有個姑娘探過頭來,找安徽婆?她在那邊打牌,我去喊她。
蜂蜜店不足二十平方。膠板把店鋪前后一分為二,后面是臥室兼廚房。說是廚房,其實也算不上,只是在煤氣罐上面擱了塊木板,板上放煤氣灶,灶上有個黑漆漆的鐵鍋。煤氣罐旁邊是個有蓋的紅色塑料桶,桶蓋上面有一碗干辣椒爆肉、一碟霉豆腐,還有幾只嗡嗡叫的蒼蠅。誰買蜂蜜呀?有點熟悉的聲音,是慧慧。蕓收回眼神。哎喲,蕓妹妹來了!坐,坐,坐。慧慧尖著嗓子,攤開雙手,動作有些夸張。蕓環顧四周,不知道坐哪兒。坐,坐,坐。慧慧繼續招呼。蕓笑,讓我坐哪兒?慧慧顯得有些尷尬,臉上泛紅說,坐床上你不介意吧?
瑤里是湖區,人口多,經濟比她安徽老家還落后,但這里的人彪悍,對外地人多少有些排擠。蕓來了十年,深有感觸。自從知道慧慧是同鄉,沒計較她是賣蜂蜜的,莫名其妙就想親近她。在鑫冠蛋糕店也是莫名其妙就幫了她,逼著老板陳竹生答應還蜂蜜貨款,還出了一筆醫藥費。
慧慧總是大大咧咧,與她的容貌和身材一點都不相稱。如果她睡過哪個男人,蕓都擔心她不經意就說了出來。她似乎忘了上次臉上的傷痕,臉上的皮膚生命力也極強,才過了幾天就看不見一點痕跡,該不會又是蜂蜜的奇特功效吧。慧慧從床底下摸出一個紙杯,倒上一杯水,再舀了一大勺蜂蜜,遞給蕓。蜂蜜很純正,蕓能聞到一股天然的香味,估計很好喝。但蕓看看這環境,卻沒了喝蜂蜜的欲望。蕓突然后悔來看她。慧慧就是一個簡單的女人,在她的天空里只有兩團云,白云和烏云。白云飄來,就是晴天。烏云壓頂,或許就是雷電交加。她認識問題也很簡單,不是對就是錯。跟這樣簡陋而又簡單的老鄉相處,不知是對是錯。蕓也有她的弱點,就是優柔寡斷。明知道慧慧是一個不靠譜的老鄉,來了還不好意思離開。
慧慧拉著蕓,坐在床邊,聊了蜂蜜又聊安徽,聊了安徽又聊自己,整個二十平方的空間里,就只有慧慧的聲音,蕓最多是點點頭。蕓每次點頭又牽出了慧慧更多的話。
此時慧慧臉上飄來的是烏云,沒有雷電交加,卻是淅淅瀝瀝。慧慧的前半段經歷是一個錯,后半段也不見得就對。第一個錯是選擇錯了父母。父母之所以錯是因為窮。如果不是窮得無路可走,誰也不愿意背井離鄉,來瑤里討口飯吃。她有三個哥哥、三個姐姐,還有一個妹妹。娘就像一頭母豬,一共生了十一個,夭折了三個。安徽老家三年兩頭發大水,中間一年還歉收,交了國庫,家里就空了。每到飯熟時,父親就靠著鍋臺,指使著母親盛飯。夠了,都快大半碗了,死丫頭遲早是別人家的,不餓死就夠了。這是給三個姐姐盛飯。老大,裝滿,老二,管飽。父親嗓門很大,說話毫無忌諱。姊妹五個不但不敢與父親爭辯,還哆哆嗦嗦,灶臺都不敢靠近,等到三個哥哥端著飯碗走開了,才畏畏縮縮端自己的飯碗。
二哥唯獨鐘情于慧慧。見慧慧飯碗空了,就遞眼色。兩人便很默契地來到樅樹底下,二哥把碗里的飯劃拉給慧慧,還問,夠不?慧慧看著二哥的空碗說,不夠你也沒了。那年齡正是長個子的時候,大哥三哥一年一個樣,唯獨二哥年年翻燒餅,個頭長不上去。五姊妹也唯獨慧慧越長越水靈。按說父親看到慧慧長得水靈應該高興,可是不,父親只要遇到不順心就拿慧慧撒氣。長得好看有個屁用?這個家遲早要敗在你這個狐媚手里。慧慧并不知道狐媚是啥意思,但父親巴掌實實在在落在頭上,疼痛讓她明白了一件事,父親討厭她。她甚至懷疑自己不是父親生的。可是,母親也是動不動就打她,還罵:我賤,一口氣生了五個賠錢貨。你比我還賤,就是一禍害。慧慧一直不知道她為什么比娘還賤,又為什么是一個禍害。
大姐十六歲就出嫁了,嫁給了鄰村的大傻,大傻是大嫂的大哥。大嫂是大姐換親換來的。大嫂還有一個傻子哥哥,叫二傻。大嫂曾攛掇把慧慧嫁給二傻。娘沒同意。大嫂家里人的腦子都長到她一個人身上,自己聰明就認為別人都是傻子。一個換一個不夠,還想換倆?娘不同意還有一個原因,二哥快三十歲,還沒娶上媳婦,娘著急,就想拿慧慧去換親。給二哥換親,慧慧沒抵觸,這個家也只有二哥對她好,她在這個家也待膩了。既然女人都得嫁人,遲嫁不如早嫁,她甚至對換親還有一絲憧憬。
命運神秘之處就是經常不按人設計的軌跡走,而是在意想不到的時候出現意想不到的變數。慧慧長到二十三歲時,還沒成人,就是沒見紅。沒見紅的女人就不算女人,鄉下人稱石女。如果是石女,哪怕是長得再好,倒貼給婆家,也不會有人要。母親的設計落空了。母親惱羞成怒,進門罵慧慧是石女,出門也罵慧慧是石女。家丑不可外揚,本來這事做娘的該藏著,這樣滿世界張揚,將置慧慧一生幸福于何地?可見母親是多么恨慧慧。父母愛一個子女沒理由,恨一個子女也不需要理由。娘都喊石女,家里人也跟著叫石女,村里男女老少都喊石女,石女成了慧慧沒出閣前又一個名字。慧慧成了石女,意味著家里要養一個老處女,誰受得了。一天,父親醉酒回家拿馬鞭抽慧慧,慧慧一動不動讓他抽,父親來氣了,不怕疼不是?父親扒光了慧慧的衣服,又狠命地抽。慧慧仍然是一動不動,目光里有一種決絕。二哥心疼慧慧,梗著脖子,瞪著血紅的眼睛,奪過父親的馬鞭,咯嘣一下,折斷了馬鞭。父親惱羞成怒,操起扁擔,追著二哥打。父親跑得急,摔了個嘴啃泥。母親心疼父親,也躺在地上號啕大哭,這是造了什么孽,不都是為你老二嗎?老二如何能下得了狠心啊!二哥邊跑邊應,不娶老婆不死人,再打就要死人了。慧慧的決絕讓二哥無意間拉了回來。慧慧想,為了二哥,她也不能死。二哥找不到老婆,她便陪二哥一輩子。
蕓聽累了,很想結束這凄苦卻并不精彩的故事,便問,二哥后來娶上老婆了嗎?
這時,慧慧的電話響了。她臉上剛才還是愁云慘淡,突然便變得春風滿面。這個女人真的很善變。慧慧完全忘了蕓的提問,努努嘴說,不好意思,接個電話。又對電話說,好的,好的,十分鐘就過去。她擦干淚痕,臉上燦開了一朵花。
慧慧猛然捶了蕓一拳,哈哈,討了三年的債,陳竹生總算答應給錢了,都是你的功勞。陳竹生就是一個畜生,先是甜言蜜語要蜂蜜,給了蜂蜜又沒錢了。他也不是沒錢,就想睡我。給了錢睡我也沒啥,偏要先睡再給錢。慧慧擼擼頭發,在枕頭底下摸出一個亮晶晶的發夾夾上,又貓著腰,在床底下撈出一雙高跟涼鞋換上。
逆光照在她苗條的身上,像水蛇一般好看。蕓有點發呆。這是一個什么樣的女人?
三
蕓在瑤里也沒什么朋友,與慧慧一來二去,居然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生意清淡時便混在一起,不是閨蜜,勝似閨蜜。慧慧正應了那句“胸大無腦”,哪怕是聊她的性生活史都面不改色,倒把蕓弄得霞光滿天。
雨真是多,從四月初八下到了七月十八,好像沒歇趟兒,一場接著一場。慧慧掰著手指頭數,一百天內就晴了三回。今天是第三回出太陽。七月的太陽像火在燒,大地就像蒸籠,不僅熱,人還像在蒸汽里。下雨天,生意不好做,這大蒸籠的天,生意更不好做。好幾天沒開張,再這樣下去,怕是這個月店租都交不上了。日頭西下時,慧慧搬了個板凳,坐到店門外。汗珠子濕透了文胸,黏稠稠的。脫掉,她換了件吊帶裙,把頭發在后面綰個結。吊帶裙有點低,只要略微低下頭,就能見深深的乳溝。她吸了口氣,有點傲嬌,不用文胸,乳房仍然堅挺飽滿。小微說她乳房里有硬塊,是不是硬塊讓她乳房堅挺?如果把硬塊做掉了,會不會癟下去?如果真的會癟下去,她寧愿要硬塊。這些硬塊對她沒有什么影響,最多是來例假前幾天,會脹得有點痛。痛只有自己知道,好看人人都知道。花兒好看,蜜蜂來了。她的乳房好看,生意就來了。她有些后悔聽小微胡說八道,硬塊就一定變成癌?為什么還有那么多挺拔的乳房?她去山里放蜂時,認識了很多花,槐花、紫藤花、山蘭花、野薔薇、海棠花、朱砂梅……她在手機上看到一種罌粟花,自言自語,活成罌粟花也沒什么不好。這時,蕓來了。
慧慧拿了兩支雪糕,一支遞給蕓,一支正要往嘴里送,一個男人又出現了。男人夾了個黑包,穿了雙黑皮鞋,頭發梳得油光發亮,藏青色的長褲,一根黑色皮帶把白色T恤管得服服帖帖。五顏六色看多了,還是黑白耐看。看裝束,不是老板,也是官員。慧慧快速吞下雪糕,生意來了。
賣蜂蜜?正宗蜂蜜。大山深處,原生態的,不摻假。蜂蜜甜不?甜,甜到心坎上。慧慧覺得這個男人傻得可愛,蜂蜜不甜,還叫蜂蜜嗎?是你嘴巴甜吧?男人微笑著,身子頂靠了她的屁股,一股熱流燙得她說不出話來。給我送一百斤甜到心坎上的蜂蜜到這里。男人在一張紙條上寫下地址。紙條上除了地址,還有名字。你叫陳明?叫我陳哥。陳明數了錢說,不用找了,明天送來。慧慧莫名其妙臉紅了。蕓想,這小蹄子還有臉紅的時候?
蕓說,這小子不懷好意。
慧慧笑,誰怕誰呀!
蕓搖搖頭,這小蹄子是不是走火入魔了?是該離她遠些,別引火燒身。蕓找了一個借口,離開了。
沒過幾天,慧慧來做套盒,又纏上了蕓,居然只是為了告訴蕓她與陳明之間剛發生的故事。理智告訴蕓,不要去聽,好奇心又讓蕓保持了沉默。
慧慧與陳明一個有情,一個有意,走到一起是水到渠成的事。陳明對蜂蜜的了解比她還多。陳明是一個有心計的男人,先從蜂蜜含有與人體血清濃度相同的多種無機鹽和維生素說起。你不是說你是吃蜂蜜才變得這樣漂亮嗎?我告訴你,這是真的。慧慧羞澀地笑了笑說,什么真的假的,甜到心坎上才是真的。陳明也笑,是誰甜到心坎上了?慧慧佯裝發怒,蜜也吃了,人也嘗了,還不是你?陳明說,你不甜到心坎上,怎么知道我甜到心坎上?一陣打鬧過后,又是一次暴風驟雨。雨過天晴之后,陳明又說,蜂蜜還有一個好處,你猜猜?慧慧有些疲倦說,懶得猜。陳明說,蜂蜜能治相思病。慧慧瞪大了眼睛。陳明翻身起床,把蜂蜜倒入精油中,又和著搗碎了的玫瑰花瓣調勻,再倒入掌心,涂抹在她身上。蜂蜜精油隨著陳明的手掌在她身上每一個部位游走。陳明咬著她的耳垂問,相思嗎?她閉上眼,不敢吭聲,害怕自己控制不住身體的戰栗。突然,陳明俯下身,用舌尖去舔她身上的蜂蜜花瓣,那舌頭就像蜂針在刺,她再也無法控制自己,把陳明推倒在床上。這哪是治相思,是要她的命。從那以后,慧慧徹底為陳明瘋狂了。陳明也很會哄她,隔三岔五地給她發微信紅包,情人節那天,還送她玉手鐲。
陳明也是賣蜂蜜的。慧慧送來的蜂蜜,陳明都要進行“加工”,裝進各種漂亮的包裝里,貼上不同的標簽,做成滋補品、美容品,甚至藥品,身價陡增。陳明的蜂蜜甜,但到不了心坎上。慧慧自從甜到了心坎上,再也懶得說原生態了。不過,她有時也逗陳明,你這是造假。陳明說,蜂蜜是假的嗎?
慧慧說,當然不是,蜂蜜是原生態的。陳明說,蜂蜜不假,怎么是造假?慧慧自詡話多,遇到陳明就沒話了,但慧慧隱約感到陳明能耐很大,沒他辦不成的事。或許……慧慧想起一件事,或許能指望他。
蕓突然覺得索然無味,“故事”沒聽完就借故走開了。
四
一段時間,如果不是小微打電話,慧慧幾乎忘了蕓尚美容院。她的乳房因為經常有陳明“按摩”,沒了腫脹的感覺,自然也忘了硬塊的事。蕓因為心里有陳明這塊疙瘩不愿意去招惹慧慧,也漸漸淡忘了慧慧。
小微的電話讓慧慧想起了蕓。她帶了一罐棗花蜜、一罐姜花蜜給蕓。不過已算不上正宗,是陳明加工的蜜,外包裝很漂亮。蕓是一個講究的人,她很喜歡蕓。如果蕓是男人,也許她會毫不猶豫纏上蕓。蕓身上有一種東西,她想靠近,又不敢靠近。二哥身上也有這種東西,她敢靠近,但二哥是親兄弟。
她在淡淡的紫色光影下,脫得光溜溜的,站在穿衣鏡前,全身肌膚白如凝脂,肚皮上的妊娠紋這些年似乎都不見了,臉上的斑紋也慢慢淡去了。陳明說是他相思蜜的功勞,她總覺得哪兒不對。不過,她現在最幸福的時光就是陳明在她身上抹相思蜜,又去舔相思蜜,其他都不重要了。她側過身來,突然像見了鬼般地驚叫起來,小微,你瞧,我腰上長膘了,是不是變成豬了?小微笑,變成豬也是一只寵物豬。慧慧說,說正經的,聽說扎針能把肉里的脂肪抽出來?
蕓推門進來,打趣她,抽啥脂肪呀,做我的寵物豬,我天天抱著你睡。
慧慧說,真的嗎?那我就不回豬窩了,做妹妹的寵物豬。
蕓說,別,哪有一個女人抱著一頭母豬睡覺的道理。
慧慧說,妹妹想抱公豬,找姐呀。
又是一陣打鬧。蕓或許是為了感謝慧慧送蜜,又或許是有抱寵物豬的沖動,留慧慧吃了晚飯,還留她住下了。慧慧在店里是一身行頭,出門又是一身行頭,那身打扮和一個高貴女人應有的氣息一點都不比蕓差。盡管如此,蕓還是沒有抱著慧慧睡的念頭。兩人躺著聊天,倒是聊得很晚。
慧慧說,妹妹不是問二哥娶老婆沒嗎?娶了。家里賣了我,娶了二嫂。
話頭從二哥開始。
那年入冬得早,雪下了七天七夜,好多棉花都凍在地頭,還沒來得及摘。偏在這時,村里來了一個彈棉花的。彈棉花啰,彈蓋絮、墊絮、搖籮絮,大絮、小絮、娃娃絮,彈——棉——花——啰!彈棉花的湖北腔從村頭拖到村尾。慧慧端了一盆水往灘場上倒,看到了一個背影從眼前走過。一張弓異常大,似乎有兩個背影一樣長,弓上綁了個棒槌,還掛了個圓木板。仔細看,不是弓大,是那人著實矮小。
背影進了村東頭粉頭家。咚、咣、咣,咚、咣、咣,彈棉花的聲音在粉頭家響了兩天,又在慧慧屋后絲瓜叔家響了三天。慧慧沒事就去看彈棉花。咚、咣、咣,咚、咣、咣,不管是地里剛撿來泛黃的棉花,還是發黑的舊棉絮,經這矬子一彈,棉花比外面的雪還白。矬子彈出來的棉絮不但有模有樣,還能用紅線在棉絮上擺弄出好看的花紋。慧慧不明白,一個又黑又矮的人,怎么就彈出了這么美妙能蓋住無數夢想的棉絮。慧慧在看棉絮,彈棉花的也在看她。
慧慧是石女,名聲在村里早已臭了,彈棉花的偏偏看上了她。彈棉花的沒有姐妹,換不成親。父母說,沒姐妹,有錢也行。慧慧就是380塊錢讓父母給賣了。慧慧一直期待著為二哥換一門親,沒想到換來的是一個一睡覺就做噩夢的男人。不去,死也不去。母親把房門拍得咚咚響,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父親說,想死?我就把你的尸體嫁過去。慧慧沒力氣再恨父母,便恨上了彈棉花的。你不讓我好好過,嫁過去了我讓你一家人都不能好好活。想通了這一層,慧慧走出了房門,該吃的吃,該喝的喝。父母拿了380塊錢,給二哥定了一門親。
結婚的那個晚上,矬子喝了很多酒,上床便睡得像一頭死豬。慧慧坐在床沿上,不敢上床。昏暗的燭光照在一張又黑又木訥的臉上,讓她渾身起雞皮疙瘩。這輩子就抱著這樣的男人睡?豈不是半輩子要做噩夢?自己雖說是石女,論長相不是萬里挑一也是千里挑一。自己已經為二哥活過一回,不能再為這樣的男人活了!想到下半夜,一個罪惡的念頭突然從心里冒出來,我要燒死他,對,燒死他,也燒死自己。罪惡的念頭像春天的野草一樣瘋長,去死吧!她站起來,腳盡管有些發抖,手也有些哆嗦,但念頭卻無比決絕。她拿起紅燭,點燃了蚊帳。火,呼啦啦躥上了房頂。她坐在床沿上一動不動,等待死神降臨。
矬子很快被驚醒,大聲喊,著火了,著火了!順勢抱起慧慧沖出了洞房。火也很快被村里人撲滅了。這是一次失敗的毀滅。矬子家也是窮苦出身,大火過后,家里越發艱難。家里盡管沒有一個人提起火的原因,但一雙雙仇視的目光時刻在刺痛慧慧。慧慧也想,是不是做過頭了?解救不幸不一定要用毀滅,只是自己還沒有想到更好的辦法。
三個月,整整三個月,慧慧都是熬著盡量不睡,即使熬不住,也是等矬子睡熟了,才偷偷閉一會兒眼。可那次真是該死,沒熬住,先矬子入睡了,并且睡得很死。該死的矬子居然等她熟睡后,用剪刀剪開了慧慧的褲頭,再把她手腳綁在床柱子上。慧慧讓撕心裂肺的疼痛驚醒,大聲哭喊,卻什么都不能改變。房間外還隱隱約約傳來罵聲,你以為是誰?是菩薩,要在家里供著?賤貨,叫著不走,打著倒退。她就拼命咬他。那次之后,慧慧在枕頭底下藏了一把刀,但矬子一直沒碰過她。一個月后,慧慧居然來了第一次潮紅。她不是石女,籠罩在她頭上二十多年的魔咒終于解除了。慧慧與矬子之間的對抗經不住時間的折磨,以慧慧放棄而告終。
風把雨帶來了,窗紗拂到了臉上,有一絲涼意,是秋天了。銀杏樹葉黃了,吹到水面,無助地打著轉轉。喜樹也結子了,一簇一簇,掛滿了枝頭。蕓輕輕地拍打著慧慧的肩膀說,都過去了,苦難是自己想出來的,多想想矬子的好,苦難就隨風而去。慧慧捏了捏蕓的臉說,妹妹沒有身臨其境,不知道苦是啥滋味。苦就是苦。蕓說,苦是越想越苦,越想越沒盡頭。慧慧笑,臉上還泛著淡淡的紅暈,妹妹還是少了一份閱歷,要想不苦,就得用甜把苦壓住。
蕓似懂非懂,看她一臉幸福的樣子,這個女人紅暈的樣子下面隱藏著什么秘密?
五
慧慧繼續講述她苦與甜的“哲理”。
慧慧說,一個人睡覺,特別容易失眠。蕓問,為啥?慧慧說,或許是用甜壓住的苦,經常會從腸胃里反芻,半夜里酸水涌到口里,睡意就跑了。蕓說,你可能有胃病,做個胃鏡。慧慧說,做過,一切正常。蕓說,或許是膽汁反流?慧慧說,都不是,或許是苦太強大了,甜壓不住。蕓憐惜地摸摸慧慧的臉說,真是個苦命的冤家。慧慧笑,睡不著也沒什么,就是累。
慧慧繼續訴“苦”。
矬子說彈棉花不賺錢了,現在的人都睡太空棉或者蠶絲被。慧慧問他想干啥,矬子說養蜂賣蜜,蜜能換錢,還能美容。慧慧對養蜂不感興趣,對美容感興趣。矬子沒一句話能說到慧慧的心坎上,所以她心里哪怕有一百句話,也只愿當一句說。對于養蜂,她想的是與其天天這樣要死不活宅在家里,不如像蜜蜂一樣追著花兒跑。一對冤家難得第一次意見一致。矬子能吃苦,在山里風餐露宿,割了蜜,又走村串戶去賣蜂蜜。賣來的錢還一分不少交給慧慧。慧慧什么事不做還嫌悶得慌,隔三岔五便跑得不見蹤影。后來,積了一點小錢,她就進城盤了個店。再后來,聽說有人便宜賣店鋪,她動了心。租店要月月交租金,如果把店鋪買下來,生意好,就賣蜂蜜,生意不好,就租給別人,包賺不虧。帶慧慧買店鋪的人是她的一個相好。和他相好,也是因為想買店鋪。慧慧想的和做的一樣簡單,我對你好,你就肯定會對我好,我把我交給你,你就該把你交給我。可是這個相好卻不這樣想。相好的接了慧慧買店鋪的十萬預付款后想,吃你N次和一次味道是一樣的。錢什么味道不能買?相好的給她玩人間蒸發,把她的微信和手機都拉進了黑名單。慧慧恨得牙根癢癢。她想掘地三尺,但她的地有多大?和陳明好,或許是一次機會。陳明的地比她的地大多了。
蕓實在是困了,嘆了口氣說,睡吧,陳明的地是陳明的地,你的地是你的地,別人家的地沒沾邊,自己的地讓人家占了。
人在無意識之下說的話往往一語成讖。
第三天,蕓便接到了慧慧的哭訴電話。慧慧從蕓尚美容院出來,就去找陳明。她想把這件事挑明,讓他幫忙找人要錢。她來到陳明的造假工廠,陳明不在。她一直等到晚上,陳明也沒有回來。第二天,她又去,陳明仍不見蹤影。給他打電話,手機嘟了一下,就說正在通話中。陳明也在玩失蹤?不可能呀,生意做得好好的,上個星期,還提過來二十斤蜂蜜呢。欠債嗎?似乎也不可能,每次見他錢包都是鼓鼓囊囊的。不會這么倒霉吧?剛抓住一個男人又飛了?她想哭。陳明口口聲聲說要給她一個安樂窩。窩呢?就是廠里這窩,床、衣柜、沙發、廚房的鍋碗瓢盆還是她一樣一樣搬來的。人呢,咋就不見了?慧慧越哭越傷心。傷心時,想起了蕓。她在電話里喊,妹妹,我的苦是想出來的嗎?蕓莫名其妙問,什么苦?慧慧說,來了就知道了。
蕓費了很大周折才找到慧慧。她坐在地上,又哭又笑,像個瘋子。房間里滿地狼藉,沙發上、桌上都是打碎的瓶瓶罐罐,床上的被子撕得稀巴爛。蕓嚇了一跳,你這是遭搶劫了?
不是,我砸的,我恨。
恨誰?
陳明。
他怎么了?
失蹤了,他媽的,又一個玩失蹤的,嗚嗚嗚。
蕓無語了。這個老鄉到底有幾個相好?冷不丁就蹦出一個來。蕓腦子里一次次發出警告,離這個老鄉遠點,但遇到這樣的事她又哪能挪得開步?
慧慧情緒穩定下來后,又講起了她的“苦難史”。蕓還不得不聽。蕓無法預料她會做出什么驚天動地的事來。
那年,二哥跟慧慧同時結婚。慧慧懷上了第二個孩子,嫂子還沒開懷。后來做檢查,嫂子沒有生育能力。父母又來求慧慧,要她把兩歲的女兒讓給二哥。慧慧向來對二哥的事有求必應。她跟矬子吵了幾場架,才把女兒送過去。女兒八歲那年,母親去二哥家,正巧碰上二嫂打女兒。母親罵二嫂,自己不下蛋,打別人的孩子不心疼。母親也是一個暴躁性格,硬是把孫女領回還給了慧慧。女兒已經長得水靈靈的,慧慧像撿了個寶一樣,就希望女兒有出息,不走自己的老路。女兒不肯去學校,她就打。女兒考得差,她也打。女兒不聽話,她更是打。女兒讀到初二,死活不去學校,說要出去打工。那性格是又一個慧慧。慧慧心里的火噌噌往上躥,操起門角里的掃把,沒頭沒臉地打女兒。矬子看到慧慧打女兒,也操起門角里的鋤頭棍,劈頭蓋臉地打慧慧。矬子一般不發火,真要發了火,誰都攔不住。那次他把慧慧的眼睛打腫了,臉也打腫了,肚子也腫了起來,尿都撒不出來。等矬子火氣消了,就像變了個人,先是把自己打得鼻青臉腫,又跪著求慧慧上醫院。女兒就是趁慧慧住院時,一個人去了上海。女兒的運氣比慧慧好上不止一萬倍。她被一個大老板相中。跟著老板,她也愿意讀書,而且是去美國讀書。據說,女兒現在的日子過得比以前的皇妃還好。女兒時常給她奶奶打電話,但從來不說她是怎么過日子。奶奶問,娟,過得好嗎?娟說,好。奶奶又問,怎么個好法?娟說,好就是好。奶奶仍不放心說,沒騙奶奶吧?難過就回來,金窩銀窩不如家里的狗窩。娟有些不耐煩說,什么年代?放心吧。又說,家里缺錢就開口。可是奶奶從來不開口。慧慧想開口,女兒又不給她機會。以前,娟也給爹打電話,可是爹沒說兩句,電話就讓慧慧搶去了。后來,娟便不再給爹打電話,只給奶奶打。有一回,娟又打電話給奶奶,盡聊些雞毛蒜皮的事,慧慧聽得心里火辣辣的,忍不住搶過奶奶的電話說,娟秀,我是姆媽。對面把電話掛了。慧慧又撥過去,電話接通了。娟說,奶奶還有話說?慧慧說,我不是奶奶,是姆媽。娟說,我沒姆媽。慧慧罵,你是樹洞里鉆出來的?娟說,以前我有姆媽,后來在一場大火中變成了惡魔,惡魔經常揮舞著掃把,還是姆媽嗎?慧慧又罵,那不是為了你嗎?對面把電話掛了。慧慧抱著電話哭,娟秀,你就這樣恨姆媽?慧慧從此不再搶電話,她知道女兒已經死了,她也知道這些都是奶奶教的,奶奶不教,女兒不可能知道火燒洞房的事。由此,她恨娟秀的奶奶,也開始恨矬子。因為恨,她已無所顧忌。
慧慧跟矬子沒感情,最初是因為矬子長得丑,其實丑不是關鍵。人跟人處久了,有了感情,也無所謂美丑。后來是因為矬子花了380塊錢買了她,但這錢畢竟用在二哥身上,想通了,也不是事。火燒洞房之后,慧慧跟矬子生下一兒一女,也就認命了。盡管矬子肚皮上長滿了牛皮癬,黏糊糊的,還有一股腥臭味,肚皮貼著肚皮時,慧慧閉著眼睛,捏著鼻子,忍一忍也過來了。女兒已經讓奶奶教成這樣,兒子雖然小,見了她也像見了鬼一樣,她無法忍受。
蕓突然想見見這個奇丑無比的男人,問慧慧,矬子在哪兒養蜂?
慧慧說,陽儲山里。
六
出城往北,不出十里地,就是陽儲山。
深秋的山像一個久經滄桑的女人,比春天更加五彩斑斕。風從山澗里吹過來,有點寒意。蜂場就在山腳下,一個黑色牛皮氈棚子,一排一排的黑色箱子,一個戴著黑色面罩的矬子在蜂群中揮舞著,像在跳芭蕾舞。蕓怕蜜蜂蜇,遠遠喊,你是帥樹明嗎?那個人好像沒聽見,繼續揮舞著。蕓又大聲喊,帥樹明!那人停下手中的活,往這邊走來。
你是誰?買蜂蜜?
我是王慧慧的朋友。
王慧慧呢?
男人往蕓后面張望著。慧慧的男人的確有些笨拙,尤其是在漂亮女人面前,更顯得不知所措,連最基本招呼人的禮節都省略了。
慧慧說家里蜂場在這兒。我順路來看看。
哦!
我就知道她不會來。她再也不會來這鬼地方!
你想她來?
當然。
她心里其實也挺苦的。
她是個好女人。
男人雖然有點失望,眼里卻有一絲光亮在流動。
那你家里為什么逼得她與子女形同仇人?
不是的。我娘有點糊涂,我沒少說娘。
話聊著聊著便放開了。帥樹明其實在慧慧和兒女之間已經做了很多工作,甚至用斷絕父女關系威脅女兒。兒女現在都喊慧慧媽媽,只是沒更多的話說。慧慧講述她與兒女的關系時,明顯有夸張的成分。慧慧為什么要夸大她與子女的惡劣關系?蕓很疑惑,該不是為自己的放蕩找理由吧?
蕓問,慧慧是你花380元錢買來的?
帥樹明有點局促不安,不是,不是這樣。380塊錢是看禮錢,她村里有規矩,不算買。
蕓說,你們結婚時,她放火想燒死你,你知道嗎?
帥樹明說,知道,不怨她。怨我長得丑。
蕓說,她遇上麻煩了,你知道嗎?
帥樹明愕然,什么麻煩?
帥樹明的眼睛睜得很大,像牛眼,雙眼皮,長睫毛,撲閃撲閃。顴骨高高聳立,把兩邊腮幫子給比下去了,也讓鼻子徹底淪陷。從眼角,到鼻尖,到嘴唇,并沒有找到慧慧說的刀疤,也沒有那樣猙獰可怕。如果不是曬得泛黑,也算得上光潔細膩。蕓甚至覺得矬子有點憨厚,還有點可愛。
帥樹明被蕓看得有點不好意思。蕓笑,慧慧說你臉上的疤讓她經常做噩夢。帥樹明也笑,本來是有一條小疤痕,是彈棉花時,弓弦突然斷了,彈到了臉上,擦破了點皮而已。她是不是還說,我肚皮上有牛皮癬?是不是說我口里呼出來的氣像糞窖的味道,吃飯特別響像豬嚼食,睡覺打呼嚕像過山雷?唉,她看我就沒一樣順眼。不說了,她為我帥家生了一兒一女,就是功臣。哦,對了,你喜歡蜂蜜嗎?要多少?槐花蜜、椴樹蜜?還是棗花蜜、枇杷蜜?帥樹明把蕓領進他的窩棚。窩棚不大,估計有十平方,幾塊板搭成的床,麻紗蚊帳的四個角用繩子拴在棚頂木條上。窗前的桌子上是一臺小黑白電視機。在亂石砌成的兩墩上,橫著一塊長長的木板。木板上有十幾個大大小小的塑料瓶子,瓶子上貼有標簽:槐花蜜、棗花蜜、枇杷蜜……標簽上還標注了功效。龍眼蜜:補腦益智,增強記憶。柑橘蜜:生津止渴,潤肺開胃。荊花蜜:益氣補血,散寒清目。山花蜜:養肝,治便秘。桉樹蜜:抗菌消毒,預防流行性感冒,治療喉嚨發炎。洋槐蜜:清熱解毒,養顏補氣。棗花蜜:補血安神,健脾養胃。益母草蜜:調經美白,日常保健。椴樹蜜:清熱利尿,養肝明目。瓶子按功效擺放,美容養顏類:雪脂蓮蜜(苕子蜜)、野玫瑰蜜、益母草蜜。去邪降火類:黃連蜜、枇杷蜜、荊花蜜、紫云英蜜、槐花蜜。養肺潤脾類:枸杞蜜、柑橘蜜、枇杷蜜……帥樹明像說快板一樣給蕓介紹。要說對于蜂蜜的了解,帥樹明比陳明要強得多,陳明對蜂蜜的了解僅僅停留在哄女人上。蕓心里感嘆,慧慧呀,你就是一只蝴蝶,而不是一只蜜蜂。
帥樹明對蕓說,你是慧慧的好朋友,看上了啥蜂蜜就拿去。又說,蜂蜜是個好東西。慧慧皮膚好,沒少吃蜂蜜,就是我這丑八怪也讓蜂蜜滋養得不錯。帥樹明掀起衣服,露出肚皮給蕓看。看見沒?牛皮癬沒了。蕓開始喜歡上眼前的這個矬子。
帥樹明還跟蕓說了一件事。人都是讓生活逼的。慧慧生了兒子后,一點奶水都沒有。帥樹明既要養娘、養老婆,還要養孩子,靠彈棉花掙不了幾個錢。慧慧天天在家罵他是廢物。都說生活比蜜甜,蜜肯定是好東西。帥樹明便想到了養蜂。養蜂人很苦,一年四季要趕著花期走。帥樹明不怕吃苦。不久,帥樹明摸索到了門道,要養好蜂,先要懂花兒。譬如說枇杷花開是深冬,七月椴樹花開,夏天金銀花滿山坡,芙蓉花開秋天到。別看春天到處花兒盛開,蜂釀出來的蜜未必就有冬天的金貴。日子久了,他還知道,什么山開什么花。他開始也恨慧慧,自從養蜂后,他不恨了。蜂要養,女人也要養,還要哄。蜜蜂有自己喜歡的花兒,你就要帶它去它喜歡的山坡。慧慧愛排場,她是村里第一個文眉的女人,第一個染發的女人,第一個穿旗袍的女人。女人愛漂亮,那是男人的臉面。養女人得花錢,所以他拼命地賺錢。女人的心大,男人的胸懷大。男人的胸懷要像天空,任由女人飛翔。女人飛累了,就會停靠在你心尖尖上。蕓讓帥樹明熾熱的話幾乎熏醉了。這是一個什么樣的男人?怎么就這樣懂女人,他與慧慧離多聚少,就是聚在一起也是入體不入心。這難道也是“生活”逼出來的?
蕓實在不忍心慧慧再糟蹋帥樹明的一片癡情,忍不住問,慧慧外面有男人,你知道嗎?帥樹明說,知道。蕓的精神世界幾乎讓波瀾不驚的帥樹明砸塌了,這還是男人嗎?做人底線都沒有了,簡直就不是人!蕓怒火中燒,心里罵了帥樹明一千次,吼出來的一句話竟然是,你這人怎么這樣?帥樹明并沒怎么去關注蕓的情感波動,而是說,前幾年暑假,娘說,孩子都大了,可以自己上學了,把慧慧帶到身邊去吧。我說,山里蚊蟲多,冬天冷,夏天熱,不是慧慧待的地方。娘罵,蚊子咬死她,我把蚊子當恩人供奉。那時我就知道,娘聽到了很多流言蜚語,是讓我管住慧慧。我說,亂由心生,隨她去吧。娘氣得吐了一次血。蕓問,為什么要隨她去,你是她男人。帥樹明說,她不明白的時候,最要緊的是讓她明白。蕓說,放縱她她就明白?帥樹明說,不是放縱,是把她交給時間。蕓無法從帥樹明的時間理論里走出來,徹底沉默了,心里彌漫著一層淡淡的悲憫。
帥樹明問蕓,你說的麻煩事,是不是她買店鋪的預付款要不回?
蕓又大吃一驚,你都知道?
帥樹明說,沒啥,錢買不到店鋪,總能買回個教訓。
蕓目瞪口呆,又隱約悟出,或許這也是帥樹明買慧慧明白的代價。
七
蕓從陽儲山回來,美容院一個接一個搞活動。搞完“雙十一”,接著就是元旦。美容院生意不好做,小城的美容院不少于五十家,只有不斷地搞活動,才能吸引人氣。快近年關,蕓才有閑情坐下來,看看窗外的風景。窗外喜樹掉光了葉子,喜樹籽跟小絨球一樣,掛滿枝丫。兩只松鼠開始把喜樹當作運動場,從樹干竄到樹枝,又從樹枝竄到樹梢,吱吱吱,唱個不停。松鼠是要把喜樹籽搬進窩里過冬吧。哦,是不是該下雪了!
這時,慧慧滿臉傷痕闖了進來,口里嚷嚷,小微,小微,給我敷膜,熱敷,加些蜂蜜。該死的刀疤又家暴我,差點沒命了。這日子過不下去了,我要離婚。
美容院沒有一個客人,本來很安靜,慧慧一來便亂作一團。
蕓聽了半天才搞清楚事情原委。
年關,蜜蜂才真正蟄伏。帥樹明的活也輕松下來了。慧慧半年沒去蜂場。帥樹明估摸城里蜂蜜賣完了,便托熟人捎去蜂蜜。蜂蜜捎去了,連個回話都沒有。帥樹明不認為丟了預付款有啥,但慧慧會不會也這樣想,是不是真惹上大麻煩了?帥樹明認為沒啥時,不覺得有事,現在想起蕓來時說過的話,越想越覺得有事。帥樹明決定來一趟縣城。
冬天的太陽出來得晚,早上八點,才剛露臉。帥樹明到了蜂蜜店,門還是關著的。他用腳踢了幾下門。砰颯颯,砰颯颯,卷閘門的聲音很大。隔壁賣鴨脖的姑娘探出頭說,買蜂蜜嗎?安徽婆沒那么早,你可以去她住的地方喊她。她就住在后面小區的車庫里。
這穿堂風吹得還真他媽的冷!帥樹明嘀咕著,把大衣扣子扣緊。大衣是女兒從上海快遞給他的,花了六千多。女兒說,爸穿上這大衣在山里就不冷了。又說,爸穿這衣服肯定帥呆了。帥樹明說,爸還帥給誰看呀?給你媽買一件吧。女兒說,不買。媽穿得越漂亮越沒爸什么事。帥樹明罵,孬婆,不能這樣說媽。今天,帥樹明穿這件大衣進城,就想刮挺刮挺地站在慧慧面前。男人口里說不在乎自己的女人怎么看,心里卻恨不得女人眼珠子看得拔不出來,只有這時男人才有機會。出門前,帥樹明就照了半天鏡子,這藏青色的大衣,配上銀灰色的狐貍毛領,還真是富貴大氣。皮鞋也是女兒寄來的,油光發亮,鞋里面毛茸茸的,腳像放進了火爐,暖氣從腳底下往上升,人也變得很亢奮。女兒還真是爸爸的貼心小棉襖!
慧慧住的地方是車庫改裝成的,綠色的卷閘門半卷著,緊挨著卷閘門裝了一排玻璃,玻璃門是關著的。玻璃門里拉了紅色的布簾。帥樹明張開嘴,想叫慧慧,卻聽到里面傳出男人的聲音。男人說,還要不?要。是壓得很低很低的女人的聲音。男人繼續說,還要不?要。這回女人的聲音變大了。還要不?大點聲。男人的聲音帶點喘息。要,要,要。女人的聲音開始放蕩起來。
帥樹明聽得頭發根都豎了起來,拳頭捏得能聽到骨節咯吱咯吱響。沒見過慧慧放蕩,帥樹明總把慧慧往好處想,甚至想先隨她一陣,只要兒女在,她總有回頭的一天。現在親眼見到這荒淫的場面,帥樹明才知道,他無法忍受。他掄起拳頭砸向玻璃門。
帥樹明和陳明扭打在一起,陳明人高馬大,幾下工夫就奪門而逃。慧慧無處可逃。帥樹明掄起巴掌,雨點般落在慧慧赤裸裸的身軀上。
蕓站在窗里看松鼠搬喜樹籽,松鼠勞勞碌碌的樣子,讓蕓想笑。世界上只要能活動的生物都是這樣勞碌,唯有樹站在那里一動不動,任由冬去春來。
帥樹明打你了?
不是打,是揍。
那還不是一樣。
不一樣,這次是往死里揍。
慧慧在蕓面前無話不說,甚至在美容院也無所顧忌。
陳明不是失蹤了,又回來了?
陳明被打假辦抓了,花了點錢,就出來了。
你怎么就信了陳明?
他就是在蜂蜜里加了點東西,怎么就不能信?
只加了一點?我怎么聽說假蜂蜜鋪天蓋地,蜂農欲哭無淚。
不管真的假的,抓了還能出來,說明有門路。有門路就是我的依靠。
你醒醒吧。
你男人也打你?
我男人不打我。日子過得像一杯白開水,我喜歡白開水。
這個矬子是一杯苦水,你喝一口試試!
別為自己找借口。苦和甜是一種錯覺,你往好處看自己男人,再想想兒女。
你見過他了?
是的。
……
美容院恢復了之前的靜謐。
帥樹明走了?
他打了我就逃了。
他不是逃,是不愿看到你傷心。就像一個做錯了事的孩子。
他惡毒著呢,沒那好心。
他在努力消除你與兒女的裂痕,你相信嗎?離了婚,這一切都將化為烏有。
美容院愈加靜謐。
想起兒子,慧慧在瑟瑟發抖。
慧慧的兒子很爭氣,讀書一路直升,高三畢業就考上了上海大學。兒子極少給家里打電話。一次給父親來電話,帥樹明說,給媽媽打電話了嗎?兒子說,沒有。帥樹明說,給媽媽打電話了,再給我打。兒子才第一次給媽媽打了電話。慧慧接了那次電話之后,有三個月沒碰過外面的男人。之后,兒子又沒電話了。兒子沒電話當然不是慧慧找男人的理由。不久,慧慧的二哥得了肺癌走了,慧慧又開始找男人。
蕓問,你知道兒子為什么給你打電話嗎?
慧慧說,不知道。
蕓說,你男人說,不給媽媽打電話,就不要給家里打電話。
慧慧哭了。
蕓問,你跟陳明快半年吧,他幫你要錢了嗎?
慧慧哽咽地說,沒有。他說過年后去找店鋪老板。
蕓說,為什么要等年后?你現在就去找陳明,看他能不能要回那筆錢。
八
慧慧大“鬧”美容院之后,一直沒有消息,蕓對慧慧漸漸死心了。這個老鄉已經無可救藥,她不是救苦救難的菩薩,沒辦法讓慧慧回頭。
或許是緣分未盡。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冬日,蕓又接到慧慧的電話。蕓毫不猶豫掛了電話,既然不能拉慧慧出泥潭,也不能被慧慧拉進泥潭。可是慧慧的電話仍然是一個接一個打進來。蕓心軟了,接了電話。這回慧慧沒哭沒鬧,而是很平靜地講完了這段時間的經歷。
慧慧被蕓說動了心,果然去找了陳明。
意外之舉,必有意外收獲。慧慧居然把陳明捉奸在床。
慧慧瘋狂地去撕那女人的臉。那女人問,你是誰呀?慧慧說,你問我是誰?女人問陳明。陳明說,問那么清楚干嗎?大家在一起,不就是圖一時快活?慧慧徹底看清了陳明。慧慧這回還真不想圖一時快活,而是想一輩子快樂。她就想陳明把那錢要回來,就跟銼子離婚。兒女已經那樣了,未必能指望得上。沒想到陳明是跟她演戲。慧慧發瘋似的往外跑。陳明怕慧慧出事,騎著摩托車在后面追。追到沿湖路,眼看要追上,陳明的摩托車被路上一堆石子掀翻,摩托車摔出去又把慧慧撞飛了。慧慧斷了三根肋骨,臉也被石子劃破了,一條疤痕從眼角斜過鼻尖到嘴唇,鮮紅鮮紅的,正是慧慧描述矬子的情形。
這些天,慧慧一直住在醫院。今天拆線后第一件事就是給蕓打電話。
蕓問,給帥樹明去電話了嗎?
慧慧無限憂傷地說,沒有。我已經回不去了。
蕓給帥樹明打了一個電話。帥樹明趕到醫院卻不敢見慧慧,蹲在病房門外暗暗抽泣。蕓說,一個大男人哭啥?你應該去揍她。帥樹明說,她已經這樣了,怎么下得了手?蕓說,不揍她就去哄她,或許是個機會。帥樹明驚詫地看著蕓。蕓又說,你不會哄,兒子放寒假沒?讓兒子過來。快過年了,把女兒也喊來。帥樹明說,這事哪能告訴兒女?蕓說,誰讓你告訴這事?誰還沒有迷路的時候?兒女或許能讓她找到方向。帥樹明說,能行?蕓罵,你以為錢能買到她的心?她為錢饑渴的時候,錢是毒藥。
終于下雪了,而且一下就是三天三夜。窗臺上落下一串鳥的爪痕,還有幾顆喜樹籽,猶如給潔白的絹布繡上了寫意畫。
蕓癡癡地看著窗外的雪景,心里無限惆悵。仿佛什么都沒做就過了一年。這一年最糟糕的一件事就是認識了慧慧,慧慧把她一年都攪得亂七八糟。她發誓要忘掉這個老鄉。
她剛發完誓,安徽婆一家人找上了門,慧慧和她的女兒、兒子,還有帥樹明。慧慧的女兒像極了慧慧,兒子像帥樹明,但比帥樹明要白凈秀氣,個子也要高些,憨厚的相貌里多了一份書生氣。
蕓暗自苦笑。看來這群蜜蜂想趕都趕不走!
作者簡介

李冬鳳,中國作協會員,江西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校外導師,都昌縣教科研中心主任,《星火》都昌驛驛長。散文、小說作品散見于《北京文學》《天津文學》《作品》《創作評譚》《星火》《花溪》《江西日報》《教師博覽》等報刊。出版散文集《鄱陽湖與女人》《鄱陽湖北岸》。
責任編輯 張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