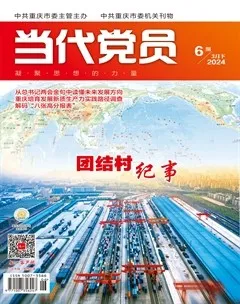千年安居 百般樣式
王婉玲 陳驊

在古鎮,光陰的腳步似乎要比在城市緩慢很多。
上午9時,太陽才緩緩爬上重慶市銅梁區安居古城對面的山梁。鋒利的光線切開薄薄的霧氣,把古城里門樓、院墻和牌坊的影子重重疊疊地壓在一起。
慕名前來的游客,徘徊在街頭一家正出鍋的雞絲豆腐腦的熱氣中,鳥雀在臨近樹梢上鳴叫,路邊的花香若有若無,三五位居民搬出小板凳坐在有陽光的青石上閑敘……
“古城的一天就這樣開始了。”30歲的導游賈詩雨,習慣以沉浸式體驗的方式帶著游客感受安居古城流淌千年的歷史脈絡。
沿著128級階梯登高而上,穿過星輝門,安居古城便如一幅古老的畫卷,順著青石路在眼前延展開來。
青石路邊,密密麻麻擠著上了“歲數”的民居,而民居之中又見縫插針地屹立著一些保存較為完整的九宮十八廟建筑群。這是“湖廣填四川”移民活動的重要見證,也是外來文化與巴蜀文化融合的載體。
“文化的多元,讓安居素有‘一座古城,百般樣式的美譽。”在賈詩雨的介紹中,昔日縣衙旁莊嚴凝重的湖廣會館、北門碼頭外高踞山腰的下紫云宮、化龍山頂風采依舊的江西會館……每一棟建筑好似都有著說不完的古城往事。
2013年起,安居古城加快了保護性開發的進度,千年古城的百般模樣從此被鐫刻在一街一巷、一步一景之中。
會館為證 人文薈萃
城北涪江,城西瓊江,兩江交匯之處,安居古城依山而立,靜臥于斯。
這是一座始建于隋開皇八年(公元588年)的傍水小鎮。明清時期,由于川渝地區經濟迅速發展,水陸交通便利的安居開始成為外省客商開展貿易、交流的商賈重地。
基于拓荒異鄉的艱辛和對故鄉的思念,一些有經濟實力的外省移民紛紛集資修建“聯絡鄉誼、互通聲息、扶持鄉友”的場所。一時間,福建會館、湖廣會館、江西會館、廣東會館、黃州會館等移民會館大量涌現。
自此,不同領域行會林立,各式建筑與地方文化不斷交融,“日有千人拱手,夜有萬盞明燈”的繁華景象成了集鎮居于大安溪畔(瓊江古稱)的古城日常。
得益于濱水之城的地理優勢和往來客商的頻繁貿易,當時幾乎戶戶養蠶的安居古城成了古代桑蠶絹帛的原產地和貿易地。銅梁區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曾凡久是土生土長的安居人,他逢人便驕傲地說:“名傳天下的蜀錦大多出自涪江流域,這也是古時安居商賈云集、人文薈萃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曾凡久看來,安居并非千篇一律的古城模樣,“房屋和街道坐落于兩灣江水之濱,古城依山就勢,鋪排在江岸的臺階上;兩座看上去形制簡陋的城門保存完好,從翹腳的飛檐到朱紅的門樓,再到黑黝黝的匾額,無不顯示著安居古城獨特的風采”。
然而,要想找到這座古城將多元文化包容為一體的更為直觀的證據,應當要數最受當地居民和游客關注的福建會館、黃州會館、湖廣會館了。這3座會館極為罕見地在一個地方隔墻相鄰、共用邊墻,一字排開、氣勢磅礴。
三館并立的背后,正是融合鄉鄰關系的見證。
徽式風格的福建會館,其高高聳立的馬頭墻本是源于福建地區筑高墻、御臺風的需求。但在地處內陸的安居,馬頭墻失去了防御臺風的功能,便以建筑的形式,承載移民對故土的思念。
“但這并未招致當地其他建筑風格民居內居民的抵制,反而相得益彰。”曾凡久說。
時至今日,安居古城在保留原有格局的基礎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活化利用:湖廣會館戲臺上,有川劇、折子戲、“坐歌堂”等傳統文藝節目;福建會館定期舉辦風俗表演,以傳播落腳在安居古城的客家文化。
非遺傳承 文化多元
在安居融合沉淀的多元文化,進一步豐富了古城的人間煙火氣。
隨著音樂響起,川劇變臉非遺傳承人張剛在湖廣會館戲臺上為到來的游客獻上表演。站點、踢腿、亮相……在扇子一開一合間、拂帽甩帶扭頭間,張剛出其不意地變換著面具和姿態,引發游客不斷的驚呼與贊嘆。
“我認為這就是非遺文化的意義,它被發現、被傳承,在不同的時代為人們帶來不同的感受與體驗。”每當被問及留在安居古城表演川劇的原因,張剛總是堅定又自信。
不僅是川劇,折子戲、荷花龍、炸酥糖……不同的地域文化以“表演”的形式在安居古城匯聚,成為千百年來安居人的“根”與“魂”。
對敖愛娟而言,喚醒一天的,不是可聞的雞鳴,而是一鍋新鮮熱乎的翰林酥。
“從早上到傍晚,這口鍋里的炸酥糖就沒停過。”敖愛娟笑著指了指制作翰林酥的大鍋,“人太多的時候,是真嫌慢!”
在敖愛娟的“抱怨”聲中,一則關于翰林酥的故事也被她“灌”進了游客的耳朵。
相傳清朝康熙年間,王汝嘉與父親王恕帶著母親制作的小米酥進京趕考,父子二人先后金榜題名并被皇帝欽點為翰林大學士。鄉親們為了討個好彩頭,紛紛視小米酥為神奇小吃,進京趕考的人都會帶著它,期望能借此得好運。此后,小米酥便被稱為翰林酥。
“這個名字其實是人們對未來寄予期待,希望以先輩為榜樣,奮發圖強。”作為翰林酥傳統制作技藝的第六代傳承人,敖愛娟認為,這份期待不單是被寄托在“翰林”二字上,也體現在翰林酥數百年來始終如一的口感上。
幾年前,由于購買者增多,敖愛娟曾嘗試過機械化制作翰林酥,但口感總是不如手工制作的。
“慢有慢的道理。”為了不辜負大家對翰林酥的期待,敖愛娟始終堅持純手工打造,每一味原料都被她親手壓制成型,如安居城墻上的石磚,層層堆疊、日夜堅守。
不只是翰林酥,作為銅梁龍舞發源地之一的安居,其土生土長的“龍文化”氛圍也異常濃厚。看龍舞、觀龍燈、賽龍舟……安居人將龍文化演繹得淋漓盡致。
李德瑜是安居古城有名的手藝人,繪畫、雕刻、龍燈彩扎,無一不精。制篾、扎龍、粘紙、填色、組裝……十余道工序在李德瑜手里“搗騰”后,一條“活生生”的銅梁龍便完成了。
每年上元佳節,十里長街的龍燈彩扎成了當地一大景觀。得益于像李德瑜一樣彩扎技藝人的堅守,銅梁人關于“龍”的念想一直被編織著。
新式吆喝 穿越時光
文化的多元造就了安居的百般模樣,也催生出安居百變的“出圈”方式。
“巴岳山、黃桷埡,‘大人細娃兒一壩壩……”在“何代科書場”,客人們端坐其中,品一碗蓋碗茶,觀說書人何代科醒木拍桌講故事、說評書,敲打金錢板,上演一場場“獨角戲”。
只見何代科在臺上時而大笑、時而皺眉、時而搖頭晃腦,多角色飾演著各類人物,引得觀眾捧腹大笑。說起曾經的輝煌,何代科“啪”的一聲打起金錢板,仿佛將觀眾的思緒一下帶回千年前,窺見古城昔日的繁華。
作為銅梁金錢板代表性傳承人,何代科是在祖輩們的金錢板敲打聲中長大的。他將古城往事以打、唱、演等形式,通過風趣的語言、上口的唱腔呈現出來,內容貼近生活日常,很容易被鄰里街坊傳唱。
“周末到銅梁真愉快,觀賞龍燈好戲連臺。安居古城看龍舟賽,‘九宮十八廟要把腳走歪……”元旦節假期的第一天,23歲的余昱均專程帶著山西朋友張嘉施來到安居古城的“何代科書場”。“朋友是頭一回到銅梁,我想用一種有趣的方式讓她了解這里的地方特色。”看著張嘉施目不轉睛地盯著何代科的說唱,余昱均滿心歡喜。
在安居,游客還可以深入劇情,與歷史來一場面對面的“對話”。
竹編球、竹扁擔、毛筆是安居“龍文化、商文化、翰林文化”的3個典型代表。在沉浸式體驗游戲《安居·繁煙》中,游客可以任選一種代表為線索,擇一信物,著上衣裳,踏上旅程。
旅程中,游客會穿梭于依山而建的傳統民居、通幽曲折的古街小巷、獨具韻味的吊腳樓,在走走停停中,與安居人共話桑麻,猜字謎、識算盤、閱四書……
“可以一邊游賞一邊在細微之處感受多元文化的交織與融合,這種體驗很特別。”張嘉施在完成一場與安居古城的歷史“對話”后,難掩意外之喜。
“我們就是希望通過沉浸式體驗,讓游客走進安居、了解安居,在游樂中將安居的多元文化浸潤于心。”安居鎮文化中心負責人牟梨花相信,這座古城會在歷史與文化的交相輝映下綻放更多的“安居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