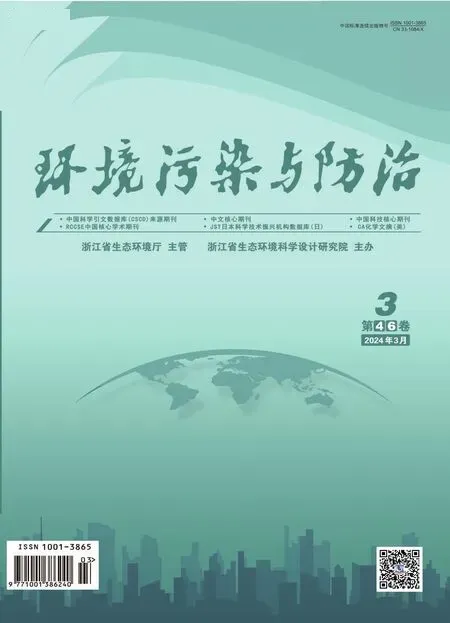土著微生物原位修復技術治理污染地下水的工程化應用現狀
鄔潤澤 徐 斌 徐 申 張 蔚 張 弛#
(1.浙江師范大學地理與環境科學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0;2.浙江省環境科技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00)
地下水資源分布廣泛,通常被認為是清潔和未受污染的,是一種重要的水源[1]。然而,各種人類活動導致了天然地下水污染的增加。2021年《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我國地下水主要污染物超標仍然較為嚴重,在1 900個國家地下水環境質量考核點位中,Ⅰ~Ⅳ類水質監測點占79.4%,Ⅴ類占20.6%,地下水Ⅴ類水百分比較上年有上升[2-3]。
微生物修復技術具有高效低耗的優點[4],相較于各種常規的物理、化學修復地下水技術,微生物修復方法可以實現將地下水中有機物(例如硝酸鹽、酚類化合物)的去除率保持在99%以上[5],因此被認為是有效的、具有研究價值的方法。其中,土著微生物修復技術不僅管理方便、二次污染少,還能有效解決傳統微生物菌劑存活率低、啟動慢等問題,而且減少了外加菌種帶來的生態安全風險。
生物修復技術大致分為非原位法和原位法[6]。原位修復技術在國外已有廣泛應用,在國內由于各環節技術水平的限制,應用較少。采用注入法修復污染場地,能加快修復效率、且涉及的土方工程較少。高壓旋噴注入法和原位深層攪拌注入法作為較新興的原位注入技術,雖然都具有適用于非均質地層、藥劑攪拌混合效果較好的優點,但也存在容易破壞地層結構、使場地承載力下降、巖土施工機械易受藥劑腐蝕等缺點[7]75。因此,在目前的實際工程中,該技術主要是通過注射井或直推注射設備,將菌劑注射至受污染地下水中。
土著微生物原位修復技術結合了土著微生物修復技術和原位修復技術兩者的優勢,在對地下水原生水文地質環境擾動較小的條件下,將土著微生物菌劑注入受污染區域,微生物在地下水中進行生理活動,降低污水中的污染物濃度,從而達到修復污染地下水的目的。土著微生物原位修復技術可通過篩選不同優勢降解菌種,降解相應的有機及重金屬污染物,和傳統修復方法相比成本低,降解效力維持時間長,是今后地下水修復,尤其是復雜污染地塊、在產工業企業長效修復的發展方向。
筆者從土著微生物原位修復技術總體工藝流程展開,介紹了土壤及地下水中土著微生物的性質及培養模式、注射井注入修復技術、直推式注入修復技術以及國內外采取上述兩種原位注入法,應用土著微生物修復地下水的工程實例,闡述了土著微生物在修復地下水工程化應用中的瓶頸并進行展望。
1 土著微生物原位修復技術總體工藝
實際工程中,將土著微生物菌劑應用注射井或通過直推式注入法原位修復污染地下水的技術工藝流程,如圖1所示。

圖1 微生物修復技術工藝流程
通過實驗室小試、現場示蹤中試、現場以注射井法或直推式注入法注入土著微生物菌劑中試,確定微生物增殖速率、適應污染物濃度上限、菌劑的添加量、注射井布設形式、藥劑影響半徑等參數,以及根據注入后的土著微生物增殖規律確定合理的采樣檢測時間和頻次。
應用于實際工程中系統化的修復流程為:從工程現場取回污染地下水周邊土壤樣品后,在實驗室中進行優勢菌種的篩選、組合優化及擴培,然后進行菌劑制備及生產。制備的菌劑用于現場的注射施工準備,在確定好井點布設位置和完成注藥前人員和設施準備工作后,將菌劑通過注射井或原位直推注入污染地下水中。修復區域經過一段時間靜止反應,基本確定菌種在地下環境中已定植、繁殖,且具有一定數量和較好活性后,利用監測井定期取樣監測地下水各項指標,檢測各項污染物濃度及土著微生物存活率是否達到目標值。
在經過一段時間地下水取樣檢測工作后,若地下水指標未達到目標值,則需綜合分析是否需要重新篩選菌種及補注微生物。如檢測結果顯示污染物濃度有所下降但未達到理想值,是由于客觀原因導致微生物數量不足形成了動態平衡,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再進行兩到三輪的原菌劑注射工作,促進降解;如已注入的微生物不能有效降解某類污染物,導致污染物濃度降低達到瓶頸,則需重新篩選優勢降解菌種,優化擴培后再進行注射工作。直至地下水和微生物的各項指標均達到目標值,完成該污染區域地下水修復工作。
2 地下水中土著微生物的性質及培養模式
2.1 土著微生物的性質
天然土壤、植物根系、巖石縫隙和地下水中都含有豐富的土著微生物,了解土著微生物的各種性質有利于在工程中應用其更好地去除污染物。
土著微生物在地下水和土壤環境中自身的生物代謝活性受溫度影響,環境中的微生物均在一定的溫度范圍內生存[8]。過高或過低的環境溫度會抑制微生物生長甚至使其失去活性。
土著微生物正常開展各項生命活動需要充足的營養物質。在受污染的地下水區域,土著微生物菌劑可以將氨氮、氯代烴、石油類碳氫化合物、金屬離子等作為碳源或電子受體,供給自身的生命活動。
篩選和優化后的土著微生物可以分泌特定的酶或胞外聚合物與地下水中的污染物發生反應,將污染物轉化為無機物[9]98,進而以無害的方式排放至環境中。
土著微生物發揮降解效力不單靠自身的活性和質量,還需要一定數量的微生物集群。在污染地下水修復過程中,若污染物濃度超出土著微生物的適應上限,會抑制土著微生物的生長繁殖和發揮降解活性。
土著微生物相較于外源微生物對本土地下環境的適應能力更強。地下水中的土著微生物以兼性、厭氧微生物為主[10],但在土壤滲透性較好、地層較疏松的地區,也存在好氧土著微生物。好氧微生物對COD的降解能力顯著強于兼性和厭氧微生物。
土著微生物具有定向響應能力。以目標污染物為碳源、電子受體或供體、輔助代謝物的土著微生物可以將污染物降解轉化。
注入地下的微生物大部分定植在土壤、粉煤灰或者其他的固相介質中,少量微生物存在于液相游離態的地下水中。
2.2 土著微生物的培養模式
在實驗室中,具備降解污染物能力的優勢菌種篩選的基本原理為:在以目標污染物為唯一碳源的環境下,可以存活且具有較好活性、污染物濃度降低的同時微生物數量不斷增加,則表明此類微生物具有降解效果,是理想的優勢菌種。隨后通過富集和分離,篩選出具有硝化和反硝化能力的菌落,通過重復傳代純化得到目標菌種[11]。整個菌種的篩選過程需要1~2周,隨后根據篩選出的單菌驗證其降解能力,以及模擬有外源污染物輸入情況下的微生物抗沖擊能力實驗。
培養過程中可能用到的手冊有《水生微生物學實驗法》[12]、《土壤微生物研究法》[13]、《常見細菌系統鑒定手冊》[14]等。
3 注射井與直推式注入技術
3.1 注射井注入技術
注射井法是基于地下水監測技術發展而來的一種高壓壓裂的藥劑投加方式[7]73。在工程中表現為采用帶篩孔或塞縫的,由聚氯乙烯或金屬制成的復合材料在污染區域范圍內建立一定直徑的注射井[15]378,化學氧化劑、土著微生物菌劑和固態藥劑等以常壓自流或高壓泵入的方式被加入注射井中,一段時間后,加入的藥劑在橫向和縱向的滲透、擴散作用下逐漸覆蓋整個污染區域[16]134,與污染物接觸反應后達到相應的修復效果。
注射井的布點在工程實際中多采用正三角形布點法[17],注射點影響半徑一般為2~3 m[18]。項目設計注射點位置、布井數量及建井深度,需根據場地情況、污染面積及障礙物進行調整。
注射井在建井時可選用Geoprobe多功能鉆機將多根相同長度的空心鋼棒依次連接直推建井,也可由液壓螺旋鉆機或手提式中空螺旋鉆建井。注射井安裝完成后,需進行擴井作業以去除井中的泥沙、粉煤灰等雜質和沉淀物。擴井水量不少于5倍井體積的水量[19]。注射井注入技術示意圖見圖2。

圖2 注射井注入技術示意圖
注射井注入技術的優點有施工簡單,操作方便,適用于幾乎所有的氣態(O3除外)、液態或固態藥劑。適用于設有大量注射點的場合。多口注射井可共用一套包括藥劑罐、攪拌電機、輸送泵以及其他設備在內的注入裝置,多點位同時開展藥劑注射可在較短時間內完成注射工作,修復效率較高。建成的注射井可同時作為監測井和對照井,且可重復用于后續多輪藥劑補注,利用率高。缺點有注射點位固定,一般需構建大量注射井,基建費用較高[20]。污染地下水修復完成后,會在修復地塊殘留注射井,影響后續的開發利用。若注入配置成液態或泥漿態的固態藥劑,一定時間后在注射井篩孔或塞縫處可能會干化堵塞。
3.2 直推式注入技術
直推式注入技術是一種新興的場地調查技術,多用于無需設備重復進場的單輪注入場合,尤其適用于地表設備、地下管道及構筑物等較多的場地。其工作原理是鉆機下壓注射桿到達受污染的地下水區域,在恒定壓力下將修復藥劑由注射桿噴出,原位修復污染地下水。
直推式注入技術優勢顯著。由于無需位置固定的藥劑輸送管,且Geoprobe多功能鉆機本身占地面積較小,故直推式注入法相較注射井法更為靈活,可在基本不影響場地內企業正常生產的情況下完成注入。此外,在建井深度范圍內,可通過上提或下壓注射桿精準地控制注射深度,有針對性地對重污染區域開展藥劑注入,有效降低了地層不均質性對注入效果的影響。
直推式注入技術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過高的注射壓力會造成溢井或形成地層裂縫,導致修復藥劑向其他非污染區域擴散,影響地下水修復效果[15]377。
4 應用土著微生物修復地下水現狀
4.1 國內應用土著微生物修復地下水實例

4.2 國外應用土著微生物修復地下水實例
國外已有許多應用土著微生物原位修復地下水的案例。M’RASSI等[24]從煉油廠的石油污染土壤中分離出烴類降解菌。分離得到的菌株表現出不同的能力:一些假單胞菌屬的菌株能夠生長并有效地利用正支鏈烷烴,而另一些菌株能夠降解高分子量的多環芳烴,驗證了烴類降解菌修復石油污染地下水的較高潛力。SINGH等[25]使用富集技術從受污染的土壤中分離出10種本土微生物,并在標準降解條件下選出其中具有最高降解潛力的5種分離物,試驗結果表明短小芽孢桿菌(Bacilluspumilus)優勢菌種在兩周內降解了該污染場地地下水中86.94%的柴油滲濾液污染物。ADTUTU等[26]應用脫鹵球菌屬菌株FL2修復TCE污染地下水,結果在7個月內脫氯率≥95%,增產井中TCE的最終質量濃度在1.84~1.87 μg/L,低于美國環境保護局2.0 μg/L的限制,處理后用實時熒光定量核酸擴增檢測系統(qPCR)對地下水微生物群落的評估顯示,經典的脫氯菌(地桿菌和脫鹵球菌屬)的數量增加了約50倍,體現了脫氯菌的長效存活能力。美國堪薩斯大學的DEVLIN等[27]采取先厭氧、后好氧的分步生物修復的方式,去除地下水中的氯化溶劑混合物與石油烴甲苯(TOL)污染,在厭氧生物活性區,通過注射井注入的營養物將四氯乙烯、四氯化碳和氯仿還原為二氯乙烯,隨后在好氧生物修復階段將二氯乙烯有氧降解,與對照組的自然衰減相比,生物修復技術可實現對混合污染物更高的去除率和更快的降解速率。
4.3 國內工程化應用現狀
我國當前應用土著微生物原位修復技術治理污染地下水的實踐大多數仍停留在實驗室小試階段,一些現場污染地塊的中試項目正在進行,但也處于小規模效果驗證階段。
5 工程化應用的瓶頸及展望
土著微生物原位修復技術在我國工程實際中應用較少,主要是由于菌種篩選技術的限制、微生物法短期降解效力相對物理法或化學法偏低等因素,導致業主更傾向花費更高的成本選擇物理法或化學法在較短時間內完成污染地下水的修復工作。此外,在地下水重污染區域和復雜水文地質環境中,如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場滲濾液污染地下水,土著微生物可能存在存活率較低和難以定植的問題[28]。土著微生物原位修復技術難以作為獨立修復技術發揮效果,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土著微生物原位修復技術的工程化應用。
pH、溫度、土壤含水量及地質特征等自然背景條件的變化,客觀上要求高標準的菌種篩選技術,由此篩選出的土著微生物才能保持理想的降解效力和存活能力。隨著土著微生物菌劑注入到地下水中,降解產生的酸性副產物使自然土壤環境的pH下降,當pH超出微生物降解污染物及維持其活性的合適范圍,即5.0~9.0,酸性副產物會擾亂微生物代謝,抑制微生物生長[29]。此外,具有潛在修復價值的細菌集中在中溫菌種(20~40 ℃)[30]。當溫度過低時,微生物活性會降低;當溫度過高時,易發生酶變性,細胞活性下降甚至死亡。再者,土質致密及土壤含水量少易造成生物菌劑的擴散效率低[9]98,若土壤或沉積物中的水被固體物質吸收,或作為結晶水與溶解的溶質結合在一起,會影響土著微生物對這部分污染地下水的降解效力。因此在土著微生物原位修復時,注重地下水修復效果的同時,也需關注地下水自然背景條件的變化[31],比如地下水流速與含水層介質的非均質性會改變污染物在地下水環境中的運移特征[32],增加微生物修復難度。
微生物法在降解效力的啟動速度和達到污染地下水修復目標所需時間兩方面普遍弱于物理法和化學法。一方面,在原理上,土著微生物菌劑注入地下水后,需依次經過定植、增殖、維持一定菌群總數,才能有效發揮降解效力,雖然篩選出的優勢土著微生物菌種是本土環境中分解速率較快的菌種,但是增殖到足夠的菌群總數仍需一段時間。另一方面,相較物理法和化學法,微生物法對地下水中污染物的降解效力相對長效緩和,需要更長的時間完成污染地下水修復。此外,前期探查確定待修復區域地下水特征污染物后,在實驗室篩選出的土著微生物以特征污染物為主要降解目標,注入地下水后,土著微生物對污染物的降解往往有定向性,并不是所有的污染物都能被土著微生物有效利用[33],這導致在前期難以對修復速度和程度做出準確預測。在復雜污染地塊地下水修復過程中,土著微生物對重金屬等有毒污染物還可能存在抑制敏感性,影響微生物存活率和降解效力,這也限制了土著微生物普遍應用于污染地下水修復工程中。
利用土著微生物來原位修復污染地下水雖面臨一定限制,但充分掌握和發掘土著微生物的性質和特點,改進注入技術和與其他修復工藝結合等,可能在將來的工程實踐中取得更好的修復效果和經濟效益。
進一步發展菌種篩選技術,篩選高效、生存能力強的土著微生物,以期使土著微生物具備優良的抗污染羽流沖擊能力,在地下水重污染區域具有良好適應性并持續穩定發揮降解效力。改進原位注入技術應以探索加大修復藥劑的擴散效果為主要目標,隨著單井修復半徑的擴大,所需的注射井數量就會相應減少,特別是在大面積布井修復時,這將大大降低實際修復工程成本[16]139。以微生物修復為主的多種技術組合也是目前的研究熱點,例如將空氣噴注[34]與土著微生物原位修復技術組合,利用已有注射井,在菌劑注入后進行噴注,促進菌劑與地下水的結合。在歐洲各國,表面活性劑微泡也被嘗試泵入地下水中,在多個超級基金項目中已被證明可加快生物降解速率。此外,循環井技術、多相抽提技術、可滲透反應墻(PRB)技術等與微生物修復技術聯用已被用于治理硝酸鹽、磷酸鹽、石油烴等多種污染物,取得了較好效果。未來的研究還需要加強對土著微生物特定的電子供體如Fe、Mn、可溶性有機碳(DOC)和無機氮上限和下限的測定[35]。在土著微生物的固定化方面,復雜流向、大流速的地下水環境常需要固定化吸附材料的應用,以活性炭為代表的菌劑吸附材料具有較好吸附性能,注入藥劑前在注射井中加入活性炭,使微生物菌劑吸附在活性炭中,可在單井有效范圍內穩定降解污染物。在修復區域設置PRB或止水帷幕也可防止菌劑流失,使菌劑濃度維持在具有較好修復污染物效果的范圍。在未來的土著微生物原位修復技術工程應用中,可探索將數字可視化技術融入地質條件測量和地下水各項指標監測中,通過模擬軟件和優化算法確定原位修復的最佳施工參數,對修復場地的高程、井點、地層結構、加藥時間、污染物深度、地下水樣定期監測結果以及其他有必要說明的問題等信息進行全面匯總和記錄,并開發地下水流動擴散模型,結合軟件和算法做出對應的修復活動[36-37]。稀土元素已被嘗試作為示蹤劑來探測地下水是否與土壤中的活性物質相互作用[38]。在未來的地下水修復工程中,基于大數據調查的數據化分析結果是精準修復和科學治理的前提和基礎。
6 結 語
土著微生物原位修復技術以其高效、綠色、可持續、對地下水環境擾動小等優點引起了眾多學者和環境管理機構的關注。針對地下水中氨氮、COD、氯代烴的微生物原位修復已經有了大量的研究,但大多數仍處于實驗室小試或現場中試階段。復雜水文地質條件下,污染地下水原位修復工程的建設和性能優化將是今后研究和探索的重點。此外,規模化、低成本的土著微生物原位修復技術的探索是實際工程應用的重要方向。
隨著我國傳統產業的提質升級,土著微生物原位修復技術可在基本不影響工業園區正常生產的情況下進行,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結合。更高效益土著微生物菌劑的研發應用、依靠軟件計算實現精準注入點位、注入所需材料的資源再利用等,將真正發揮微生物修復技術高效低耗的優點,提高其作為獨立修復技術在市場中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