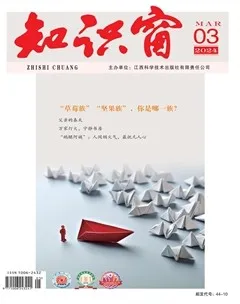下午五點,不要遺忘太陽
戚舟

下午五點,古人稱之為酉時,也叫日入、傍晚時分,正逢日落將歇的好時候。《莊子·讓王》中寫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
然而今日,或許西北的太陽太過與眾不同,偏愛晚睡晚起。我在曠遠的邊陲小城,從未在下午五點感受過黃昏即來的悠悠光景。就說晝短夜長的冬日,旭日高照已是上午十點,下午五點只能算是午后,要到七八點才能迎來日暮。
太多個午后五點時分,無論上學還是工作,眼中風景只有窗外屋檐下的方寸天空,它由一棵老樹、兩三座建筑、幾片云,還有偶爾盤旋而過的飛鳥組成。偶時抬望眼,我總瞧云絲緩慢地自我拉扯,悄悄翻卷變換姿勢,而那經年挺立的老樹,遙望著遠方巋然獨存的雪山,眼底充滿歆羨,卻只能任憑近身的古樸老樓定格歲月,和天空共同搭構不規則的留白,好讓窗里看風景的人釋放情緒。五點過后,陽光微斜,飛鳥的尾尖劃過樹梢,揚起一陣風雪,愣怔的人恍然回神。平平無奇的下午時光繼續流淌,然后被人滯留在情緒的邊角。
只有在周末或節日里,這段時間才不至于如此靜寂。當窗外響起貨郎的叫賣聲——有時是音調不夠標準的“鮮奶子咧”,有時是老舊喇叭里成串的“收頭發,收舊家具,收洗衣機”——我便從午歇的慵懶中清醒過來,走出家門,來到各式各樣的街巷。快節奏的城市生活總有光陰慢下來的地帶,比如舊市場,鼎沸人聲幾乎穿破篷頂,在你來我往的口舌之爭里,讓人透過塵俗不喜的生計看到鮮活溫馨的一面:不必香車佳肴,或許一串紅彤彤的冰糖葫蘆就能帶來快樂。又如舊城區的小公園,記得有天我無事閑轉,雪在腳下不斷咯吱作響,好像春花欲燃的聲音,無端讓人心潮澎湃。我仰望天空,倏地發現太陽已隨著時間的流逝快速墜落,原來日光消逝也有速度,它如眷戀夜燈的風雪夜歸人,散著橙色的光撲向遠山的懷抱。在那一刻,我想我將銘記這段時光。
比起西北,南方的下午五點更符合莊子的逍遙心意。過去幾年,我奔走于全國各地,見識過許多不一樣的風景。泉城濟南的冬天,太陽總熬不過五點,大霧四起,雪漫天地,昏黃的夜燈下行人匆匆,我逆人潮歸家,頂風微躬的身卻忍不住漫步起舞,心底漸燃一團野火,就像太陽因早落而彌補給我的火種。長沙春日碎雨纏綿,四月天芳菲未盡,卻已被太陽逗弄得暈頭轉向。比如橘子洲頭的日入時分,忽而雨,忽而風,日光斑駁在湘江,很有“半江瑟瑟半江紅”的意境,桃花就在陽光里開開落落,鋪滿整個沿江大道。日暮而歸,我轉身遙望,正好看見江水吞沒最后一縷光,桃花殘紅隱入夜幕,平生一股心安。
那年在成都,夏秋交接時分多風多雨,常淋得人心煩意亂,尤其臨近下班的五點左右,看著窗外忽來的瓢潑大雨,我品不出“巴山夜雨漲秋池”的美,只是惶然如何去擠地鐵。那日有事早歸,我誤乘公交車到一片老區附近,被雨點催眠的心陡然驚醒,眼前綿延數里的銀杏林在風雨中搖晃,仿若戎裝老將,讓人在悲愴之余熱血沸騰。我撐傘匯入觀林的人群,雨聲漸弱,原該西沉的太陽從極遠的天際隆重登場,人群歡呼,當陽光透過林隙拂在脊梁,我也彎起久無笑意的嘴角。有什么可惱的?心若向陽,風雨便遮不住光。就像下午五點,比起拂曉、正午和深夜這些獨特時點,雖少了唯美和期待,卻讓人在等待中看見別樣的風景,如西北寒冬里的圓日盛別,又如南方小城里太陽的應景西落,或于風雨雪,或在山河海,無論落身或藏心,那份直觀的作別與觸碰,帶給人的是思索、悸動、安定和自我審視——日月青黃不接,“我”便是唯一的光明。
下午五點,雖是“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但請不要遺忘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