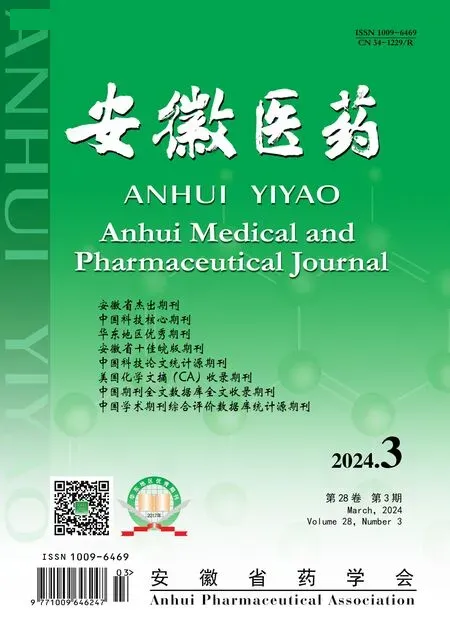犬尿氨酸通路在兒童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中的研究進展
荊曉琦,方成志,張丙宏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新生兒科,湖北 武漢 430060
神經發育障礙(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NDD)是由于遺傳和環境因素綜合作用而導致的中樞神經系統發育缺陷[1],以兒童期發育運動延遲,社會和情感行為改變以及認知障礙為特征[2-4]。在涉及的腦區達到功能成熟的特定發展階段之前,兒童NDD 相關病理表現可被識別,表現為神經軟體征、認知缺陷、腦形態學改變等,并出現相關臨床癥狀,最終可能導致終身疾病[5]。作為一組與遺傳異質性和后天疾病高度相關的神經精神類疾病,神經發育障礙全球兒童患病率為2%~5%,給社會和家庭帶來極大的負擔[6]。常見的兒童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包括孤獨癥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SD)、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癲癇、精神分裂癥(schizophrenia,SCZ)等[6-8]。兒童NDD 的發病機制復雜,長久以來人們普遍認為突觸形成和修剪、神經細胞分化遷移、髓鞘形成等相關基因異常與環境因素共同作用導致了病人的復雜癥狀[1,9-11]。但越來越多的研究揭示了神經炎癥和免疫失調是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共同機制的重要環節[12-13]。直接證據包括病人細胞因子表達譜的變化,當機體處于細胞因子激活狀態時,循環促炎化合物水平的升高與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癥狀加重、神經病理學表現突出和認知缺陷加劇相關[14];Purves-Tyson等[15]發現早發SCZ病人腦中補體C1qA、C3 和C4 的基因表達增加;而腸道菌群紊亂引起炎癥因子的累積以及抗體產生的失衡,影響了病人的腦發育及神經元可塑性[16]。犬尿氨酸通路(the kynurenine pathway,KP)的神經活性代謝產物在神經系統發育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有學者發現,犬尿氨酸(kynurenine,KYN)、犬尿喹啉酸(kynurenic acid,KYNA)和3-羥基犬尿氨酸(3-hydroxykynurenine,3-HK)在大鼠胎兒腦中水平較高,出生后快速下降,并在成年期保持較低水平[17]。研究表明,圍生期母體感染和缺氧均會影響胎兒大腦中KP 代謝產物水平和大腦發育,增加出現精神神經癥狀的風險[18-21]。早期神經發育中,α-7煙堿性乙酰膽堿受體(α-7nAchRs)、N-甲基-D-天冬氨酸(NMDA)受體等KP 代謝產物相關受體的功能障礙與ADHD、ASD 和SCZ 病兒的中樞神經發育異常關系密切[22-24]。本研究就KP 在兒童NDD 中的研究進展綜述如下。
1 KP的組成及相關代謝產物
1.1 KP 的組成色氨酸是人體的必需芳香族氨基酸。生理狀況下小部分色氨酸代謝成血清素,超過95%的色氨酸在吲哚胺-2,3-雙加氧酶(indoleamine-2,3-dioxygenase,IDO)和色氨酸-2,3-雙加氧酶(tryptophan-2,3-dioxygenase,TDO)的作用下首先代謝為中間產物KYN 并進一步產生喹啉酸、KYNA 和煙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AD+)等神經活性代謝產物[25]。KP是免疫系統的重要調節通路,其關鍵酶可被皮質醇和炎癥細胞因子激活[26]。KP 的特殊性在于它能夠同時產生具有神經保護作用和神經毒性的代謝產物。生理條件下,“喹啉酸分支”處于休眠狀態,KYN 優先通過犬尿氨酸氨基轉移酶(kynurenine aminotransferases,KAT)在星形膠質細胞中合成具有神經保護作用的KYNA;KYN 也可生成3-羥基犬尿氨酸后轉化為喹啉酸并最終分解為NAD+[27-28]。近年來的研究發現KP與炎癥-免疫失調過程的緊密關聯。干擾素-γ (INF-γ)、白細胞介素-1β (IL-1β)和腫瘤壞死因子α (TNF-α)等促炎細胞因子可誘導IDO 的表達上調[29-30];生理條件下喹啉酸/KYNA 的比例受到嚴格控制,其比值的微小波動可能導致嚴重的神經病理學改變[31]。越來越多的研究揭示了KP在神經發育過程中的作用,關注它在疾病狀態下的改變能夠為調控KP 治療兒童NDD 提供理論依據。
1.2 喹啉酸喹啉酸主要由活化的小膠質細胞和巨噬細胞產生。作為一種內源性NMDA 受體激動劑,喹啉酸主要通過抑制谷氨酰胺合成酶和星形膠質細胞重攝取谷氨酸具有興奮毒性作用[32]。過量的喹啉酸通過增強鈣離子的內流和蛋白激酶、磷脂酶、一氧化氮合酶等細胞損傷相關酶的活化,進而激活相關凋亡途徑[33-34]。有研究證實,喹啉酸也能夠參與活性氧形成,介導脂質過氧化,介導神經細胞損傷[35-38]。Rahman 等[39]在培養人原代胚胎神經元時發現,病理濃度(>100 nmol/L )的喹啉酸能夠調控蛋白磷酸酶(protein phosphatase,PP)1、PP2A、PP2B等PP上絲氨酸和蘇氨酸殘基的磷酸化,激活τ蛋白(tau蛋白),誘發神經毒性。
1.3 KMOKMO 是KP 途徑的關鍵酶,在腦中主要表達于小膠質細胞[40],也存在于外周組織(肝臟、腎臟和胎盤)的巨噬細胞中[41]。口服KMO 抑制劑Ro 61-8048 可以增加沙鼠海馬細胞外液中KYNA 濃度,并且應用該化合物在神經系統疾病的靈長類動物模型中能夠發揮神經保護作用[42-43]。Giorgini等[44]在KMO 基因敲除小鼠中觀察到,KYN 和KYNA水平明顯升高,3-HK和喹啉酸水平有所降低。以上表明,靶向KMO 在一定程度上可恢復KP 代謝產物的失衡。
1.4 KYNAKYNA 在腦內星形膠質細胞中由KYN 經KAT 催化產生,在神經系統疾病的體內外模型中發揮抗炎抗氧化的作用[31,45-47]。生理濃度的KYNA 通過拮抗α7nAchRs,抑制突觸前膜釋放谷氨酸;病理狀態下,KYNA 作用于NMDA 受體上的甘氨酸位點[半抑制濃度(IC50)10~30 μmol/L]和谷氨酸位點(IC50500 μmol/L),通過阻斷興奮性神經遞質傳遞,從而保護神經功能。GP35作為KYNA 的內源性配體,二者結合可參與調節膠質細胞中谷氨酸釋放、單核細胞外滲、炎癥反應以及細胞因子釋放等多種病理生理過程[48-49]。
1.5 KAT在人類、小鼠和大鼠的中樞神經系統中,目前已經分離出4種KAT的亞型,分別為KAT Ⅰ、KAT Ⅱ、KAT Ⅲ和KAT Ⅳ。其中,KAT Ⅱ高表達于星形膠質細胞,是大腦合成KYNA 的主要催化亞基[50]。Bortz等[51]發現,抑制大鼠的KAT Ⅱ能夠降低腦內KYNA 水平,提高認知能力。在嚙齒動物和靈長類動物中使用KAT Ⅱ抑制劑PF-04859989 可減少中腦多巴胺放電,改善認知功能,對苯丙胺和氯胺酮引起的感覺障礙也有緩解作用[52]。
2 KP在兒童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中的作用
2.1 KP異常與ASDASD是具有高度異質性的神經發育性疾病,特點是社交和溝通障礙、刻板和僵化的行為模式、興趣范圍狹窄等[53]。KP 的腦-腸軸受損進而誘發免疫炎癥被認為是ASD 的潛在發病機制[54]。ASD 病兒血漿和尿液中KP 改變以色氨酸水平降低、高 IDO1 活性為特征[55]。與正常兒童相比,ASD 病兒的 KYNA 血漿水平顯著降低,KYN/KYNA 比值顯著升高,喹啉酸過量蓄積,表明ASD病兒中色氨酸消耗較大,KAT 活性降低[54]。有研究者發現,ASD 病兒的臨床特征可能與小腦、腦干等多個大腦區域的小膠質細胞過度激活所導致的突觸功能受損相關[53]。作為ASD 的潛在致病因素,小膠質細胞過度激活的關鍵時期可能從胎兒期持續至早期發育階段[53]。流行病學相關研究表明,母體孕期免疫激活會增加后代患ASD的風險[56]。
2.2 KP 異常與癲癇癲癇是兒童期較為常見的神經系統疾病,以大腦神經元異常放電引起短暫中樞神經系統功能失常為特征,常伴有其他心理、認知和軀體合并癥[57-58]。既往研究證實,原發性癲癇病人和繼發于自身免疫性腦炎的癲癇病人的血清和腦脊液中IDO1 和KYN/色氨酸比值均升高;Deng等[59]在繼發性癲癇動物模型中觀察到,IDO1主要定位于小膠質細胞,下調IDO1 表達,血清和海馬的KYN 水平和KYN/色氨酸比值顯著降低。這些結果表明,IDO1 可能與繼發性癲癇的密切相關。同時Dey 等[60]在繼發性癲癇病人中發現,隨著癲癇持續時間、發作頻率的增加,KAT Ⅱ活性降低,內源性KYNA 合成減少,喹啉酸的從頭合成顯著增加,最終導致海馬細胞谷氨酸過度釋放。此外,難治性兒童癲癇發作頻率與KYNA 濃度有關,而生酮飲食可能通過誘導KAT活性從而增加KYNA的血漿水平[61]。
2.3 KP 異常與SCZSCZ 病因假說主要涉及神經遞質異常、神經發育障礙和免疫系統紊亂,但這些假說都不能完全解釋SCZ 病人的復雜癥狀和異質性。現有證據表明,在沒有身體傷害的情況下,心理壓力可以引起炎癥活動的顯著增加,而事實上近一半的SCZ 可被定義為“高炎癥/免疫生物型”[15]。SCZ 的KYN 假說基于腦內過量的KYNA 可以通過干擾谷氨酸能和膽堿能傳遞,間接影響多巴胺能信號傳導,從而導致SCZ 癥狀[31]。此外,SCZ 的認知障礙程度與大腦中KYNA 水平有關[62]。SCZ 伴隨的炎癥和氧化應激,通過誘導IDO而激活KP相關神經毒性級聯反應[63]。Zhang 等[64]發現,首發且未用藥精的神分裂癥病人外周血中IDO 水平升高,且IDO 水平與TNF-α、IFN-γ等促炎細胞因子水平和陰性癥狀呈顯著正相關。IDO 在大腦中的神經元、膠質細胞和巨噬細胞中廣泛表達,IDOrs9657182 等位基因的多態性與SCZ發病機制有關[63]。在SCZ病人的尸檢中發現,前額葉皮層中TDO2 的mRNA 表達量顯著增加[65]。在動物模型中使用TDO 抑制劑后,紋狀體中脂質損傷和羧基蛋白水平下降、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升高,海馬中羧基蛋白水平降低、過氧化氫酶活性升高。
3 總結與展望
作為連接內分泌、代謝、免疫等多種生理過程的紐帶,KP 失調通過誘導神經炎癥、興奮性氨基酸毒性、氧化應激等諸多病理生理機制,參與了多系統疾病的發生與發展。鑒于KP 的功能多樣性和在中樞神經系統中的重要地位,學者們進行了大量研究探索KP的激活途徑以及KP的重要酶和代謝產物所介導的神經損傷機制。最新的藥理學和遺傳學研究補充了代謝實驗的部分不足,提示通過靶向KP以恢復其代謝產物失衡,在未來預防和治療神經系統疾病中有巨大潛力。目前靶向KP 重要酶及產物的治療策略在神經系統疾病的體內外實驗中得到了驗證,例如,Murakami 等[66]發現托莫西汀可通過調節ASD 動物模型大腦額葉皮質中KYNA 水平,改善社會行為和(或)社會識別記憶受損;研究者在癲癇小鼠模型中觀察到,敲除IDO1基因能夠減輕神經元損傷、癲癇持續狀態后的炎癥反應和癲癇發作[59]。未來我們將進一步研究KP 在兒童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病理生理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爭取為臨床決策提供新的理論指導和實驗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