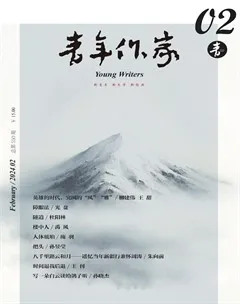困在極限時(shí)空里的人
徐福偉
極限境遇是小說(shuō)中經(jīng)常用到的一種時(shí)空設(shè)置方式,將人物推向有違于日常的,甚至極限的境遇中予以審視與考驗(yàn),以求立體化地呈現(xiàn)人性的復(fù)雜與多面性。作家龍一曾分享過(guò)塑造人物形象的秘訣,要不斷地“折磨”文本中的人物。我覺(jué)得設(shè)置極限境遇可能是“折磨”人物最為有效的一種方式了。
本期三部作品皆關(guān)注困在極限時(shí)空里的人。《把頭》最為成熟老到,關(guān)涉漁獵文化,圍繞生活在查干湖邊的蘇倫巴根一家三代捕魚人的命運(yùn)展開(kāi)敘事。蘇倫巴根的父親是漁把頭,為家族和孩子爭(zhēng)得了榮耀,但酒后卻被凍死在查干湖冰面上。蘇倫巴根在與父親徒弟爭(zhēng)奪把頭的冬捕比武中意外失敗了,郁郁不得志,直到十五年后潛入冰湖中成功摘掛子,獲得了頭魚的獎(jiǎng)賞,但在回家途中又遭遇土匪搶劫,好在保住了性命。最后,“蘇倫巴根用手拂去嘴邊的雪花,輕聲哼起了歌。‘查干淖爾呦,查干淖爾呦——”在這悠長(zhǎng)的歌聲中,蘇倫巴根徹底戰(zhàn)勝了自我的心魔,走出了困擾自身十五年的極限時(shí)空。兒子圖日樂(lè)為情所困,暗戀上了漁把頭的女兒,但懾于兩家冬捕比武恩怨,愛(ài)而不得,痛苦萬(wàn)分。在遭遇土匪搶劫的極限境遇時(shí)空中開(kāi)始成長(zhǎng)起來(lái),下一任漁把頭的新星即將冉冉升起。
《電梯時(shí)分》獨(dú)辟蹊徑,從乘坐電梯的日常生活切入敘事,以日常書寫反日常,在被困電梯里男女波瀾不驚的對(duì)話中勾連起了各自過(guò)往人生片段,含蓄而曖昧。兩個(gè)在原生家庭中缺少愛(ài)與親情的男女即將擦撞出愛(ài)的火花時(shí),電梯修復(fù)了,女人在十四樓迎來(lái)了接她的丈夫和孩子,男人也將女人留下微信號(hào)的紙條扔掉并又在無(wú)名指戴上了在褲兜里悄悄摘下的戒指。這個(gè)極具反諷的結(jié)尾處理巧妙地揭示出了被困在城市牢籠中的現(xiàn)代都市人人性中虛偽的一面,彼此戒備,也許只有在極限境遇的時(shí)空中才能打開(kāi)心扉,一旦回歸現(xiàn)實(shí)中,馬上變得冷漠起來(lái)。
《凜冬》以點(diǎn)帶面,通過(guò)塑造倒霉的外賣員形象,揭示出城鄉(xiāng)差距的擴(kuò)大化,進(jìn)而挖掘出了進(jìn)城打工的普通民眾對(duì)于未來(lái)幸福生活的向往與追求的精神內(nèi)核。肩負(fù)著要接鄉(xiāng)下的老婆和孩子來(lái)城里過(guò)美好生活重任的外賣員林東,連續(xù)遭遇丟車和被投訴的境遇,被困在了這一極限時(shí)空中。林東遷怒于投訴的女人,實(shí)施報(bào)復(fù),在接到即將分娩三胎妻子的電話后,幡然醒悟,開(kāi)始救贖行為。優(yōu)秀小說(shuō)在讓人看到生活的絕望之處時(shí)總會(huì)留下一道光亮,哪怕是一閃而過(guò)的微光。《凜冬》無(wú)疑做到了這一點(di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