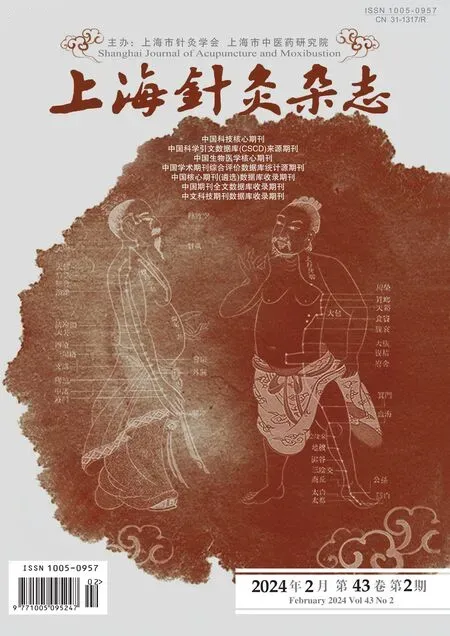林咸明教授針藥結合治療慢性蕁麻疹經驗介紹
徐詩婷,陳麗瑩,陳楊云,徐諾,林咸明,2
(1.浙江中醫藥大學第三臨床醫學院,杭州 310053;2.浙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三醫院,杭州 310005)
蕁麻疹是一種由肥大細胞脫顆粒介導的皮膚病,常導致紅斑、風團,臨床以瘙癢為主要表現,病程超過6 周為慢性蕁麻疹,感染、藥物、食物和心理因素是最常見病因,半數患者癥狀持續 2 年,20%患者可持續10 年[1]。由于發作的不可預見性及病程的遷延性,慢性蕁麻疹不僅是一種皮膚病,更是一種明顯損害患者生活質量的疾病[2]。目前針刺和中藥治療慢性蕁麻疹臨床療效明確,復發率低,不良反應少,可操作性強,治療本病具有優勢[3-7]。結合臨證經驗,林咸明教授主張針藥結合治療慢性蕁麻疹。針刺強調從神論治,以調神為先,用藥調體為本,循“開-調-收”之譴方思路,標本兼治,針藥結合共起疏風、調神、調體之效。筆者受業于林咸明教授,受益匪淺,現將導師經驗及理論特色整理如下。
1 明確病因,強調從神論治
慢性蕁麻疹歸屬中醫學“風疹”“癮疹”范疇,若發于眼瞼、口唇等皮膚疏松位置,又稱為“游風”。中醫古籍對癮疹的記載最早見于《素問· 四時刺逆從論》,“少陰有余,病皮痹隱軫”。《瘍醫大全·斑疹門主論》:“胃與大腸之風熱亢已極,內不得疏泄;外不得透達,怫郁皮毛腠理之間,輕則為疹。”癮疹中醫病因多為先天稟賦不足,或胃腸積熱,或病久耗傷氣血,血虛生風生燥,風邪外襲致玄府閉塞,營陰溢于脈外郁于皮下而生疹。
經過多年臨床實踐,林咸明教授發現慢性蕁麻疹患者多伴有情緒異常,且發作的次數、程度及病程與精神因素息息相關。有研究[8-9]結果也表明,與健康人比較,蕁麻疹患者更容易出現焦慮、抑郁等癥狀,而心理應激亦可使其加重。因此,林咸明教授認為“神亂”是慢性蕁麻疹反復發作的關鍵病機。形為神之宅,神為形之主。《周慎齋遺書》:“病于形者不能無害于神;病于神者,不能無害于形。”王冰言:“百端之起,皆自心生,痛癢瘡瘍,生于心也。”心主血,充血脈,主神明,又屬火,若心火傷神,神無所主,心神失常,是謂“神病”。心為陽臟而部于皮表,蕁麻疹作為皮表之患,皮損是“形病”,其伴發的焦慮抑郁情緒及失眠是“神病”,形神相依,皮膚瘙癢不止,心神失養,精神昏瞀,形神俱傷,互為因果。
“神亂”作為慢性蕁麻疹反復發作的關鍵病機,林咸明教授強調從“神”論治,認為元神和則陰陽和,陰陽和則氣血營衛和,營衛調和,臟腑氣血經絡得通,又能激發元神,神安則心安,心安則人安,人安則病愈。針刺在情緒疾病如焦慮癥、抑郁癥的治療上是積極的治療手段[10-11]。“調神針法”[12]是林咸明教授多年臨床實踐中得出的經驗配穴法,在皮膚病治療中收效顯著[12-14],通過改善神志異常,調養心神,緩解皮損狀態,形神兼治,促使疾病痊愈。
2 針以調神為先,神安則人安
2.1 重視瀉火調神
林咸明教授認為蕁麻疹患者血虛日久,肌膚失養而化燥生風,風氣搏于肌膚致皮損,反復遷延日久,血虛可致陰虛,使虛火內生于心。心陽過亢,火熱升騰,易灼傷絡脈,影響血運而加重蕁麻疹,形成惡性循環。同時心神失養,心血濡潤功能失常,心陰涼潤不能,心陽溫煦不能,陰陽失衡,會導致失眠、焦慮、抑郁等心神失常表現。除心主血之外,與血相關的還有肝和脾胃。肝藏血,肝陰不足,虛火上擾,亦會影響血運;且肝喜條達而惡抑郁,蕁麻疹患者多伴焦慮抑郁情緒,肝火偏盛亦會加重神機失常;脾胃化生血,胃腸積熱易引動風邪,郁久化火。因此林咸明教授調神注重降瀉心肝胃之火,選“安神六穴”降心火、調心神,取四關及腹四針清肝胃之火,進而總調腦神[14],從根源上治療疾病,減少疾病復發。
2.2 善用“安神六穴”以調神,提倡元神為先
調神針法,包括朝神、養神、安神3 部分,林咸明教授極力倡導元神為先。“調神針法”首先通過針刺枕部穴位以調腦神,配合包含耳針和體針的“安神六穴”。“安神六穴”即體穴迎香、安眠、足三里,耳穴心、肺、神門。《靈樞·官能》:“用針之要,勿忘其神。”機體的治神、守神狀態可促使中樞神經細胞功能的同步化,從而增強機體接受針刺刺激的敏感度[15]。林咸明教授針刺時重視醫患雙方積極性,即醫者專其神,患者安其神。頭者,精明之府。《標幽賦》中記載“凡刺者,使本神朝后而入”“既刺已,使本神定而氣隨”,因此林咸明教授針刺時會首先使患者集中精神,先于安眠穴“得氣”后出針,這不僅可以刺激腦部供血,也可達“朝神”之用。針刺安眠穴可有效調節腦電圖α波頻率[16],促使患者進入調神狀態。林咸明教授認為蕁麻疹以體虛為本,以風為使,風邪侵擾,上先受之,針刺頭部穴位,不僅可以疏風散邪,使邪有出路,還能通調腦神以達元神。耳穴作為脈氣輸注的另一種形式,有效溝通了耳廓皮膚表面與人體、經絡、組織器官。“諸痛癢瘡,皆屬于心”,耳穴心有養神和營之功;耳穴神門可安神鎮靜止癢;耳穴肺為治療皮膚病的要穴,起宣通肺氣、調理皮毛腠理之效;配合體穴迎香開竅通絡活血、足三里補益氣血,使患者氣血調達,人安神守。
2.3 取用四關穴以調陰陽
四關穴即合谷、太沖,既主陰陽又主氣血。陽明為多氣多血之經,合谷穴可清瀉火熱又與肺經相表里,又降脾胃之火,太沖主肝經又理氣調胃,二穴相配,達內外疏通,表里透達之功。血一氧化氮濃度對于評價蕁麻疹的臨床療效具有一定指導意義[17],血一氧化氮間接參與血管收縮、免疫應答與炎癥反應[18]。針刺四關穴能調節血一氧化氮濃度從而影響血管收縮[19],蕁麻疹的治療可從中獲益。林咸明教授認為取用四關穴不僅直接作用于機體免疫功能,同時也使氣機出入調和,營衛和降有序,血液運化有司,使神機通暢,達陰陽已通之效。
2.4 配合腹四針以調臟腑氣血
胃腸道屏障功能的失調易誘發異常免疫應答,可誘發蕁麻疹[20]。慢性蕁麻疹患者日久,氣血耗傷,臟腑功能易失調,因此,林咸明教授認為蕁麻疹以體虛為本。脾胃為氣血生化之源,為后天之本、升降之樞紐,蕁麻疹遷延難愈易損傷脾胃,脾胃虛損,正氣不固,風邪易侵,調整脾胃不僅充養氣血,也促其升降有調,寓標本兼治之意。林咸明教授在治療慢性蕁麻疹時常取腹四針(雙側天樞穴及中脘和關元穴)以健運脾胃,調達中氣,中氣健運則土和。天樞穴,為大腸之募穴,腹部之氣街,性善走而不守,通過針刺胃經穴位,也有益于激發胃經經氣以影響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而起免疫調節作用[21]。任脈行身前正中,為陰脈之海。任脈之中脘穴、關元穴以調和營陰而達止癢之效,同時中脘又為胃之募穴與腑會,又系手太陽、少陽、足陽明、任脈之會,可通調陰陽,祛風止癢。
2.5 隨證施治,不囿一法
林咸明教授認為慢性蕁麻疹病程日久,遷延難愈,病因多相互兼夾,主張在調神針法穴位組合的基礎上,隨證施治。風邪侵襲時安眠多換風池以疏風止癢,加用外關穴以祛風解表;胃腸熾熱加用曲池穴以清瀉陽明之熱,強調針刺時手法的重刺激,多采取捻轉瀉法;血虛風燥取三陰交、陰陵泉和太溪穴以養陰柔血,強調手法的輕刺激,多平補平瀉。同時林咸明教授認為“急病治病,慢病調體”,慢性蕁麻疹作為一種反復急性發作的自身免疫疾病,在診治過程中要分清緩急。急性發作期需“急癥急攻,祛邪為上”,取大椎和膈俞穴刺絡放血令“邪有出路”,且不用灸法;緩解期常取足三里溫針灸以厚脾胃之本,培補后天之土,防止疾病復發。
3 藥以調體為本,體健則邪不可干
林咸明教授認為蕁麻疹作為一種自身免疫性的過敏疾患,需用藥改善患者過敏體質,調養精神。林咸明教授治療慢性蕁麻疹主張“開-調-收”之遣方思路,方多用小柴胡湯加減,兼以分型論治加減藥物,再配合后期日常養護以促使疾病痊愈。
3.1 “開”以挫病勢,安心神
“開”為開先路、打沖鋒之意,以期直達病所,迅速起效。林咸明教授認為慢性蕁麻疹沉疴日久,急性發作時瘙癢難忍,多伴精神癥狀,為此,始方多用相對大劑量、藥勢峻猛之藥物以直達病所,配以性善走而不守之藥物,如大黃、路路通等以急攻之;用解表透邪之藥直趨病位,如荊芥、防風等;在劑量上,蕁麻疹患者病久耗傷氣血,虛熱內生,或是胃腸積熱以引動風邪,發病時全身風團處皮色紅,多夾火熱,林咸明教授會選用大劑量的黃芩、黃連等以清郁火、挫熱勢。瘙癢癥狀的迅速改善不但可以緩解失眠、焦慮等精神共病因素,也增強患者治愈信心及診療依從性。“開法”也與林咸明教授采用調神針法時先行刺激頭部穴位有異曲同工之妙,均先穩定患者情緒,防止心理應激誘發及加重蕁麻疹[9],有益于后期治療。
3.2 “調”以調體質,貫始終
“調”為調體質,意在鞏固療效。患者經過“開”的治療過程,病情得以控制,當考慮從“調”施治。林咸明教授認為蕁麻疹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療時需改變患者的過敏體質,從而改變易患狀態。免疫作為一種生理功能,通過識別“自己”和“非己”,作為機體的一種防衛系統。現代藥理學研究[22]證明,小柴胡湯可通過刺激免疫分子而發揮調節免疫的作用。《傷寒論》有描述“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小柴胡湯主之”,“血弱氣盡”即小柴胡湯證之根本病因。林咸明教授認為慢性蕁麻疹日久,雖然風為關鍵病理因素,但是病程遷延,損傷氣血,正氣虛損,邪氣易入,和小柴胡湯的“血弱氣盡”引起正氣不足、營衛俱損的病機相通。作為和法的代表方劑,小柴胡湯“和法”的理念與現代免疫系統的調控理念亦相通[23]。因此,林咸明教授治療本病時多用小柴胡湯加減。若少寐,煩躁甚者,加生龍骨、生牡蠣以重鎮安神;若疹塊遇風加重,多集中于頭面及手足,脈浮,多為風邪侵襲,加徐長卿、路路通、白鮮皮等疏風活血;若發作與進食明顯相關,平素嗜食肥甘厚膩之味,小便黃赤者,舌紅苔黃膩,多為胃腸熾熱,加大黃、黃芩等通腑瀉熱;若病久不愈,手足心熱,舌紅少苔,脈細弱者,為血虛風燥,加當歸、芍藥等養血潤燥。
3.3 “收”以穩療效,防復發
“收”字強調疾病后期的養護與調理,防止疾病復發。相異于初診時用量之大、藥性之峻猛,后期調整藥物及劑量以達“收”之效,如生姜多改用炮姜,加入清熱但善滋陰之石膏以收斂,調整大黃劑量或改用補益之劑調補脾胃,固護后天之本,如六君子湯加減。《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林咸明教授認為慢性蕁麻疹后期需配合改變日常習性達防治之效,如調節情志,培養良好生活習慣,盡量避免接觸致病源,忌食蝦、蟹、辣椒等刺激性食物等。同時血虛風燥作為蕁麻疹的病機關鍵一環,肌膚失于濡潤不利于蕁麻疹的治療,因此林咸明教授建議蕁麻疹患者日常生活應適時涂擦身體乳,兼防治之意。
4 醫案舉隅
患者,男,68 歲,于2021 年10 月26 日初診。主訴全身散在性皮疹瘙癢反復發作12 年,加重1 個月。患者12 年前無明顯誘因下出現全身散在性紅色皮疹,高出皮膚,基底潮紅,呈片狀分布,伴瘙癢,時輕時重,秋冬季節多發,未予系統診治。近1 個月上述癥狀加重,呈全身性發作,尤以腹部、四彎處顯,皮膚劃痕癥(+),就診時患者面色潮紅伴耳尖發熱發燙,尤以兩顴為重。胃納一般,情緒不安,夜寐欠安,大便偏干,小便無殊。舌紅苔少,脈弦細。西醫診斷為慢性蕁麻疹急性發作;中醫診斷為癮疹(血虛風燥證)。治則為瀉火調神,養血潤燥。調神針法聯合小柴胡湯加減。取安眠、迎香、耳穴(心、肺、神門)、合谷、天樞、中脘、關元、三陰交、足三里、陰陵泉、太溪和太沖穴。患者取仰臥位,穴位處碘伏棉球局部消毒后,選用0.25 mm×40 mm毫針,先于安眠穴處捻轉進針,得氣后出針;向鼻梁方向斜刺迎香0.3 寸;耳穴(心、肺、神門)垂直刺入 2~3 mm;針刺合谷時,囑患者手半握拳,直刺0.5~1 寸,提插平補平瀉至得氣;依次于天樞、中脘、三陰交和陰陵泉穴直刺1~1.5 寸,太溪直刺0.5 寸,均捻轉平補平瀉至得氣;太沖穴斜刺0.5 寸至麻脹感;選0.30 mm×50 mm 毫針,直刺足三里穴1~2 寸,向下斜刺關元穴1.5~2 寸,捻轉平補平瀉至得氣。留針30 min,隔日1 次,每周3 次。首診針后予大椎和膈俞穴刺絡放血。一診方用柴胡10 g,黃芩12 g,黨參10 g,姜半夏9 g,生姜6 g,大棗15 g,甘草12 g,當歸12 g,赤芍20 g,牡丹皮12 g,地骨皮15 g,制大黃12 g,路路通25 g,荊芥3 g,防風6 g。每日1 劑,水煎服,分早晚兩次服,共10 劑。2 d 后患者散在性皮疹紅色略有消退,瘙癢減輕明顯,兩顴及耳尖色溫恢復正常,4 d后患者皮疹紅色消退明顯,腹部紅疹全部消退,8 d 后患者散在性皮疹大部分消退,瘙癢減輕,四肢風團消退,不凸起于皮膚,情緒較前好轉。11 月9 日二診方為一診方去荊芥和防風,訴時有頭暈、口苦,遂加白蒺藜30 g 和龍膽草6 g,煎服法同前,共7 劑。11 月12 日復發1 次,左側臀腿分界線處可及紅色片狀風團伴瘙癢,其余皮膚未及。11 月13 日針畢后配合大椎刺絡放血,1 天后好轉。11 月18 日三診方為二診方去大黃,生姜改炮姜9 g,黨參加至20 g,加石膏30 g,共7 劑,煎服法同前。服藥期間配合針灸治療,囑患者及時做好肌膚保濕及調整飲食習慣。針灸14 次后,瘙癢癥狀基本控制,后減頻次至每周1次,針灸1個月后,全身皮疹消退,夜間睡眠改善,后期電話隨訪半年內未再發作。
5 小結
慢性蕁麻疹因其反復性、遷延性,影響患者日常生活,導致情志疾病,形神俱損,互為因果。本病以體虛為本,以風為使,常夾火熱,“神亂”是本病反復發作的關鍵病機。林咸明教授臨床治療本病注重針藥結合,以期身心同治,標本兼顧。針刺強調從神論治,“調神針法”以瀉火調神,“安神六穴”以調腦神,四關及腹四針調臟腑陰陽;不拘一法,隨證調整針刺方案;方用小柴胡湯,橫看兼雜諸證,隨證加減藥物,縱觀疾病特點,循“開-調-收”之譴方思路,提倡針藥結合以優化組合,縮短療程,達形神兼備、事半功倍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