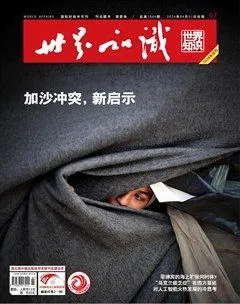歐盟首個國防工業戰略有何深意
呂蘊謀
3月5日,歐盟委員會公布《歐洲國防工業戰略》(以下簡稱“《戰略》”),同時還提出歐洲國防工業計劃(EDIP)的立法提案。這是歐盟首個有關歐洲國防工業的戰略,確定了明確的目標愿景和向戰時國防工業狀態轉型的刺激舉措,體現出了一定的防務獨立和戰略自主色彩。
五大措施提升國防工業能力
歐盟在《戰略》中明確了其國防工業發展的目標,即提出截至2030年,歐盟內國防貿易額占歐盟國防市場額比重應不少于35%,歐盟內采購份額占國防采購總預算比重應不少于50%,以及歐盟成員國至少40%的國防裝備采購應通過聯合采購進行。在上述目標的指引下,為向戰時國防工業狀態轉型,歐盟提出了增強國防工業響應能力和韌性的五大措施。
一是“更多、更好”的國防投資。《戰略》提出,要建立由成員國代表、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和歐委會代表組成的國防工業準備委員會,負責國防建設的統籌;出臺歐洲軍備計劃結構,為防務合作提供稅收減免;效仿美國“政府對政府”的軍售模式,建立歐洲軍售機制,設立歐洲統一的國防產品目錄和國防儲備庫,參考疫情期間促進疫苗生產的做法提出國防生產框架性合同等。
二是“更快反應、更有韌性”的國防供應生態。為援助烏克蘭,歐盟曾于去年出臺《支持彈藥生產法案》,以刺激歐洲補充國防儲備庫。但該法案屬于短期計劃,調整范圍也僅涵蓋彈藥及導彈。《戰略》則擴大了歐盟現有國防工業生產刺激計劃的范圍,且延長了時限。除支持生產外,歐盟還提出要支持“不熄火”的國防生產線和可改造的民用生產線,以便危機來臨時國防產能可以迅速跟上。歐盟還建議設立加速國防供應鏈轉型基金以幫助中小微國防企業獲得融資、建立歐盟防務產品供應安全制度等。
三是“更雄厚”的資金支持。在歐盟預算方面,EDIP提案提議增加15億歐元防務預算,并將俄羅斯在歐凍結的資產收益用于投資烏克蘭國防技術與工業發展。在金融機構支持方面,《戰略》建議加強對歐洲投資銀行的審查,調整貸款政策,放寬關于投資國防的限制性規定。
四是“更入流”的國防戰備文化。《戰略》認為,歐盟應當扭轉觀念,樹立“沒有和平就沒有繁榮”的新發展與安全觀。國防戰備文化還意味著調整歐盟現有的監管政策,協調科技、教培、綠色轉型、就業等其他領域宏觀政策的一致性,優化國防工業發展的大環境。此外,引導私人投資流向國防工業也是營造國防戰備文化的應有之義。

2024年3月5日,歐盟委員會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公布《歐洲國防工業戰略》并舉行新聞發布會,就加強歐盟國防工業能力明確了長期愿景。從左至右分別為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負責數字政策和競爭事務的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維斯塔格和歐盟內部市場委員布雷頓。
五是“更重協調”的對外伙伴關系。在烏克蘭方面,《戰略》提出要支持烏克蘭參與歐盟的國防工業計劃,包括參加聯合采購、產業升級、經驗交流等,還提議同烏召開國防工業論壇,以及在烏設立國防創新辦公室。在北約方面,《戰略》提出仍應將北約作為歐洲集體防御的基礎,并在循環經濟、裝備互操作性、氣候變化、新威脅等領域加強與北約的對話,提倡使用北約標準。
有內外兩個維度的動機
歐盟提速國防工業建設,有內外兩個維度的動機值得關注。根本性因素在內部,即歐洲國防工業能力與需求遠未匹配,歐洲的國防工業實力總體發展較慢,掣肘因素較多,突出體現為三點。
第一,投資不足。冷戰后,歐洲長期享有和平紅利,更重視將有限的資金投入國防外的其他政策領域。雖然從北約3月14日發布的2023年度報告來看,歐洲的國防投資已迎來連續九年的增長,但與世界其他主要力量的投入相比,仍不在一個量級。2023年美國的國防開支占北約總開支的67%,俄羅斯近期則宣布將把“近三分之一的國家支出用于國防”。底子不好,增速不足,歐洲的國防實力與美、俄的差距恐將越拉越大。
第二,內部缺乏協調。當前,歐盟成員國在國防能力建設方面的協調、統籌與合作明顯不足,本國利益優先、重復建設、低效投資現象較為普遍,部分成員國甚至刻意隱藏自身的國防能力建設進程。歐委會此前發布的研究報告披露,因重復建設,歐盟國防預算總額中有近30%的資金遭到浪費。同時,歐盟雖早在2007年就設定了歐盟內聯合國防裝備采購應占采購總額35%這一標準,但截至2022年,該項占比的實際水平仍僅達18%,可以說遠未及格。此外,比起歐盟內部生產的國防產品,很多成員國對“盟外貨”表現出明顯的偏好。數據顯示,雖然歐盟整體國防開支連年增長,但自烏克蘭危機爆發至2023年6月,78%的成員國國防采購資金流向歐盟外,其中流向美國的資金就占采購總額的63%,而歐盟自身的防務產業卻未得到新增軍費的有效潤澤。為此,法國等國頻頻發出“購買歐洲貨”的呼聲,力推在各項援烏或者防務政策中加入“購買歐洲貨”的條款,此次出臺的《戰略》便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了此種立場。
第三,對外依賴嚴重。歐洲國防市場的碎片化特征顯著,國防產業的供需兩端均存在較為明顯的對外依賴。一方面,部分成員國存在明顯的進口依賴。數據顯示,歐盟去年新增的防務裝備僅有25%在歐盟內生產,75%從歐盟外采購。正如前歐盟軍事參謀部總參謀長佩魯什所言,“防務自主是戰略自主的前提”,“如果歐洲連最微型的武器系統、配件都要依賴外部供應,戰略自主必會困難重重”。另一方面,歐洲軍工企業存在出口依賴。當前,歐洲的軍工企業需在狹小、分化的成員國個體市場而非歐洲一體化大市場中競爭、生存和發展。需求側影響供給側,歐洲企業普遍對歐盟內防務研發、采購、生產合作興趣不足。還有些企業為了生存,不得不將重點放在出口上,嚴重依賴對外訂單,給歐盟國防供應安全埋下隱患。由此,歐盟希望通過此次出臺的《戰略》彌補上述存在的內部問題。

2024年1月19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瑟堡視察海軍基地,并敦促法國國防工業加快向“戰爭經濟模式”轉型。
刺激性因素在外部,即對俄羅斯的恐懼與對美國的焦慮持續交織,當前的歐洲既是“防俄歐洲”(Russia-proof Europe),也正在變成“防特朗普歐洲”(Trump-proof Europe)。首先,隨著烏克蘭危機的延宕,歐盟視持續對烏軍援為優先政策事項,而資金、供應能力與政治意愿則是影響援烏的三大核心因素。其中,若無與需求匹配的國防供應能力,再多的資金與意愿都只會導致“肥水流向外人田”。其次,歐洲評估認為,未來幾年俄羅斯直接進攻北約的可能性有所上升,歐洲自身已開始感受到生存威脅。歐洲部分學者甚至拋出“俄羅斯將在美國大選后至2025年初期攻擊波蘭和立陶宛之間的蘇瓦烏基峽谷”這樣貌似言之鑿鑿的觀點,讓歐洲更加緊張。最后,歐洲的安全壓力上升,而美國的安全保障意愿卻不斷探底。將自身的發展與安全“交給美國搖擺州的五萬選民決定”,顯然不是歐洲的理性選擇。因此歐洲媒體普遍認為,減少對美國的依賴是歐盟出臺《戰略》及相應立法提案的重要動機之一。
能否有效執行受三方因素影響
放眼未來,《戰略》及EDIP能否幫助歐洲防務強起來,仍需關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支持資金規模。在EDIP提案中,歐盟提出要為國防工業發展增加15億歐元的支持。這一數額顯然不足以支撐歐盟的防務雄心,距離歐盟內部市場委員布雷頓前期預想的1000億歐元差距仍較大,歐委會執行副主席維斯塔格也承認這“不是一個大數目”。因此,歐盟少量公共資金能否如愿對私人資金起到帶動作用,將成為一個重要觀察點。歐盟設計的其他財政工具(如使用俄凍結資產的收益、聯合發行國防債等)能否落地,也值得持續關注。這些或將成為下一屆歐委會的政治責任。
二是成員國政治意愿。EDIP作為歐委會行使立法動議權而提出的條例提案,目前需依照歐盟立法程序,經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通過才能生效。在這一進程中,成員國的政治分歧及博弈將集中爆發。當前看,成員國對于歐盟機構插手國防與國家安全這一最敏感的主權事項態度仍較謹慎。此外,使用俄在歐凍結資產收益等具體事項在成員國間也遠未達成一致意見。
三是美國及北約因素。美國向來是歐洲防務能力建設的關鍵影響因素,美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皆曾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深度影響過歐防務聯盟的走向。目前,美國似乎有意讓歐洲對自身安全擔負更大責任。但由于本次涉及歐洲計劃建立獨立甚至與美存在競爭關系的國防生產供應鏈,美國的態度料將更為復雜。美“政客”新聞網也評論稱,《戰略》“對美國軍火商而言顯然不是個好消息”。同時,北約在去年的維爾紐斯峰會上也提出了國防生產行動計劃,北約版計劃與歐盟版計劃是互補還是競爭,歐盟與北約間關系將往何處去,也有待進一步觀察。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歐洲安全項目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