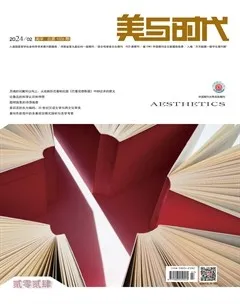論魯迅的科學認識和神思

摘? 要:以往關于魯迅神思與科學的研究,大多關注它們的相通性,但它們之間的差異也值得探討。在魯迅的思想中,懸擬、學思與科學指向客觀世界的真理,而神思、文學和宗教則使人體悟到美與人生。魯迅把它們當作人類歷史中同等重要的組成部分,認為它們缺一不可,不分高下,同時他又劃定了它們各自的范圍,并針對彼此越軌的現象進行了批判。魯迅認為調和它們的方法則是不局限于其中一個領域,對它們并行接受。
關鍵詞:魯迅;神思;科學
科學與文學作為魯迅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貫穿他的一生,它們相輔相成、相互滲透,皆為魯迅“立人”與“救國”理念的核心。在早年的《科學史教篇》《文化偏執論》《破惡聲論》等論文中,“神思”作為一個重要的概念不僅對科學發展產生重要作用,而且也在宗教、藝術等領域發揮效用。魯迅提出的“偽士當去,迷信可存”,更是對宗教等非科學思想進行了辯護,肯定了其積極作用。
然而,在中后期,魯迅雖也有肯定宗教和迷信的方面,但更多地是對偽科學認識進行批判,這與當時中國的社會環境和他的啟蒙目標有關。事實上,魯迅對宗教和迷信的肯定和批判可以從另一個維度來看,那就是想象力對人的認識的作用。
在歐洲,還有另一位傾其一生探討詩學、想象力和科學認識的人,他就是法國哲學家巴什拉,他用十幾本著作論述科學哲學、想象哲學,開辟了新的領域,對法國的思想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因此,本文欲以互文理論與巴什拉的科學哲學為方法,以想象力與科學認識的關系為切入點重新審視魯迅的科學、宗教和文學思想。互文理論著眼于魯迅的思想整體,對其文本的前后指涉進行梳理,以其自身思想闡釋自身;巴什拉的科學哲學則力圖與魯迅的思想進行雙向闡發,當然,巴什拉與魯迅的時代雖然有一部分重合,但二人的視角、所處的社會環境、發展的方向并不相同,即使是用一個術語與概念也有不同的意義,但二者異中有同,其對于偽科學認識的批判、對想象力的肯定都極具價值。因此,對二者的思想在比較視域中進行雙向闡發,是一件可行的事。
一、魯迅的科學、文學與宗教之范圍
“神思”作為一個關鍵詞頻頻出現在魯迅早年的論文之中,在《人之歷史》《破惡聲論》《科學史教篇》《摩羅詩力說》《文化偏執論》中皆有出現,在魯迅的科學、文學和宗教思想中都具有重要地位。這與他的立人思想有關。他一方面向中國引介科學思想,另一方面又肯定宗教、文學對個人和社會的積極作用,想要以此培養不偏不倚的個人。“神思”作為人的主體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會受到魯迅的重視。
有關魯迅“神思”觀念的研究,學界已經進行了充分的探討。日本學者伊藤虎丸認為,魯迅的科學觀中宗教、神話和科學都是由神思所創造的,這意味著魯迅把科學看做“人”的自由精神的產物,把科學史看做人的精神史[1]15。他認為就魯迅而言,科學與“迷信”是一脈相通的,而不是對立的。使它們相通的,就是“神思”[1]23。王衛東則認為,魯迅這里與“學”之思相對的“神思”應是指人類在知識起源處神話、宗教和哲學所共用的想象力,而“學”之思則為近代意義上的科學知識[2]。
因此,關于魯迅思想中神思與科學的相通點,已經大體明了,但現在的問題在于魯迅思想中科學的客觀知識、神思和迷信之間是否存在界限?如果有,在哪里?此外,魯迅神思是否是那種無拘無束、脫離一切的空中樓閣?迷信又是如何成為科學的對立面的?事實上,通過考察,筆者認為魯迅的思想存在著分界線,那便是他自覺的學科思維,通過劃分,魯迅認為科學、文學和宗教雖然可能有相同的認識對象,但是在方法上和思維上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論。此外,任何學科都是有范圍的,一旦超過自己的適用范圍,科學、文學和宗教就會成為對方的發展阻礙。魯迅也沒有設定那個學科更加重要,在他看來,科學、文學應該并行不悖,都是青年所應當具有的素養。
想要進一步闡述上述問題,首先,我們要重新考察一下魯迅的“神思”“迷信”和“懸擬”之間的相互關系。
1907年,魯迅的《人之歷史》問世,是對當時生物學前沿理論的科普之作,雖然此前已有《中國地質略論》這篇涉及科學的文言論文,但是真正涉及到科學方法和科學史觀的應當是《人之歷史》。在這篇文言論文中,魯迅考察了進化論的演變,在開篇第一句,他認為“進化之說,煔灼于希臘智者德黎(Thales),至達爾文(Ch.Darwin)而大定。”[3]8在這里魯迅將進化學說的源頭追溯到古希臘時期,顯示出后面《科學史教篇》中科學史觀的萌芽。還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在這篇文章中對于神話和妄信的否定,他認為盤古、女媧等有關天地、生命起源的中國古說皆為“神話之歧途”,而神造說更是“景教之迷信”,而進化論之成,自破神造說始[3]13。可以看到魯迅在這里將神話和傳說當成迷信和妄信,它們阻礙了客觀認識的進步,而科學的進步是從破除迷信開始的。也就是說,迷信之所以遭到魯迅的否定就在于其對于客觀世界的認識已經落后,應當被排除到科學之外。而迷信能夠被排除則在于實踐和正確的科學方法,在《人之歷史》中最鮮明地體現這一點的人是達爾文和海克爾。
魯迅認為達爾文之所以能使進化論大成,則在于他使用內籀也即歸納推理法,通過觀察和搜集事實,建立了“達爾文學說”。海克爾則相對更多依賴懸擬。魯迅認為海克爾的種族發生學向上探究的歷史久遠,很多證據已經無法直接觀察,必須要靠間接推理與批判反省。并且,如有證據不足的地方,海克爾使用了化石和懸擬的物種來彌補。懸擬即揣摩想象,也就是說,魯迅同意海克爾采取想象的生物來充當科學的證據,在《人之歷史》的最后,魯迅更是根據耐格里對無生物世界和生物世界之間界限的消解,以及法國學者把非生物變為生物的實驗,預想未來會出現宇宙發生學。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魯迅似乎更加偏愛“懸擬”這一方法。
魯迅在《人之歷史》中對內籀和懸擬的看法在《科學史教篇》中延續下來,他認為培根對內籀的強調在于之前的懸擬夸大之風,而懸擬雖然培根不喜歡,但對于科學的發展也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正如王德威所說,魯迅雖然肯定科學的重要,但不以經驗主義,以及緣由內籀(歸納)法形成的實證科學為然。魯迅提出“懸擬”作為調和,而“懸擬”關乎假設與想象[4]。
那么科學的想象與文學的想象的相似和不同是什么?或者說,懸擬與神思之間的相同和區別是什么?
首先談相同點。在魯迅看來,科學作為對客觀對象的認識,其假說或者說懸擬必須建立在客觀的證據之上,其必須能得到驗證,不管時間是在將來還是在現在,它必定是可實現的,符合客觀世界的規律。而神思作為宗教、神話和文學產生的主體源泉,其也是唯物的,無法脫離客觀世界而獨立存在。
在他看來,神話的誕生是“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則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異”[5]32,而宗教的產生是古人“大觀天然,懷不思議,則神來之事與接神之術興,后之宗教,即以萌孽”[5]29。詩則是古民神思與自然萬物相合相同的產物,也就是說,神話同樣是對于客觀世界的一種認識,只不過這種認識得到了想象力的加工。宗教就是在這種加工的基礎上產生的,而文學也是如此。文學想象同樣是建立在現實世界的基礎上,無論什么樣的天才,其神思都無法創造出世界上完全沒有的東西。魯迅認為:“天才們無論怎樣說大話,歸根結蒂,還是不能憑空創造。描神畫鬼,毫無對證,本可以專靠了神思,所謂‘天馬行空似的揮寫了,然而他們寫出來的,也不過是三只眼,長頸子,就是在常見的人體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長了頸子二三尺而已。”[6]綜上所述,魯迅的神思并不是一種空想,而是和自然、物質緊密結合的創造性想象。這讓我們想起《人之歷史》中,進化論思想的建立與化石、現實物種觀察以及海克爾種族發生學與懸擬之生物的關系,或許可以說魯迅的神思與懸擬之間有著糾纏不清的關系。
而二者之間的區別,魯迅在早期論文最早提及神思的時候就做出了區別。在《科學史教篇》中,魯迅認為:“蓋神思一端,雖古之勝今,非無前例,而學則構思驗實,必與時代之進而俱升。”[7]26在這里,魯迅認為神思并不存在進步這一概念,不會隨著歷史的前進而發展,而科學需要設立假說,并且驗證這一假說,因此會隨著時代的前進而發展。以往的研究大多傾向于論述神思與學之思的相通性,但其實二者之間的差異也值得討論,因為它涉及到魯迅思想中科學的適用范圍。那么學之思與神思是一個東西嗎?縱觀《魯迅全集》可以發現神思的應用與神話、宗教和文學緊密相連,神思或許作為人之精神的組成部分與學之思相通,但神思無法產生近代意義上的科學。神思可以沒有進步的概念,但學之思必須要有。并且隨著時代前進的不只是實證知識的積累,學之思也是。在《人之歷史》中,進化論便是學之思,其發展脈絡則從泰勒斯的生命起源于水,到“別動說”“形蛻論”、蘭麻克之論、達爾文的進化論、終至海克爾的種族發生學。因此,學之思要沿著一條軌道前進,而防止其越軌的方法則是用實驗驗證,而學之思的盡頭則是對于客觀世界正確的認識,在發展過程中也必須以此為標準。而神思則不需要,在魯迅看來,它可以不符合客觀世界的正確認識,但前提是能滿足人們的形而上需求。考察完神思和懸擬的區別之后,便可以進一步來談談魯迅給宗教、文學和科學各自劃定的學科范圍。
魯迅在《科學史教篇》中認為:“蓋科學者,以其知識,歷探自然見象之深微,久而得效。”[7]25也就是說,科學是對于自然現象的客觀知識,他認為希臘羅馬的科學學說雖然有錯誤,但卻具有和近代一樣的探索未知和自然的科學精神。而亞刺伯的科學停止進步、迷信叢生的原因則是亞刺伯人失去了求索精神。到了基督教獨尊的時期,科學更是遭到排斥遏制。但與之前的《人之歷史》不同,魯迅并沒有把宗教的迷信和神話當作科學認識的阻礙加以否定,反而肯定了它的合理性。他提出:“蓋無間教宗學術美藝文章,均人間曼衍之要旨,定其孰要,今茲未能。”[7]29在這里,魯迅雖然考察的是科學的歷史,但卻是以人文的整體視角來觀照西方精神的演進,宗教、科學、文學全都占據著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不同的領域共同推動人類歷史的進步。因此,在《人之歷史》中無法容忍的神話和迷信在此具有了合理性,它們雖然阻礙了科學認識的進步,但是在其他方面卻另有用處。最后,魯迅提出了科學的極限:“蓋使舉世惟知識之崇,人生必大歸于枯寂,如是既久,則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謂科學,亦同趣于無有矣。”[7]35科學是對客觀世界真理的追求,美感和人生應當交給宗教和文學。科學、宗教和文學應該并行不悖,而不能彼此越軌。
在《文化偏執論》中,魯迅認為那些為了救國而盲目接受西方眾治思想的人和那些患了重病不去求助醫學反而向巫術和神力祈禱的人一樣。神力和巫術在這里被否定是因為它們超出了自己的適用范圍,對于身患痼疾的人,醫學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神話和巫術脫離了其產生的根源,變成了阻礙客觀認識的成見。這也是后來它們屢屢遭到魯迅批判的原因。
對于科學超出其適用范圍的情況,魯迅也給予了批判,在《破惡聲論》中,魯迅認為那些偽士奉科學為圭臬,“不思事理神閟變化,決不為理科入門一冊之所范圍,依此攻彼,不亦傎乎。”[5]30他們不知道科學有它的極限和范圍,盲目運用,用動物學的知識否定神龍的存在。在魯迅看來,神龍是中國古民神思所創造的,有關它的討論應當放在文學和神話研究中,鄭重其事地用科學對神龍的價值進行否定和嘲笑,反而顯得偽士們自己愚蠢。在《摩羅詩力說》中,魯迅對于科學和文學的界限進行了進一步的劃分,他引用了約翰·穆勒的話:“近世文明,無不以科學為術,合理為神,功利為鵠。”[8]74魯迅認為文章也是如此,原因在于它能涵養人的神思。除此之外,文章還能“啟人生之閟機,而直語其事實法則,為科學所不能言者。所謂閟機,即人生之誠理是已”[8]74。之后魯迅使用了一個比喻,熱帶人沒有見到冰前,即使告訴他冰的科學定義,但他還是不知道冰是什么樣子,而把實物放在他眼前時,他就會立刻明白冰塊是什么。魯迅認為文學能啟發人生也是同樣的道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魯迅把握到了純粹的科學知識是一種對于實體的抽象概括,其脫離具體對象后很容易變成空洞無物的概念,因此,科學及其抽象思維無法把握人生。而文學可以,魯迅看到它與神思、形象思維的聯系,認識到其可以使人直觀地感受到人生的道理。此外,科學和文學關于自然和美的看法也有差異。科學對于自然是想要控制它并認識它的法則,文學和詩才能引導人進入到美之境界。因此,魯迅思想中科學和宗教、文學的范圍已經明了,而此后魯迅對于科學和文學、宗教相互越軌的批判與其前期思想實則是一脈相承。
二、迷信的二元性
科玄論戰在中國近代思想發展史上是一件大事件,而那場論戰中魯迅卻選擇了缺席和沉默。這個異常近來已經有學者做出了解釋,有的根據對他前期思想的考察,認為魯迅缺席的原因在于科玄論戰的問題他已經說過,而有的學者經過考察則認為魯迅并未沉默,而是創作了《祝福》這篇文本進行回應。
事實上,《祝福》中隱藏的信息確實不能僅僅是宗法制對婦女的扼殺這一種解讀可以囊括的,倘若將范圍擴大一點,聯系魯迅創作文本的整體,或許可以看到其相互指涉的內在聯系。
在《祝福》中有一個暗線一直縈繞在敘述者與讀者周圍,那就是祥林嫂所問的靈魂的有無。圍繞這一點可以展開多種談論,倘若回顧魯迅前期的思想就可以對敘述者的沉默早有預料。正如先前所說,魯迅認為僅僅科學無法解決人生之誠理,在他看來,靈魂這一概念是由于人們形而上的需求所產生的,不能用科學進行分析。因此,敘述者無法僅用科學啟蒙來解決這個問題。或者說,形而下的回答無法解決形而上的問題。實際上,《祝福》與魯迅的另一篇文本《我之節烈觀》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而且關于科學、迷信和人生觀的問題在那里面也有所探討。
在1918年的《我之節烈觀》中,魯迅認為《新青年》上對虛君共和、靈學派的駁論“都是《新青年》里最可寒心的文章”[9]121。其與辯地球方圓的文字相差無幾。在魯迅看來,無論是康有為的保皇說,還是靈學派的鬼神論早就應該被否定,消失在時代的推進中,正如“地方說”一樣。然而其活躍至今,并且還需要《新青年》特意發文反駁,這實在是讓魯迅感到寒心且害怕。魯迅對靈學派倡導的鬼神之說進行了決絕的否定,然而并不是說魯迅簡單地反對靈魂的存在,他反對的原因在于靈學派將鬼神當作道德的根本。而早在兩個月前,魯迅就看到傳統道德與鬼神之說結合對女性的壓迫和戕害:“只有說部書上,記載過幾個女人,因為境遇上不愿守節,據做書的人說: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獄;或者世人個個唾罵,做了乞丐,也竟求乞無門,終于慘苦不堪而死了。”[9]127這段話或許便是《祝福》故事的思想來源之一。在《隨感錄三十三》中,魯迅認為能救中國的只有這鬼話的對頭的科學[10]318!原因在于“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10]314。這里指的科學并僅僅是對于自然的客觀知識,還包括先前的懸擬和學之思。而這一點在《我之節烈觀》中有所體現。魯迅根據社會提倡節烈的思想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采用的論述方法是先提出疑問,然后再根據事實和道理進行解答。如魯迅先向讀者反問:為什么救世的責任全由女子承擔?然后他條理清晰地依次作答:按照陰陽的舊說,女子是“陰類”,是主內的,是男子的附屬品。然則治世救國,正須責成陽類,全仗外子,偏勞主體。決不能將一個絕大題目,都閣在陰類肩上[9]123。而按照新說,男女平等,義務略同,縱令該擔責任,也只得分擔。其余的一半男子,都該各盡義務。不特須除去強暴,還應發揮他自己的美德。不能專靠懲勸女子,便算盡了天職[9]123。按照這樣的方式,魯迅抽絲剝繭,否定了支持節烈的舊日常識,并闡述節烈的發起原因、歷史發展以及不改革的緣由等有關節烈的內容。每一個觀點前都有問題作為引子,而每一個問題的解答都有事實和邏輯作為依據和支撐,事實上,問題的提出本身便可以看到魯迅的科學思維。這篇文章便是魯迅對祥林嫂節烈困境的回答。
事實上,如果回到《祝福》的文本世界,可以看到最終導致祥林嫂精神塌陷的不是迷信和宗教,而是其對尊嚴和愛的需要被傳統的宗法道德無情地踐踏。迷信和宗教客觀上還給予了她一個擺脫心靈上負罪感的機會。在文本中,柳媽媽告訴祥林嫂因為她嫁了兩個丈夫,所以死后會在地獄里被分成兩半,唯一的辦法是捐一條門檻當作替身。祥林嫂照做了,她捐完門檻以后,“神氣很舒暢,眼光也分外有神,高興似的對四嬸說,自己已經在土地廟捐了門檻了。”[11]20然而,當她在祭祖那天坦然幫忙時,四嬸卻說:“你放著罷,祥林嫂!”[11]20祥林嫂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燭臺,只是失神的站著[11]20。
可以看到,迷信和宗教為祥林嫂打破原本的境遇提供了一條出路,祥林嫂徹底受到打擊則是因為這條出路不被四嬸承認。四叔禁止祥林嫂去碰祭祖用的東西是因為她“不干凈”,而祥林嫂也察覺到了這一點,門檻成為了她贖罪的替罪羊,承擔她的“不凈”。但四嬸的否定卻讓她最后的嘗試化為一場空,戕害祥林嫂的是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因此,文中的敘述者雖然接受了科學啟蒙,但他所具有的科學常識無法使祥林嫂得到解脫,因為他缺乏與傳統宗法道德直接對抗的勇氣。單純的常識啟蒙無法觸及到祥林嫂困境的核心,柳媽媽的“鬼神說”雖然是迷信,卻客觀上為祥林嫂打開了“贖罪”的通道,但傳統宗法道德的根深蒂固和無孔不入還是讓祥林嫂陷入絕境。魯迅早期思想中對于宗教和迷信的矛盾態度也在這里顯現。
然而,迷信在魯迅中后期思想中更多地還是作為批判對象,原因在于它對客觀認識的進步造成了阻礙。
《長明燈》中的主角執意要吹滅廟里的長明燈,認為這樣就不會有蝗蟲和病痛。但正如文中反對者所回答的:“就是吹熄了燈,那些東西不是還在么?”[12]63熄滅長明燈并不能解決蝗蟲和豬瘟的問題,因此,這一行為更多地只是具有象征意義。
金修森在分析巴什拉的“認識論障礙”中認為:“謬誤比無知更有害。如果只是無知,那么基于尚未對其進行研究的事實,問題就一直停留在中立狀態。但是在謬誤的情況下,問題卻被掩蓋了,表現為已經解決的問題和不存在疑問的問題。……無知只是對未解決的對象置之不理,而謬誤則是把它隱藏起來。”[13]長明燈是迷信,也是謬誤,村里的人相信如果吹滅了它,村子就要變海,所有人就要變成泥鰍。事實上,主角也知道熄滅長明燈無法解決蝗蟲和豬瘟,但他只能先這么干:“我知道的,熄了也還在。”“然而我只能姑且這么辦。我先來這么辦,容易些。我就要吹熄他,自己熄!”[12]63那么,在魯迅看來,什么辦法可以解決豬瘟和蝗蟲呢?自然只能是靠科學,靠學之思和知識的進步才能解決客觀世界的認識和問題。長明燈是迷信的化身,它的危害在于以一個無法證實的錯誤見解使得村子固步自封,村民更是以玄虛錯誤的認識指導自己的實踐。因此,主角吹滅長明燈,便是將認識從錯誤的迷信中解放出來。這樣,人們便會重新回到“無知”的狀態,繼而向未知處進行探索,終有一天豬瘟和蝗蟲的問題能得到徹底解決。
除此之外,迷信的危害還在于其對“學之思”的領域造成了干擾,以錯誤的知識指導實踐,從而導致現實中的許多悲劇和愚行,而魯迅對此的批判則集中在醫學上面。
魯迅在父親生病時接觸到了儒醫,而他自身也因為拔牙的事情對中醫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事實上,到后來他也認識到傳統中醫也是實證經驗積累而來的醫學。魯迅看到雖然《本草綱目》里有部分不實的記載,但大部分藥的功用卻都是古人一點點探索而來的。因此,魯迅對迷信危害的批判其實是落實在對那些將醫學和玄學結合、客觀知識與玄虛結合的人和事之上。
魯迅回憶為父親治病的時候,特意提到了藥引和醫命之事。事實上,藥引在中醫中確有用處,但是到了梧桐葉和敗鼓皮丸的使用時就帶有迷信的成分了。“只在舊方上加了一味藥引:梧桐葉。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醫者,意也。其時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氣。其先百藥不投,今以秋氣動之,以氣感氣”[14]295,梧桐葉的使用是因為其帶有秋氣,而當時是秋天,因此它可以使其它藥物發揮作用。而敗鼓皮丸“是用打破的舊鼓皮做成;水腫一名鼓脹,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14]296因為水腫又名鼓脹,所以打破的鼓皮便具有克制它的作用,但鼓脹只是水腫的外在表現,而不是它的病因,并且能指與所指的關系是社會性的、任意的。打破的鼓皮與鼓脹的聯系是能指系統和直觀形象上的,不能得出對實際的治療產生幫助的結論。最令魯迅念念不忘的,則是陳蓮河認為應該請人為魯迅的父親看命:
有一回陳蓮河先生又說,“我想,可以請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許是前世的事……”[14]297
醫學與玄學結合在一起,病人的病與其前世的道德有關,這件事讓魯迅印象深刻,以至于他后來的小說中出現了相似的情節。《弟兄》中中醫的那句“可以醫。不過這也要看你們府上的家運。”[15]便是魯迅對其的諷刺與不滿。
事實上,迷信作為一種錯誤的認識,是對客觀對象的扭曲,其產生有著主體的主觀根源。巴什拉通過對前科學時代偽科學知識和文獻的考察,提出了認識論障礙這一概念:認識論障礙并不是認識對象的復雜性和人類精神方面的弱點,而是認識行為的本身——深入地認識——迫于某種功能性的必須,出現了緩慢和紊亂[16]9。
在巴什拉看來,想象固然能激發科學家的靈感,然而和隱喻、形象一樣,其也是科學發展中的認識論障礙。人的心靈將客觀物質增值,以此阻礙了科學的發展,他認為只有靠抽象精神才能把握到科學的精髓。
關于魯迅所批判的迷信,正好可以采用巴什拉的科學哲學來進行深入考察。那些錯誤的產生與想象有著密切的關系。
“所以月經精液可以延年,毛發爪甲可以補血,大小便可以醫許多病,臂膊上的肉可以養親。”[17]魯迅將它的源頭歸結于道學家的“萬物皆備于我”以及萬物之靈的思想,認為正是這種主觀唯心的態度,使得人體的分泌物和產物被提高到不應具有的高度。《狂人日記》和《藥》里提及的人血饅頭,或許也是這種思想的產物。事實上,關于類似的迷信,西方也存在,巴什拉便對這種思想展開了分析和批判,他首先引用了相關的文獻:
幾乎不可設想,在18世紀的藥典里還保留著如百花水和狗屎這類藥物。百花水只是蒸餡奶牛糞便的產品……喬弗洛瓦的《醫學材料》一書同樣缺乏批評,他建議用老鼠屎來治便秘,用它在體外治疥瘡,用蜂蜜和洋蔥汁調和在一起可以使人長頭發。[16]187
然后,他對一系列相關的材料進行了分析。他認為糞便的重要性與消化的神話有關,與精神分析學說肛門期的占有感存在聯系。他認為關于糞便的學說是強烈的多功能增值,并且是一種反向增值。人們不愿意相信一種天然產品的臭味是本質性的。人們欲把一種客觀價值賦予已經克服個人厭惡這個事實,人們欲贊賞并受人贊賞。為了讓反價值具有某種價值,人們動用了一切[16]189。認識論障礙的產生是由于人的精神與無意識對客觀事物的增值,貪婪和占有的心態使得糞便作為令人厭惡的事物反而具有了治病和美容的效用。
此外,還有魯迅多次提及的拔牙往事。因為中醫將牙損的原因歸結為陰虧,所以他的牙痛直到前往日本才得到解決,而中醫的錯誤認識或許是受到了力比多障礙。巴什拉認為因為人們向孩子隱瞞生殖的秘密,因此出現了互逆的命題:既然里比多是神秘的,那么一切神秘的東西就都是里比多。于是人們立刻愛上了神秘,人們需要神秘。很多文化因此變得幼稚,喪失了對理解的需求。……神秘還必須與人類有關。最后,整個文化變得“小說化”。前科學的精神自身也受到了影響[16]192。
牙齒虧損的原因與性結合在一起,而在中國,性更是道德之大忌。因此,關于牙齒的認識便被封閉在神秘之中,上千年都沒有得到解決。
生病與請神算命結合在一起,也可以嘗試用巴什拉的方法來解釋。巴什拉通過考察煉金術得出了一個結論,那就是實驗者會將實驗的失敗歸結于自己的道德不夠純潔等主觀原因,而不是考慮材料的問題,客觀認識和道德結合在一起,看來并不稀奇。這就為醫學和玄學結合提供了可能,病人的病治不好不是藥物的無效,而是自身道德的原因。
事實上,關于此類的材料可以反復羅列,畢竟魯迅那個時代所處的中國正處于轉型突變期,科學、迷信和玄學的糅合混雜比比皆是,與巴什拉所考察的歐洲前科學時代具有相似性。當然,中西方的文化和社會等諸多方面的差異導致巴什拉的分析和結論并不一定完全適用中國的情況。論述上述材料是為了證明,魯迅所批判的迷信實際上產生的原因與想象力對認識領域的過度滲入有關。這種唯心主義的干擾無論東西方都客觀存在。巴什拉在《科學精神的形成》中力圖說明,當人們不對想象力進行心理分析的時候,這種形象的交叉很頻繁。一種釆納形象的科學比任何東西都更容易成為隱喻的犧牲品,因此,科學精神必須不斷地與形象、類比、隱喻作斗爭[16]37。他考察的認識論障礙實際上正是產生神話、詩歌的思維。事實上,梧桐葉和破鼓虎丸的中醫原理便體現了聯想和想象的思維。
而這種看法與魯迅的思想并不沖突,他在前期所提出的分科思維,雖然側重于為迷信、宗教和文學劃分出一塊不受理科統轄的領域,但也批判了迷信和妄信對科學的干擾。如果說巴什拉是通過考察發現,那些在知識領域里有害的、否定的東西,一旦進入了夢幻那非真實的世界中,立刻變成了有益的和肯定的東西[18]。那么魯迅則是發現,太過脫離現實的神思一旦離開文學、神話等虛擬的領域,就可能會對科學領域和現實世界產生不良的危害。
三、神思、迷信與科學認識之分野
和前期的思想一脈相承的地方還在于魯迅仍然強調了科學的極限,并提出了調和科學和文學的方法。1925年,魯迅發表了一篇名為《詩歌之敵》的雜感,這個題目是直抄春木一郎的文章。魯迅還援引了他對于“反詩歌黨”的分類,其中第一種是固執的智力主義者,他們因為無法擴大自己的精神,所以無法感知到專訴于想像力的或藝術的魅力。
針對他們,魯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詩歌不能憑仗了哲學和智力來認識,”[19]246那些蔑視詩歌的科學家“精細地研鉆著一點有限的視野,便決不能和博大的詩人的感得全人間世,而同時又領會天國之極樂和地獄之大苦惱的精神相通”[19]246。可以看到這里的看法與他前期的思想一致,即認為科學的視野是有限的,關于想象力和情感的詩歌不能靠理性和邏輯思維來認識。
在這篇文章中,魯迅還提出欣賞美的事物,不應當用科學的目光來進行判斷,否則黃鸝鳴叫、流螢明滅的背后是它們在尋找配偶,花則只是植物的生殖器官,美麗的外表是為了受精。也就是說,當審美的客體淪為知識的客體,就喪失了美的感覺和想象的延伸力量。
那么,在魯迅看來,是不是說文學家和詩人就應該沉浸在自己的領域,而科學家也可以對自己研究以外的東西置若罔聞呢?
事實上魯迅曾多次談到神思、迷信和科學應該如何保持一個平衡的問題。
1924年魯迅在講學時,針對當時把中國古典神話當作兒童讀物材料的情況發表了看法。魯迅認為,神話符合兒童的天性,可以給其帶來審美愉悅,但兒童如果不接受科學教育,將聽到的神話信以為真,這種做法就是有害的。正如魯迅對迷信批判的原因一樣,神話、鬼神等神思造物不應該脫離它們的虛擬領域,一旦脫離就有可能造成危害。而調和的方法便是引入科學知識,讓人們能夠分清彼此不同的領域。
因此,魯迅多次提出理科生要看一下文學書,文學生也要看一下科學書,這樣可以對人和事有更深的了解。他認為:“現在中國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人們大概以為自己所學的一門是最好,最妙,最要緊的學問,而別的都無用,都不足道的”[20],針對如此偏激的看法,魯迅認為每門學問都各有用處,難分高下,世界上倘若只有文學,反而無聊。這種看法在前期的《科學史教篇》中便已出現。
不僅如此,魯迅還對科學知識的時代性提出了要求。在1933年的《談蝙蝠》中,魯迅談到中國近來對蝙蝠的奚落,有些人認為蝙蝠不屬于鳥類和獸類,所以毫無立場。魯迅指出這是受到了伊索看法的影響,但他緊接著說,這種看法是可笑的,伊索所處的年代,動物學還很幼稚,但現在動物的分類就連小學生都很清楚。他認為那些將古典童話當作正經話來講的人“只足表示他的知識,還和伊索時候,各開大會的兩類紳士淑女們相同”[21]213。事實上,這段話是魯迅針對梁秋實對他指責的反駁:大學教授梁實秋先生以為橡皮鞋是草鞋和皮鞋之間的東西,那知識也相仿,假使他生在希臘,位置是說不定會在伊索之下的,現在真可惜得很,生得太晚一點了[21]213。梁秋實因為魯迅對第三種人的批評,發表議論,認為那天魯迅既未赤腳,也未穿皮鞋,正是“第三種人”。因此,魯迅寫了這篇文章作為回應。具體的史實不再討論,這段話從中反映出魯迅的一個思想,那就是每個人都應當掌握與其時代相符的知識。伊索的時代,動物學的知識還很淺薄,但到了今天,時人的學識卻并不能停留在彼時他的水平。
這個思想更加明顯地體現在1936年魯迅的一封書信中。在信中,他針對厭惡理科的文學青年,希望他們“不要放開科學,一味鉆在文學里。譬如說罷,古人看見月缺花殘,黯然淚下,是可恕的,他那時自然科學還不發達,當然不明白這是自然現象。但如果現在的人還要下淚,那他就是胡涂蟲”[22]。在這里,魯迅對月殘花缺的批判似乎與前面存在矛盾,但其實并不是這樣。看見月缺花殘而留下眼淚,一種可能是看到殘缺的景物想到自身而觸景傷情;還有一種可能就是真的認為月亮的殘缺和花朵的凋謝是它們生命的丟失,也就是將想象的事物當成了真實,將神思轉化為了迷信。我們可以說,魯迅神思和迷信的界限,在于科學這一代表“真”的知識維度是否引入主體的精神世界中,在于主體是否認識到神思造物是虛擬的。
四、結語
科學、文學和宗教在魯迅思想中相互交疊,但又各有自己的領域,缺一不可,不分高下。科學作為客觀世界的知識,必須得到經驗和觀察的檢驗,且以真理為最高旨歸。但科學卻不能超出自己的范圍,不能被拿來批評文學和詩,不能使人體悟人生。文學、詩歌和宗教作為神思的產物,可以讓人欣賞到美,領悟人生的真理。然而,倘若缺乏對事物的正確認識,分不清現實和虛構,將神思蔓延到學之思的領域,那么神思就會變成迷信,阻礙科學的發展,其錯誤的認識也會對現實世界產生危害。魯迅敏銳地察覺到這一點,始終堅持培育無偏頗的個人,希望中國青年既有符合時代的科學常識,同時又不失去想象力和對美的感知。他一方面反對有人將科學獨尊,另一方面又不遺余力地批判迷信和偽科學知識,相信科學啟蒙的力量,其思想產生于時代,又超越時代。
參考文獻:
[1]伊藤虎丸,孫猛.早期魯迅的宗教觀——“迷信”與“科學”之關系[J].魯迅研究動態,1989(11):14-25.
[2]汪衛東.“科學”與“精神”、“神思”、“道德”、“理想”和“圣覺”:《科學史教篇》中“個人”觀念的梳理[J].魯迅研究月刊,2007(4):40-43.
[3]魯迅.人之歷史[M]//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4]王德威.魯迅、韓松與未完的文學革命——“懸想”與“神思”[J].探索與爭鳴,2019(5):48-51.
[5]魯迅.破惡聲論[M]//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6]魯迅.葉紫作《豐收》序[M]//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227.
[7]魯迅.科學史教篇[M]//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8]魯迅.摩羅詩力說[M]//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9]魯迅.我之節烈觀[M]//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10]魯迅.隨感錄三十三[M]//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11]魯迅.祝福[M]//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12]魯迅.長明燈[M]//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13]金修森.巴什拉:科學與詩[M].武青艷,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79.
[14]魯迅.父親的病[M]//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15]魯迅.弟兄[M]//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38.
[16]巴什拉.科學精神的形成[M].錢培鑫,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17]魯迅.論照相之類[M]//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91.
[18]達高涅.理性與激情—加斯東·巴什拉傳[M].高衡,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22.
[19]魯迅.詩歌之敵[M]//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 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20]魯迅.讀書雜談[M]//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458.
[21]魯迅.談蝙蝠[M]//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 第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22]魯迅.致顏黎民[M]//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 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77.
作者簡介:張佳銘,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