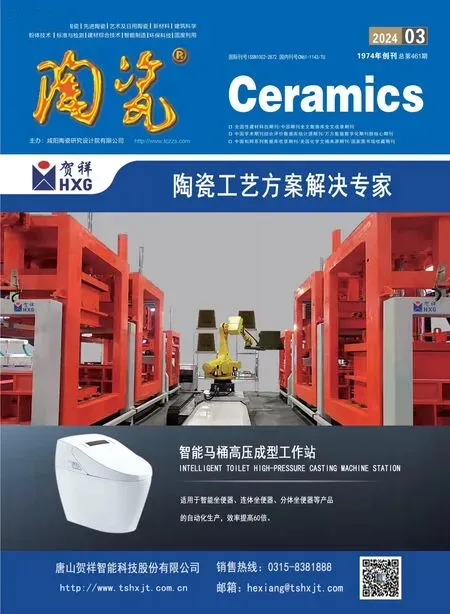論怪誕風格在陶瓷藝術中的應用*
劉思維
(景德鎮陶瓷大學 江西 景德鎮 333000)
“怪誕”一詞本是西方文藝理論中的學術術語,其字面詞義為怪異荒誕、離奇不羈。怪誕作為一種藝術手法或藝術特征在原始時期就已初露端倪,然而其作為一種美學范疇內的審美形式卻很晚形成,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才有人對其進行正式而嚴肅的探索。19~20世紀以來,隨著人類認知和審美的發展,怪誕風格的表達也由最初的“單純想象”轉變為“對現實的異化”,這種與現實相連的藝術手法也逐漸使得怪誕被認為是一種人類對自身情感的表達、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思。在陶瓷藝術領域,怪誕風格也以其獨特的形式為人類審美提供新的視角。
1 怪誕風格的概述——從被否定到被肯定
怪誕作為一種藝術現象由來已久。在怪誕正式成為風格流派之前,羅馬時期的建筑家維特魯威就曾對這種藝術現象做出過評價:“細小的花莖支撐著人頭或獸頭,花頂上畫著莫名其妙的不和諧的小雕像。這些東西過去從未存在過,現在也沒有,將來也不會有。”他認為這些不合理的組合完全背離了世界的秩序,是一種混亂的想象。這種“混亂的想象”在15世紀以意大利語詞匯洞窟(La grottesca 和Grottesco 與洞窟(Grotta))為基礎,演變為“怪誕”一詞,成為了一種風格流派。
隨著當時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推崇理性、秩序的藝術家和思想家數量日趨龐大,直到18世紀,怪誕的“非理性化”性質致使其仍然只能作為普遍意義上的貶義詞存在,它是“可笑的”“歪曲的”“反常的”以及“荒謬物、對自然的歪曲”的代名詞。至19世紀,怪但仍被看作是離經叛道的表現形式,即便是黑格爾也對其感到厭煩:“我們不能在這種騷動混亂中找到真正的美”[1]。
人們對怪誕的認知,在社會階級矛盾激化、戰爭頻發的19~20世紀發生了極大轉變。在文學、藝術領域,怪誕的“扭曲”“異化”“不合理的拼接與組合”逐漸成為一種人文主義情感的發泄與表達方式而不再遭到貶低和排斥。
作家維克多·雨果曾在其劇作《克倫威爾》的序言中,把怪誕從虛妄的幻想中拉回到現實世界,使其與現實關聯而非單一的想象。沃爾夫岡·凱澤爾發揚了雨果的論斷,在其著作《美人和野獸:文學藝術中的怪誕》中,他稱其論述的怪誕是一種極具現代性且精辟的經典批評,他突出強調了其中陰森、恐懼的指向,是“疏遠或異化世界的表達”[3]。此外,還有菲利普·湯姆森在《論怪誕》中就怪誕與現實的關系進行了進一步的深化與闡釋,“怪誕乃是意圖祛除世界上一切邪惡勢力的一種嘗試”。他指出:“怪誕乃是作品和效應中的對立因素之間不可調節的沖突。”[2]所以可以認為,怪誕的一系列定義是“有著矛盾內涵的反常性”。怪誕是以矛盾的方式呈現的,是由滑稽與恐怖、過分與夸張構成的不可調和之存在。
2 怪誕風格在陶瓷藝術中的表達形式——對現實世界的異化
怪誕藝術的怪誕性往往和真實性對立統一,完全憑借想象所產出的作品不能被視作怪誕,因為它并未與現實產生聯結,只作為一個孤立的精神產物而存在。只有將作品與現實有意識地結合,才能產生怪誕。因此,在陶瓷的藝術創作中,適當對真實事物采取夸張和變形等藝術手法以達到“怪誕意趣”的目的更能體現出一種藝術的自由張力。
2.1 異化的人
從人類世界的第一尊造像出現以來,人物一直是藝術創作中最重要題材之一。從史前世界到現今,人類對自我的塑造也經歷了一系列的發展。不過我們依然能從這些遺留下來的塑像中看到怪誕形式的影子:公元兩萬多年前的《維倫多夫的維納斯》,采用夸張的手法表現女性的身體部位,如豐臀寬胯,碩大的胸部造型,以表達原始人類的母神崇拜與生殖崇拜(見圖1)。然而,這些造型并非現實的真相,而是通過夸張的手法表達遠古人類的生存希冀。

圖1 多地區均有女神像出土

圖2 《Two Views One Window》
當代藝術家也依然會采用這種類似方式去表達帶有“怪誕”風格的人物,如Patricia Rieger的陶瓷藝術作品《Two Views One Window》中長著四只胳膊的雙面人像,他的胳膊伸向不同的方向,仿佛在實現某種摸索與探尋。這樣的人體全然不屬于真實的人類形態,難免讓人產生怪異的感受,不同的觀者自會由作品引發聯想,從而對其產生不同的理解。這也是怪誕藝術作品想要呈現給人們的結果,即并非單純的以“讓人產生怪誕之感”為目的,重點在于“產生怪誕之感”之后的,人們的自我深省以及外化的行動。
2.2 異化的物
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曾提出了關于原始人的哲學基礎理論“萬物有靈觀”。如緬甸的克倫人相信植物也像人和動物一樣有自己的靈魂。遠古先民也會賦予動植物崇高的意義,通過對其本來面目的改造和再創作,最終使其偶像化,或成為人們拜謁的對象,或成為統治者以統治、震懾為目的,用以加強“君權神授”這一觀念的手段。
若從這個角度來分析,當一件藝術作品將物的形象通過某種程度的拼接改造,使之成為一種人類前所未見之物,或者為其賦予人性、神性或怪奇性,使之與“人”產生瓜葛,成為了一種似是而非的“人”,無疑會引發人們的驚詫、恐懼,甚至是崇敬之感。一些考古發現也佐證了這樣的畸變形式:在古埃及《亡靈書》中就畫著長有豺頭的死神阿努比斯的圖像,這些怪異的結合無疑對當時的人民產生了一系列的精神操控作用。而在當今陶瓷藝術領域中,將物進行畸變改造的創作也是十分常見的,但這樣的組合早已與政治和神性脫離,藝術創作更多的關注當下社會問題:人類對世界的觀點以及對自我的反思。
以色列陶藝家Ronit Baranga以其設計的“Body of Work”系列作品(見圖3)而被廣大中國藝術愛好者所熟知。在她的作品中,手、口等器官被編排安置在精致的餐具上,這似乎很難用常規的美學來定義。但是當這些餐具匯聚到一起時,手指唇舌相互交錯,給人一種莫名的緊迫感,而這種緊迫感并非來自外界,而是源于觀者內心的某種渴求。

圖3 Ronit Baranga作品
另一位陶瓷雕塑藝術家Jessica Sallay-Carrington也擅長將不同形象進行重組和再創(見圖4)。或將動物的頭部與女性人體相結合,或將不同動物的特征組合到一起,從而形成一個新的形象,陶瓷的易碎性與脆弱性恰好也符合作者對集體中的個體,自然中的生物以及男權社會下的女性問題的關注。

圖4 Jessica Sallay-Carrington作品
3 怪誕風格的藝術價值
從傳統美學的角度來說,美是指一種使人感到舒適的,一種理想化的形象。而怪誕風格中的扭曲畸變形象往往與傳統意義上的美相去甚遠。隨著人類對自我和世界的思考,人們對美的認知逐漸多元化,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終其一生去追求“惡之花”,并將這種與傳統的美背道而馳的意象表述為一種“英雄氣概”。在傳統的秩序世界里,人們需要遵循準則:怪奇故事的出現,是為了使群眾從中得到教化。強調善惡有報,以達到某種理性的統一;幻想中的巨獸被賦予特定的靈性,使人感到恐懼,其目的與前者別無二致。而當怪誕成為一種審美形式而被人們接納之時,時空以及固有的秩序被打破,從而為人類看待世界增加了新的可能:怪誕風格的藝術作品取材自現實,卻突破了素材原本的樣式,為觀眾提供了比現實更自由的想象空間。劉法民曾對怪誕藝術形象進行概括,即用最熟悉的構成最陌生的,用最美善的構成最丑惡的,用最現實的構成最超現實的,用最非人的構成最人體的[4]。總之,怪誕脫離了正常邏輯和思路,是帶有解放和顛覆意味的。
4 結語
怪誕風格的藝術價值通過對現實的異化表現出來,可將其總結為對自由愿望的滿足,對陌生驚奇的創造、至情至理的表現,對自我的深層關注以及對哲理或觀念的表達。其語義已由藝術審美轉變為對人的精神的關注。在陶瓷藝術中,怪誕風格還處在相對冷僻的的境地,依然缺乏相對完整的研究體系。但怪誕作為一種藝術風格顛覆了傳統的秩序與美學,在其與陶瓷藝術融合時,能夠充分利用陶瓷泥土的可塑性,燒成后的易碎性、脆弱性等特質去表達自然與社會中種種關系的“不適感”,這種“不適”往往隱藏著人類最本質的理想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