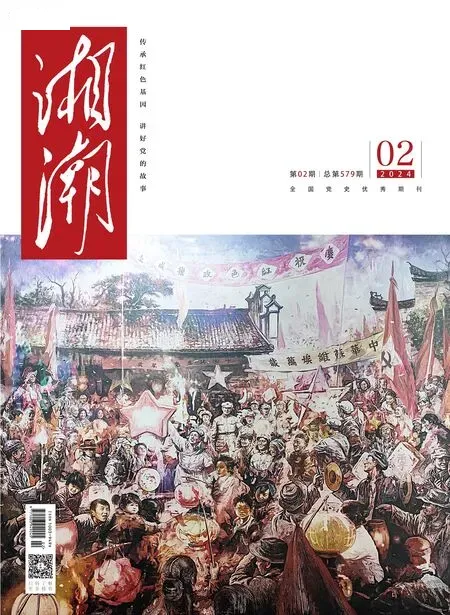任弼時調查研究的幾個特色
作者|周 春
任弼時十分注重調查研究,始終強調“我們在訂計劃、寫決議的時候,必須經過仔細的調查研究,按照實際可能的條件,按照群眾的覺悟程度和經驗去決定我們的政策和辦法”。他認為“事前加以深入的調查研究,事后詳盡地總結經驗教訓”,就能“使我們少犯錯誤,不重犯錯誤,而能較快地走上正確的軌道”。他在處理每件事情時,總要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后才發表意見。調查研究成為任弼時一生的一個重要習慣,在他30年的革命實踐中形成了獨具一格的特色。
堅持問題導向,明確調研方向
任弼時堅持以問題為導向開展調查研究,跟著問題走,奔著問題去,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認為“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目的,就是為了從這些學習中能夠得到方法,得到經驗,去幫助我們解決實際問題”。
1925年,全國已經建立了幾十個地方團組織,任弼時清醒地認識到這些團組織都存在一些問題,如組織渙散、紀律松弛、團干部缺乏、各階級成分比例不均、不能正確認識自己的職責、向外活動少、上下級關系不密切、團員數量少等,嚴重阻礙了團組織的發展。任弼時十分重視這些問題,用了九個月的時間開展調查研究,發放青工調查表等各類調查提綱、表格近10種。除了了解到各地團組織的基本情況外,還掌握了地方團員發展、團組織建設情況。依據這些資料,任弼時有針對性地健全與調整了青年團的組織和機構,進一步規范了青年團的建設工作,加強了團的領導機關的工作效能。
1931年,任弼時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黨校校長。在檢查各級組織工作開展情況時,他發現一些地區的黨組織存在問題,如缺乏集體領導,書記說了算,不能認真地實行黨內民主,群眾的積極性沒有充分發揮,等等。對于這些問題,有些同志不以為然。任弼時經過調查研究之后,嚴肅地提出,這是關系到黨的組織和領導是否健全的問題,必須解決。為此,他提出了四條措施加強地方黨委的領導。
1940年,任弼時從莫斯科回到延安。他發現中央直屬機關、軍事機關、邊區的黨政機關三大系統各行其是,存在人員復雜、機構重疊、辦事交錯、責任不清、制度缺失、沒有統一的行政管理機關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任弼時進行調查研究并拿出解決方案,在充分考慮各種因素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央一級的行政管理機關,即中共中央辦公廳,他兼任辦公廳主任,并建立了行政、干部供給、財務會計、文件管理和檔案保管等制度。在改善生活方面,他一視同仁,提出不僅中央領導的生活要改善,廣大干部群眾的生活也要改善,后建立小灶、中灶、大灶制度。為了保證供應,他還對物資來源作了反復研究。為了加強調查研究,他還在中央辦公廳成立了政策研究室。通過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各部門之間明確了行政關系,工作開始條理化、正規化。
傾聽群眾意見,形成解決辦法
任弼時指出,向群眾學習的重要途徑就是深入群眾進行調查研究。1943年,他撰寫了《共產黨員應當善于向群眾學習》一文,深刻闡述了為什么要向群眾學習以及如何向群眾學習。在文中,針對“有些同志所擬的計劃或決定,不是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不是從總結群眾實踐斗爭的經驗產生”的“空論”,他強調要“善于去傾聽群眾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善于去總結群眾斗爭的經驗并找出其教訓與規律,再去指導群眾行動”。對于有些同志“沒有從調查研究群眾的實踐中去想辦法,而是從感想從書本上去想辦法”的情況,他強調要“從照顧群眾的利益出發,從照顧群眾的經驗出發,從依靠群眾的力量出發”。
任弼時每到一地,哪怕是在緊張的戰斗和行軍中,只要有幾分鐘時間,他都要找當地群眾拉家常,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在會議上,他常常要求談工作問題的同志說得具體些。在陜北,他利用打獵的機會,跑到農民的山莊里,問農民收的糧食夠吃不夠吃,幫助他們研究如何提高生產、增加收入。在北京,他利用警衛人員到街上買東西的機會,調查商人的生意好不好,研究如何才能把市面繁榮起來。
1934年10月,任弼時率部在貴州石阡與白崇禧部隊激戰,被包圍在山谷中,身處絕境,極其兇險。如何突圍?指揮部找來了一個向導,調查研究突圍路線。向導是個樂觀爽朗的農民,熱情地介紹了這一帶的情況,臨末,向導將袖子一卷道:“你們急什么?不要急。山山有路,路路通南京嘛!”任弼時立即要一個政工人員把農民說的這句民諺記了下來并要求向全軍傳達。“山山有路!”部隊被這句話極大地鼓舞了,好像注入了新鮮血液一樣,他們發出震撼山岳的呼號:“紅軍不可阻擋!”“我們一定勝利!”在強大精神力量的帶動下,戰士們發起了勇猛的沖鋒,最終突出重圍。
全面抗戰勝利后,對于要不要進行土地改革,黨內產生了分歧。任弼時參加會議,聽山西、河北、山東、華中各解放區的負責同志談各自的情況,大家普遍反映土地改革掀起了一場極大的群眾運動,群眾直接從地主手中取得土地,熱情極高。在群眾運動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決了和正在解決著土地問題,因此,土地改革不是要不要搞的問題,而是如何深入引導的問題。任弼時在認真聽取群眾意見的基礎上總結了各地區斗爭的經驗,提出了解決土地問題的具體方針、政策和辦法。
精析調研數據,把握發展規律
任弼時十分注意理論聯系實際,總結符合實際情況的工作規律。他指出要遵循毛澤東提出的“必須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體情況,從不同地區、不同歷史條件的具體情況出發,決定當地當時的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毛澤東起草的《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8月27日,中央調查研究局正式成立,毛澤東兼任局長,任弼時任副局長。已經掌握豐富調查研究經驗的任弼時再次領命開展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工作。在經濟建設工作上,任弼時分析了大量調查數據,指導中共陜甘寧邊區中央局做出了《關于開展邊區經濟建設的決定》。這個決定全面系統地提出了邊區經濟建設的方針和政策,為廣大軍民戰勝困難、渡過難關指出了明確的方向和具體的目標。
1943年下半年,陜甘寧邊區出現了物價波動、通貨膨脹、財政金融紊亂的現象。為了弄清楚原因,任弼時用了近三個月的時間開展調查研究,在研究分析的基礎上找出了癥結所在。他在筆記本上詳細地記錄了邊區政府有關負責人的發言和大量的經濟數據。1944年,在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任弼時作了長篇報告《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工作的基本方針》,成為指導邊區經濟建設的重要文件。在報告中,任弼時展示了“延安念莊變工隊的統計”“關中新正三區二鄉別嶺村的統計”“安塞高川村1940—1943年經濟發展情況”“藍鳳城1941—1943年收支對照表”“藍鳳城各項開支表”“藍鳳城支出中購買邊區內外物品的費用對照”“三五九旅戰士開支比較”七張圖表。這些調查資料數據翔實,在比較中將邊區的情況和問題分析得十分透徹。毛澤東批示,將這篇報告作為“黨內高級干部讀物”印發5000份。
任弼時從調查研究入手,一步一步推進各項經濟舉措,扭轉了邊區的經濟困境,使邊區經濟面貌為之一新,并探索了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規律。
注重調研成果,敢于堅持真理
堅持真理是任弼時偉大的精神品質,他堅持原則,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善于在復雜的斗爭中把握正確方向。任弼時曾說過:“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誰有真理誰就有資格發言。”王震評價任弼時“注重調查研究,深入實際,善于正確解決復雜的、重大的問題”。對于通過調查取得的寶貴成果,任弼時敢于堅持自己的正確意見。
八七會議后,在反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時,黨內“左”傾錯誤思想抬頭。1929年,任弼時任中共江蘇省委代理書記。當時上海的白色恐怖非常嚴重。有一次,浦東農民武裝斗爭失敗以后,準備再進行一次武裝斗爭。任弼時知道后,立即找到在浦東一帶做農村工作的劉曉,咨詢他當地農民群眾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情緒高低程度及具體斗爭情況。任弼時要求劉曉以一個地區的具體情況來作典型說明,反復提出了許多需要研究的問題,還要求劉曉請一名當地農民來談話。劉曉找來參與斗爭的一名農民同志,任弼時先給這位同志端茶遞煙,拉家常,消除他的緊張情緒,之后才有針對性地了解當地的具體實際,包括當地、當時的事物、人情,敵我力量對比,農運干部與組織等情況,甚至對下一季收成的預期,等等。談完之后,任弼時沒有立即下結論。后來,他告訴劉曉,再來一次武裝斗爭的條件是不夠成熟的,必須立即取消武裝斗爭的計劃,接著非常具體地向他闡明為什么要這樣決定的理由。事實證明,正是因為任弼時的慎重決策,才避免了又一次的“左”傾錯誤。
1933年11月,任弼時任中共湘贛省委書記。當時湘贛地區肅反擴大化嚴重,出現了許多“左”傾錯誤。負責青年工作的張愛萍被一名“AB”團分子供認為青年總團部負責人之一,遭到逮捕,相關口供材料已送到了任弼時手中。任弼時看了后提出質疑,認為“不應只憑口供,應該從他此一時期工作的檢查中來找根據”。隨后,任弼時委派顧作霖去調查。顧作霖進行調查后,發現張愛萍一事純屬誣陷,張愛萍因此得救。后來張愛萍成長為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為了防止肅反擴大化,任弼時在組織部門的會議上明確提出:“以后肅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調查,重證據!”“要建立嚴格的審批制度。”
1947年,中共中央頒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把土改運動推向了高潮。此時,有些地區也發生了“左”傾錯誤,毛澤東委托任弼時進行調查,研究土地改革的方針政策。彼時,任弼時高血壓復發,中央決定讓他去楊家溝附近的錢家河休養一段時間。但任弼時并沒有休息,而是每天都在駐地周圍的村子做調查,一共調查了30多個村子。他訪問農民群眾,調查生產、生活情況及他們對土地改革工作的意見,感受土改運動在基層一線的脈搏。他還安排身邊工作人員利用幫助群眾干活的機會,按村、按戶調查人口、土地以及評定成分的情況。在此期間,他還查閱了大量的黨內文件。通過調查研究,他發現“左”傾錯誤十分嚴重。有一個名叫蔡家崖的村子,共552戶,地主富農本來只有40多戶,結果劃了120多戶,嚴重擴大了打擊面。任弼時堅決反對這種“左”傾錯誤,明確提出“錯誤地擴大打擊面,打亂革命陣線”,稱這是“幫助敵人,孤立自己”,并要求“哪怕只是劃錯了一個人,也必須改正”。1948年1月,任弼時在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作《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并以蔡家崖村為例“解剖麻雀”,具體分析發生錯誤的原因。這篇報告成為糾正“左”傾錯誤的力作,后經毛澤東修改補充定稿,被確定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

△ 1947年,任弼時在轉戰陜北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