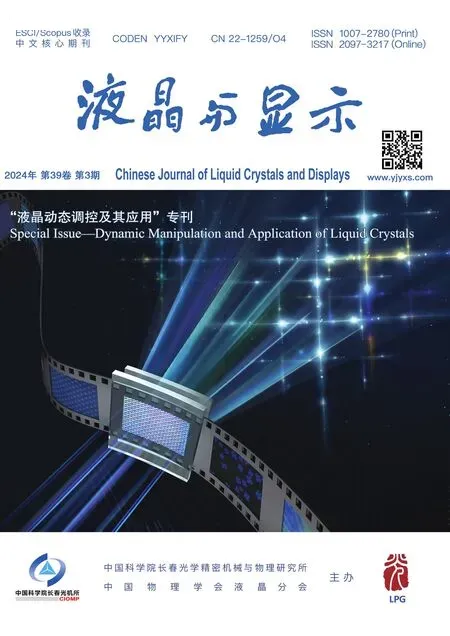近晶相液晶超結構的多元外場調控
張涵, 王龍洋, 朱柏翰, 王澤宇, 魏陽, 馬玲玲, 陸延青
(南京大學 現代工程與應用科學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93)
1 引言
微納尺度的多層級嵌套有序超結構在高性能新材料的開發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自然界的許多現象,如荷葉“出淤泥而不染”的自凈能力[1]、蝴蝶絢麗多彩的翅膀[2]、水黽的“輕功水上漂”[3]等,都源于生物體內存在的特殊的多層級超結構。人們從大自然中汲取靈感,研制出無數接近甚至超越生物材料的結構和功能材料,為新材料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因此,開展多層級超結構操控與性能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液晶是介于液體和晶體之間的第四種狀態,既有液體的流動性,又有晶體的有序性[4-7]。液晶通過自組裝可以形成豐富的多層級超結構,如膽甾相液晶指紋織構[8]、藍相液晶雙螺旋超結構[9-11]和近晶相液晶焦錐疇超結構[12-13]等,這些超結構在基礎科學和應用研究中均發揮著重要作用[14-20]。同時,液晶還能對光、電、磁、聲、熱、力等各種外界刺激做出反應,這使其成為智能軟物質領域的佼佼者[21-23]。
近晶相液晶相比于其他液晶相態有序度更高[24],液晶分子分層排列。當近晶相液晶分子層與硬質表面相互作用時,受到表面錨定作用導致分子排列發生跨尺度形變,極易在微觀尺度上誘導焦錐疇陣列等復雜拓撲缺陷結構的形成。盡管這些拓撲缺陷被證明在光電、傳感器、微操縱等諸多領域具有重要應用潛力,但要實現可預測和可重構的缺陷結構調控仍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為此,在國際方面,韓國科學技術院H.T.Jung等人先后提出了多向摩擦和多重壓印法來控制環面焦錐疇陣列,獲得了具有不同對稱性的環面焦錐疇陣列[25-26]。韓國科學技術院 D.K.Yoon等人利用面內電場使環面焦錐疇結構在相轉變過程中轉變為鋸齒形結構和各向異性的焦錐疇結構[27-28]。法國索邦大學E.Lacaze等人進一步發現,材料在近晶A相向近晶C相轉變過程中會產生一種與油紋垂直的周期性皂色條紋結構[29]。
在國內,北京大學楊槐教授與中科院理化研究所熊桂蓉研究員等人通過制備周期性三噻吩類近晶相液晶微米線材料,在低溫下獲得了具有高載流子遷移率的大面積有序微條結構[30]。香港科技大學郭海成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郭琦教授和西北工業大學馬營教授等人基于近晶C*相(鐵電)液晶材料的快速響應性開發了一系列電驅動光開關、偏振光柵、叉形光柵、Pancharatnam-Berry透鏡等光學元器件[31-33]。還有研究學者提出利用自組裝單層膜、氫鍵自組裝等方法取向鐵電液晶,從而使器件具備良好的抗振動能力和百微秒量級的響應時間等。
上述研究多集中在近晶相液晶缺陷結構的制備和利用近晶相液晶材料構建快速響應器件方面,很少關注近晶相液晶材料的自組裝多層級超結構轉變及其動態調控與機制研究。近年來,本研究團隊在近晶相液晶焦錐疇超結構和膽甾相液晶指紋超結構的光控取向操控方面取得了系列進展[34-37],并基于受控超結構報道了仿生自驅動可編程執行器和四維可視化成像技術[38-39]。可以想象,如果能夠引入多元化外場,利用液晶的刺激響應特性,實現近晶相液晶多層級超結構的高效動態調控,將有望激發更多基于液晶超結構的前沿創新性功能化器件。
本文聚焦近晶相液晶超結構的自組裝過程、多元外場相互作用、外界刺激對焦錐疇缺陷超結構的動態調控規律等方面進行了研究。首先,本文研究了光取向和液晶膜厚對近晶相液晶正方焦錐疇陣列的形態和大小的操控。然后,通過材料復合引入聚合物穩定策略,研究了特定溫度下正方焦錐疇微透鏡陣列的電刺激動態調控性能。最后,研究了近晶相液晶拓撲超結構在引入手性后帶來的多維度調控,通過溫控切換膽甾相液晶指紋超結構和近晶相液晶焦錐疇超結構,實現了同一材料體系雙相態多層級超結構的功能集成。
2 近晶相液晶超結構在不同膜厚和取向條件下的受控調制
近晶相液晶相比于向列相和膽甾相液晶,其有序度更高,呈層狀結構。當近晶相液晶薄膜上下表面處于對抗性的表面錨定條件下,即上下表面液晶分子受到不同方向的錨定,致使液晶分子層無法保持原本的平行層結構時,為保持液晶分子層間距恒定,分子層會發生一定程度的展曲形變以適應錨定條件。在液晶彈性能和各向異性表面錨定能的共同作用下,最終形成體系能量最低的缺陷態超結構陣列,如焦錐疇(Focal Conic Domain, FCD)、油紋等。
在FCD缺陷態結構中,存在兩條共軛的缺陷線于兩個正交的平面內。根據取向情況的不同,缺陷線具有不同的形態(如一組共焦的橢圓和雙曲線的一支,或一組共焦的拋物線等)。發生形變的液晶分子層圍繞上述特征缺陷線緊密包裹,最終形成一系列類似于杜賓環面的周期性層狀結構。當近晶相液晶薄膜厚度小于一定程度時,液晶分子將自組裝形成垂直于取向的周期性油紋超結構,周期為百納米至微米級。油紋內部存在一系列半圓柱狀液晶分子層、旋轉晶界和相互平行的位錯線。
2.1 均勻取向下膜厚對超結構的作用規律
當均勻平面取向時,近晶相液晶分子8CB將組裝形成正方焦錐疇(Square Focal Conic Domain,SFCD),偏心率為e=,雙曲線的兩條漸近線恰好垂直,故而得名。由于取向誘導,此時SFCD大小均勻,排列有序,并且SFCD的朝向(缺陷結構的偏心方向)平行于取向方向,如圖1所示。

圖1 SFCD的層級結構及其內部缺陷線示意圖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tructure and line defects of SFCD
實驗中,我們在25 ℃室溫環境下,將取向后的玻璃基板放置在熱臺上加熱至55 ℃。用毛細玻璃管蘸取少量8CB均勻涂覆玻璃基板,迅速將其轉移到旋涂儀吸頭處,設置不同轉速旋涂30 s,從而獲得不同厚度的液晶薄膜。圖2展示了在偏光顯微鏡下觀察到的不同轉速下的液晶織構圖。當轉速小于5 500 r/min時,膜厚較厚,呈SFCD結構。SFCD尺寸隨膜厚減少而單調減少,隨著取向錨定作用逐漸增強,結構排列逐漸整齊。而當轉速超過6 000 r/min時,FCD結構轉變為周期性Zigzag結構。這是由于當液晶膜厚小于某一程度后,液晶分子層受取向層作用更明顯,分子層展曲方式發生改變,最終形成Zigzag結構。圖2(e)中白色框中展示了典型的疇結構單元,正是這樣的疇結構單元交替排列形成了Zigzag陣列。Zigzag結構的平均寬度隨液晶膜厚減小而變小。

圖2 均勻取向下不同旋涂轉速對超結構的作用規律。(a)2 000 r/min;(b)4 000 r/min;(c)5 000 r/min;(d)5 500 r/min;(e)6 000 r/min;(f)7 000 r/min;(g)9 000 r/min;(h)11 000 r/min。比例尺為10 μm。Fig.2 Influence of spin-coating speeds on FCD and Zigzag structures under homogeneous alignment. (a)2 000 r/min; (b) 40 00 r/min; (c) 5 000 r/min;(d) 5 500 r/min;( e) 6 000 r/min;( f) 7 000 r/min;(g) 9 000 r/min;( h) 11 000 r/min. The scale bar is 10 μm.
2.2 二值突變取向下膜厚對超結構的作用規律
利用光控取向技術結合自主研發的基于數字微鏡陣列(Digital Micromirror Device, DMD)的微縮投影曝光系統[40],進一步實現了對近晶相液晶的FCD圖案化操控。
首先,本研究利用光控取向技術引入二疇結構,取向方向相對于中心分界線分別為+45°和-45°。在這兩個取向疇內,臨近取向層附近的液晶分子將被誘導相互垂直排列。當轉速較低(3 000 r/min)時,得到的液晶膜較厚,由于層狀液晶體系最小自由能的約束,在同一個取向周期內形成朝向相互垂直的SFCD陣列,在特定的奇(偶)疇邊界處形成系列半環面FCD,如圖3(a)矩形框所示,半徑約為8.3 μm,疇尺寸較大,且FCD周圍還伴隨著其他小SFCD結構,形成主次分明的FCD超結構。這是因為在膜厚較大時,取向對FCD結構的限制變弱,在對抗性錨定條件下,液晶分子層不連續變化引起了大小FCD的伴生。隨著轉速增加,膜厚逐漸減小,這種FCD超結構轉變為多層級的Zigzag超結構,即一個層級為周期性近晶相液晶分子層,另一個層級為取向單元內的周期性Zigzag陣列,又一個層級為由周期性光控取向結構引入的Zigzag超結構陣列,并且膜厚越小,Zigzag結構條紋的平均寬度也隨之變小,數量增多。

圖3 二值突變取向下不同旋涂轉速對超結構的作用規律。(a)3 000 r/min;(b)7 000 r/min;(c)11 000 r/min。比例尺為10 μm。Fig.3 Influence of spin-coating speeds on FCD and Zigzag structures under orthogonal binary photoalignment. (a) 3 000 r/min; (b) 7 000 r/min; (c)11 000 r/min. The scale bar is 10 μm.
2.3 Q-plate連續漸變取向下膜厚對超結構的作用規律
為了進一步探究液晶薄膜厚度和取向結構對超結構的操控,本文在二值突變取向結構的基礎上,設計了一種繞著中心奇點連續漸變的特殊取向結構,即Q-plate,使FCD拓撲缺陷結構的朝向可以隨方位角連續漸變,實現了對朝向的操控。本研究利用微縮投影曝光系統制備Q-plate取向陣列,圓取向結構內的取向方向隨方位角連續漸變。當近晶相液晶在取向基板上涂覆成膜后,通過控制不同轉速,獲得了如圖4所示的FCD超結構。當轉速為3 000 r/min時,由于液晶薄膜厚度較厚,取向結構內形成SFCD,形狀為扇形,朝向中心奇點;而取向結構外所形成的FCD為環面FCD,形狀為圓形,無特定朝向和位置有序性。由于內外均為FCD的填充,整個取向圓結構邊界不清晰。隨著轉速分別增加到7 000 r/min和11 000 r/min,在取向圓結構內部,出現了環繞型Zigzag結構,而它們的方向會隨著取向不斷改變。與此同時,在取向圓結構外部,仍然保持著環面FCD結構,其尺寸會隨著轉速的增加(即膜厚的減小)而逐漸減小,表明膜厚和取向結構共同作用于近晶相液晶超結構的調控。

圖4 Q-plate連續漸變取向下不同旋涂轉速對超結構的作用規律。(a)3 000 r/min;(b)7 000 r/min;(c)11 000 r/min。比例尺為20 μm。Fig.4 Influence of spin-coating speeds on FCD and Zigzag structures under radial continuous gradient photoalignment. (a) 3 000 r/min; (b) 7 000 r/min;(c) 11 000 r/min. The scale bar is 20 μm.
3 近晶相液晶FCD微透鏡陣列的電刺激動態調控
3.1 近晶相液晶FCD超結構的微透鏡成像功能
FCD獨特的指向矢分布使其具有微透鏡成像功能。為了驗證其成像能力,我們基于顯微鏡平臺搭建了如圖5(a)所示的成像光路。劍形掩膜板目標探測物被放置于顯微鏡光源處,并與載物臺上的FCD微透鏡陣列樣品間距11 cm。考慮到微透鏡焦距僅在微米量級,故近似認作為無窮遠處物體以平行光入射成像。經過對焦,可對微透鏡陣列像平面處的成像狀況進行觀測并由CCD拍攝記錄。圖5(b)展示了FCD微透鏡陣列在未加電狀態下的成像情況,在每個微透鏡單元的焦平面上均可觀察到清晰的劍形像。當目標探測物為鏤空的矩形時,成像效果為清晰的矩形點陣。

圖5 聚合物穩定的近晶相液晶FCD超結構的微透鏡成像功能。(a)成像光路;(b)無外電場作用下FCD微透鏡成像示意圖。比例尺為10 μm。Fig.5 Imaging function of the polymer-stabilized smectic liquid crystal FCD microlens array. (a) Setup of the imaging system; (b) Textures of imaging of the FCD microlens array without external electric field. The scale bar is 10 μm.
3.2 復合材料制備和基于聚合物穩定的超結構動態調控
在近晶相液晶研究領域,其分子排列的高度有序使分子間相互作用較強并具有恒定的層間距,限制了液晶超結構陣列在外場下的動態調諧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研究優化了近晶相液晶的組分,引入聚合物穩定的策略,制備了聚合物穩定的近晶相液晶FCD超結構材料體系。即使材料相轉變為向列相后,液晶分子仍會被錨定排列成原本FCD時的結構。由于此時材料體系處于向列相,因此賦予了其可調性。
我們在8CB液晶體系(94.12%,質量分數)中摻雜4.8%(質量分數)的液晶聚合物單體RM257和1.08%(質量分數)的光引發劑819,其中RM257的作用是形成聚合物網絡,用于穩定超結構中液晶分子的排列。通過在上下基板上引入兩個對抗性錨定的取向條件(分別為均勻的平面取向和垂直取向),成功誘導構筑了六方密堆積SFCD陣列,且其大小可以通過改變轉速(膜厚)進行調控。隨后,我們將自組裝形成的SFCD陣列(近晶相態下)暴露在紫外(UV)燈下進行聚合,聚合光功率為2.6 mW/cm2,使之形成聚合物網絡,穩定住SFCD的構型。與未聚合的SFCD陣列不同的是,當此樣品被加熱時,聚合后的SFCD陣列在整個向列相溫寬范圍內均可被觀察到,而未聚合的SFCD陣列在SmA-N相變后消失。
3.3 FCD微透鏡陣列的電刺激動態調控
通過引入上述聚合物穩定策略,我們系統地研究了上述SFCD陣列在35 ℃下的電刺激動態調控性能(圖6)。當一個1 kHz的垂直電場作用于樣品時,電場力使液晶分子指向矢偏轉,趨向于垂直于基板。電相干長度ξ=(K/εΔε0)1/2/E,其中K為液晶彈性常數,ε0為真空介電常數,Δε為介電各向異性,E為電場強度。從圖6可以看出,隨著外加電場的增大(從0 V增加到100.6 V),Δn隨之減小,SFCD的襯度也逐漸減小。當E>100 V·μm-1時,FCD接近消失。隨著外加電場的減小,SFCD重新出現。織構在十幾個電壓周期內保持良好,表明在電場驅動過程中聚合物網絡保持穩定,焦錐疇超結構具有一定的穩定性。

圖6 聚合物穩定近晶相液晶FCD微透鏡陣列的電刺激動態調控。比例尺為5 μm。Fig.6 Dynamic modulation of the polymer-stabilized smectic liquid crystal FCD microlens array under the electric stimulus. The scale bar is 5 μm.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電場驅動的多層級超結構轉化同樣也適用于其他受控自組裝的近晶相超結構,產生形式多樣的受控結構演化,進而引發包括折射率調制在內的光學、形態學以及其他物理屬性的動態調控。
4 手性與溫度對液晶拓撲超結構的動態調控
4.1 手性近晶相-膽甾相雙相態拓撲超結構體系的構筑
手性和多層級結構是材料科學中兩種常見且復雜的結構類型,構筑與操控手性多層級結構已成為材料科學的前沿領域。液晶的自組裝功能與外場響應性為研究手性多層級結構提供了平臺。
我們對近晶A相液晶8CB摻雜光敏手性劑構成的雙相態體系進行了動態調控規律探索。通過摻雜1%(質量分數)的光敏手性劑ChAD-3c-R,在8CB液晶中引入手性和光響應特性。近晶相液晶材料8CB在不同的溫度下,展現出兩種不同的相態:向列相和近晶A相。具體地,當溫度下降低到33.5 ℃時,8CB會從向列相轉變成近晶A相。利用材料的雙相態特性,可以通過溫度調控不同相態下的不同多層級超結構。在受到這種特殊摻雜影響后,8CB復合材料的相變點也略微發生改變,實驗測得新的相變溫度約為31.12 ℃。在相變點以上可自組裝形成膽甾相液晶指紋超結構,而在相變點以下轉變為近晶相液晶FCD超結構。
4.2 均勻取向下手性液晶拓撲超結構的溫控演變
我們在光學顯微鏡下對均勻取向的手性液晶超結構隨溫度的演變過程進行了詳細觀察(取向方向為水平,圖7)。特別地,在溫度降至32.34 ℃(膽甾相)時,可以觀察到局域微區膽甾相液晶指紋超結構呈現有序的周期條紋排列(圖7(ⅰ),黃色圈內)。但由于均勻取向在二維空間的限制作用較弱,條紋整體方向性顯得相對無序,我們把此時的指紋織構稱為條紋0。

圖7 均勻取向下手性液晶拓撲超結構在相變點附近的溫控演變,取向方向為水平方向。比例尺為100 μm。Fig.7 Phase transition process of chiral liquid crystal superstructures near the transformation point under homogeneous alignment versus temperature. The scale bar is 10 μm.
在溫度從32.34 ℃降至32.14 ℃的實驗過程中,在偏光顯微鏡下觀察到一種新的條紋結構的誕生,即條紋1(圖7(ⅱ),綠色圈標出)。這種新的條紋相比原有指紋結構更粗,并伴隨著一個逆時針方向的小角度旋轉。隨著溫度的進一步緩降,條紋1逐漸生長并旋轉,直至31.94 ℃,原有的指紋結構基本轉化為條紋1,如圖7(ⅲ)所示。
當溫度下降至31.45 ℃時,又出現了一種新的條紋結構,稱為條紋2(圖7(ⅳ),紅色圈標出)。這一新的生長條紋與之前的條紋結構形成了顯著對比,呈現出方向性的突變,傾向于與條紋1方向垂直。在這一過程中,整體的指紋超結構的有序度有所下降。
隨著實驗溫度繼續下降至31.32 ℃,在圖7(ⅵ)(使用藍色圈標示)中記錄到第三種新的條紋結構,命名為條紋3。這種結構呈現出進一步的有序度降低。相應地,均勻分布的指紋織構的疇區域也逐步縮小。這導致最終形成了兩套相互嵌套的碎條紋液晶超結構。
隨著溫度繼續降低,指紋織構逐漸轉變為FCD超結構,在31.12 ℃附近呈現二者共存的狀態。最終當溫度降低至31.02 ℃時,指紋超結構實現完全轉變,偏光顯微鏡下只觀察到了FCD超結構。
我們進一步建立了不同條紋超結構隨溫度變化而發生的旋轉規律。從圖8可以看出,隨著溫度降低,條紋0、條紋1、條紋2和條紋3均發生逆時針單向旋轉,接近勻速旋轉,且前三種條紋的旋轉速度呈遞增趨勢。由于條紋3出現的溫度范圍窄且有序性較差,其整體旋轉速度略有下降。在溫度到達31.2 ℃以后,近晶相液晶FCD超結構開始出現,導致后續旋轉角度基本保持不變。這些發現有助于進一步理解手性液晶超結構的自組裝演化過程,并為調控雙相態超結構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

圖8 不同拓撲缺陷條紋的旋轉角度隨溫度的變化Fig.8 Rotation angle of three fingerprint-like topological defect structures as a function of temperature
4.3 圖案化取向下手性液晶拓撲超結構的溫控演變
在均勻取向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對手性液晶超結構進行更加復雜的Q-plate圖案化取向構筑,進一步探究在圖案化光控取向下指紋織構的光響應過程以及前后FCD的變化。
如圖9所示,FCD出現在30 ℃。由于近晶相液晶有序度和粘度較高,并不具備光刺激響應能力,當溫度升高到33 ℃時,液晶超結構呈現出指紋織構,此時,該體系具備了光刺激響應能力。我們用功率為100 μW/cm2的藍紫光驅動手性螺旋結構解旋,由此,指紋織構旋轉并逐漸消失,最終呈現光潔的向列相態織構(圖9(c))。

圖9 Q-plate圖案化光控取向下手性液晶超結構的光響應過程以及光驅動前后FCD陣列的變化。(a)近晶相FCD超結構(光響應前),比例尺為50 μm;(b)膽甾相指紋織構(光響應前),比例尺為50 μm;(c)膽甾相指紋織構消失(光響應后),比例尺為75 μm;(d)近晶相FCD超結構(光響應后),比例尺為75 μm。Fig.9 Photoresponses of chiral liquid crystal superstructures under Q-plate patterned photoalignment and changes in FCD arrays before and after light-driving.(a) Smectic LC FCD superstructure(before photo stimuli),the scale bar is 50 μm;(b) Cholesteroid fingerprint texture(before photo stimuli),the scale bar is 50 μm; (c) Disappearance of cholesteroid fingerprint texture(after photo stimuli),the scale bar is 75 μm; (d) Smectic LC FCD superstructure(after photo stimuli),the scale bar is 75 μm.
隨后,將溫度重新降回30 ℃,將光響應前后的FCD超結構進行對比,可以發現:(1)光響應前后由于正交偏振設置導致消光區域(黑刷子)的數量和位置大體一致;(2)光響應后,部分FCD轉變為尺寸更小的FCD;(3)光響應后,出現由交錯的FCD組成的超結構鏈(圖10)。

圖10 Q-plate圖案化光控取向下手性液晶超結構的光響應前后的顯微放大織構對比。比例尺為75 μm。Fig.10 Textures of the chiral liquid crystal superstructures under Q-plate photopatterning before and after light stimulation. The scale bar is 75 μm.
此外,我們還展示了阿基米德螺線、偏振光柵等光取向結構下手性液晶超結構隨溫度的演變過程(圖11)。實驗展示了液晶相轉變過程和光驅動過程中豐富的手性超結構演化過程,并通過精確的溫控實驗分析了不同溫度下不同條紋結構的旋轉規律。這些發現對于理解液晶超結構的刺激響應行為具有重要意義,并為近晶相液晶材料的動態調控提供了實驗依據。

圖11 (a)阿基米德螺線(比例尺為75 μm)和(b)偏振光柵光取向結構下手性液晶超結構隨溫度的演變過程(比例尺為50 μm)。Fig.11 Superstructures of chiral liquid crystal versus temperature under(a) Archimedean spiral(The scale bar is 75 μm) and (b) polarizing grating patterned photoalignment (The scale bar is 50 μm).
5 結論
本研究結合光控取向技術、膜厚控制、電場、溫度、光場、手性等多元外場刺激對近晶相液晶中的FCD超結構及其相轉變后的指紋超結構進行了多維度的動態調控及規律分析。特別地,本研究通過優化近晶相液晶的組成,在8CB液晶體系(94.12%,質量分數)中摻雜4.8%(質量分數)的RM257和1.08%(質量分數)的光引發劑819,提出聚合物穩定策略,成功實現了近晶相液晶FCD微透鏡陣列的電刺激動態可調。此外,通過在99%(質量分數)的液晶8CB里摻入1%(質量分數)的光敏手性分子開關ChAD-3c-R,巧妙利用近晶相液晶的雙相態優勢,實現了基于同一材料體系在光、熱等外界刺激條件下不同多層級手性超結構之間的動態轉變、調控和演化。
本研究提出的多元外場調控策略加強了對液晶材料結構及光電性能調控的維度、力度和靈活度,將推動新型液晶光電功能元器件的開發和應用。例如,手性超結構的動態轉變和調控為智能窗戶、光開關、傳感器和信息存儲等領域提供了新的材料平臺;電刺激下的可調FCD微透鏡陣列可應用于先進光學系統,如高分辨率成像、光通信以及動態顯示技術。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將更深入探究近晶相液晶自組裝多層級超結構的構建和動態調控的微觀機制,并結合新型液晶功能材料開發,將液晶超結構的動態調控技術轉化為新型傳感元器件和新型平板顯示等新一代信息技術領域的應用。